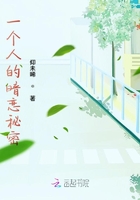八月初,桂子初开。王夫人言身体不适,常于卧榻昏睡。
太医诊后报皇上,言王夫人已有两个月身孕,可胎动迹象迟缓,羊水鲜少,却未能查探出是何缘故。
皇上龙颜大怒,斥太医无用,白受俸禄。
王夫人却泰然处之,处处容人,替已是乏术的太医求情:“太医尽力写方子就是,写方子可是需费心力的,皇上莫要苛责。”
她眼睛越发清亮,眉黛娟秀,行走有端。皇上见王夫人这娇弱惹人怜的模样,心下欢喜。环顾四壁,又觉漪兰殿太过素淡质朴,皇上不由得叹息:“你这宫室太过简陋了,朕真是亏待了你!”
“哪里!漪兰殿该换的都换过了,皇上惦着娡儿!”王夫人窝在皇帝怀里,撒娇道,“臣妾不就留下那醉仙灵芙嘛,平阳可是爱得紧!”
皇上宠溺地刮了刮王夫人的俏鼻梁,“你说的是,朕偏不许了,来人,把那醉仙灵芙给朕撤了!”
“别!”王夫人拦住皇上,嗔道,“臣妾宫内本就素淡,怎么能把这灵芙给撤了呢,这可不行!”
我见王夫人将为人母,也颇为感怀。想起自己撤去醉仙灵芙后精神再也不似先前萎靡,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竟壮着胆子上前直谏:“皇上,丹心见这灵芙花花朵张开,色泽却枯燥,估计是殿内香熏浓郁,灵芙经受不住。王夫人日间打蔫,怕也是受了这熏香缘故。”
“皇上,老臣驽钝,实在该死!”我话说到这份儿上,在场的老太医很快明白了前因后果,料想事态严重,跪在地上不停磕头。
“太医,你这是为何?”皇上见太医只顾磕头,惊忧地望着王夫人。
“怕是这熏香捣的鬼!”太医正色道,“臣听闻醉仙灵芙和某些香木混在一起是有毒的,夫人……夫人怕是中了毒!”
果真有毒!我吓得心怦怦直跳,阿娘中醉仙毒,这宫中竟也会出现这毒药,这般阴魂不散纠缠着我,就像是冲着我来的!我又怨又恨,真怕王夫人有差池。
“什么?”皇上不可置信地望着太医,径自站起身子,“朕要看看究竟!”
“臣求撤下香炉,容臣先细看,再告知皇上究竟,还请皇上先行避开!”太医顾虑皇上龙体,言辞诚恳。
“不,朕要亲验!”皇上并无顾虑,要求亲自检验,令我在侧协助。郭公公和太医小心地将香炉移开,我小心地拿起炉盖,望着袅袅烟香退去,果然见着了淡紫色的奇鲮香木!
木质已有些生焦,纹理细密,呈花蕊状,我放于手心一捏,便碎成末。
第十三章废立“果真,果真!”太医不住叹息,也不知是惊慌的缘故还是被烟熏的缘故,居然老泪纵横。
皇上脸色已是煞白,剑眉皱成一团。
皇上掂起被郭公公用黄巾包着的香木,掌心用力一捏,便碎落一地。我从未见过皇上像如今这般面带杀气,毫不掩饰心头怨恨。皇上震怒:“竟有人让宫中十二年后重现奇鲮香木,无论这人是谁,是何居心,朕都要让他永生永世不得安宁!”
皇上说完此话,闭眼不语。我心头震撼,睁大眼睛低着头,不敢喘息。
太医搔首踟蹰,犹豫再三才道:“混上了醉仙灵芙,确是有了毒性,恐怕小皇子难保……”
哗啦一声,皇上拂袖将茶几上的玉盘扫落地上,目眦欲裂,“你敢再说一遍‘小皇子难保’,朕要你掉脑袋!你没看见朕的皇子好好活着吗?”
太医急欲求饶。皇上不依不饶,威慑道:“太医你胆敢诅咒朕,朕偏偏不受!”
“臣该死!”太医磕头砰砰有声,瑟瑟发抖道,“老臣实在该受剐刑,可老臣若是真的受了此刑,夫人皇子得以安康的话,臣万死不辞。”
这话听着依然刺耳,皇上脸面绷得更紧,太医以为皇上有所动摇,顺势接着往下说:“皇上,奇鲮香木和醉仙灵芙相混,对于怀孕之人简直……简直就是……”
太医把心一横道:“受此香熏者,胎儿出宫多为死胎,抑或畸形,大大不吉,大大不吉呀!臣请皇上祸患止于忽微,挥剑断臂,以绝后患呀!”太医额间已沁出冷汗。王夫人闻言已晕厥过去。
皇上面色灰败,气息粗重,众人把头低到地上去,皆不敢妄动。
“拉下去砍了!”皇上眼皮没眨一下,就勒令处死太医,我耳膜似被生生震破。太医还未及呼号,便被拖走。我吓得腿软,恨自己怎不早些相告。
我旋即冲上去伏在皇上脚下,“丹心有错,未能早有警觉,方铸成大错。医者父母心,太医直言,皇上却要处斩太医,是为讳疾忌医,太医何罪之责?”
“你……”皇上瞪着我,气得发抖,指着我鼻子训,“你简直狂妄!”
“丹心错就错在心存懦弱,学艺不精,不敢定断,方才误了夫人。”这话一出口,怕是王夫人也不会原谅我了。
“也罢,暂留太医一命,朕不想满手血腥。”见我毫无悔意,皇上倒也冷静下来,“让朕的孩儿也为朕不齿。”
我喉头酸涩,立于高处的,是皇更是父呀!
人世间比看着自己孩子死去更可怕更揪心更残忍的是——要亲手将他虐杀!
这样的残忍,之于寻常父母,尚且难以忍受,对于一个是皇是君的人,又是怎样的噬心蚀骨?
江山动乱犹可雄兵一策,喝令四海,征战天下;而此刻自己的娇妻爱儿受难,却无力挽救,甚至要亲手杀害,这是怎样的残忍!
皇上待我照顾有之,恩宠有之,严苛亦有之,我却误了王夫人腹中孩儿性命——那是刘彘的亲弟弟,也算是丹心的小弟啊。
宫室内一片寂静,一炷香过,皇上才启声:“都退下吧,今日之事外泄者,杀无赦!”
君令下,皇上出宫殿。我眼睛昏花,殿门光线浑噩,模糊中那明黄身影已了无踪迹。
三日后,皇上送汤药,王夫人长跪于地,不肯饮。奉旨太监强行灌药,王夫人当场昏厥,沉睡三日不见醒。
王夫人用药之时,皇上身处掖庭“保宫”,受传诏者乃栗姬。保宫之内情形不得而知,但对于“保宫”,我还是有所耳闻的。
未央刑房,首暴室,次保宫,末蚕室。入暴室者,进去后都是由宫人驾小车推出来的,裤裆自膝下染上三尺红,所惩大多为犯错不可饶恕的“贱人”。而入保宫者,不死也残!
刘荣顾及母亲,皇上却在此时应下众臣废储檄文,下诏废了栗姬夫人,削去刘荣太子封号,拜受临江王!
皇上怒极,不仅控制了栗姬、周亚夫、窦婴一众,还加强南北军护卫京畿,严密戒备武库!
刘荣被废了!我脑袋发蒙,一时恍恍惚惚。
皇上传诏漪兰殿,要我入玉华亭。我正想这是唱的哪一出,怎会是我呢?
漪兰殿众人皆神色鄙夷望我,我知晓那日为太医开罪,得罪了不少人。我不敢多言,可也暗自庆幸,皇上终是要我回报了!
因王夫人流产之事,我怕极了这宫里一切。若我推托不去,倒也可以逃脱,与漪兰殿重修旧好,可我不够狠绝,终是下定决心前往。
玉华亭,琴音清冷,我思绪回到那个月圆之夜,玉兰花慢,丝竹萧瑟。赵信远归匈奴前夕,刘荣的心境与我相通,同是天涯沦落人,我怎能不动容?
刘荣停下抚琴,迎风而立,白裳落拓。我不敢靠近,只远远地张望。
“你来了。”声音略显疲惫。
“不知太子殿下诏丹心来,所为何事?”我诚惶诚恐。
“我已是临江王了。”他自嘲一笑,神态落寞,“丹心,你是知道的吧?”
“嗯。”我点头,声音很低。
“知道我为何唤你来此?”
我想也未想便应答:“皇上旨意。”
他讪笑,“哈哈,不过邀人送别,经由父皇同意罢了,你自可不来的。”
“丹心惶恐。平日和太子殿下无深交,竟得太子殿下荣恩赏识,实是汗颜。”我听着心里发酸,他说起送别,我便想起那夜听着他弹奏的《江有汜》,心下不忍。
如今,赵信留下了,他将长伴我身侧。而刘荣呢?他本是储君,此刻见我却也要经由皇上允许,悲凉至斯。何况,霍织艳已作出选择,并未随他而去,日后要寻,怕也要越经山川万里。
“陪我喝一杯吧!”亭中有台,引得曲水。我接过刘荣递过的美酒,感念他的一曲《江有汜》。若不是那曲,我怕是未料到我会如此依赖赵信,也未必会求他留下。我轻抿了口酒,便再也喝不下。
“刘荣未有幸与你深交。当日在长信宫时,阿娇一曲《云中君》,却是你听得最明白。刘荣视懂琴之人为知音,因而也并不顾念其他,执意相邀你,我也未觉不妥。”刘荣举杯敬我,说辞极是豁达。
“太子……王爷胸襟,令人叹服!”我一饮而尽,肚中火辣辣的,这杯酒,不好喝!
“谢太子……谢王爷殿下!”我以衣袖擦擦嘴角,一时口拙,几乎又说错了话。
“丹心可想再听我弹琴?不如让刘荣趁此再弹一曲!”未等我回应,刘荣已令人抱来绿绮,置于流觞曲水间,开始弹奏。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一曲《采蘩》,每个音律都击在我心头上。曲中声声言明我身负职责,要恭谨侍奉,当不辞辛苦,必要时须得听令,不可推脱。
我当忠于何人?皇上?王夫人?还是刘彘?刘荣?僵立听完一曲《采蘩》,我已然三魂七魄相分离。待我回神,刘荣只静默望我,眼眸清俊。
三日后,王夫人醒,皇上极尽欢颜,漪兰殿红妆亮彩,张罗平阳公主婚嫁。
九月初,平阳嫁与曹寿。那日,她真美,身穿五彩织锦嫁衣,娥眉淡扫。
花嫁不似南宫出嫁时隆重浩荡,却也足见气派。
卫青随平阳入代地。皇帝虽未下令,却也默许卫青居于婚辇之侧,随行护驾。那青灰骏马之上如鹰隼一般傲然挺立、英姿勃发的少年,再也不似初见时的毛头小子,那亮若剑锋的眸子闪动,竟让我看得失神。
他拿走了干将剑,却不愿久居长安,反倒是随平阳同往偏隅代地。那双狼一样的眸子在心底闪烁,我胸口闷得喘不了气——干将剑已归他,我本该同他两清,可我却未能放开。似尝败绩,又似自尝苦果。
花嫁远去,宫中再无喧嚣之意。倒是十月,未央宫云谲波诡,风云再起。栗姬难耐枯燥,神志混乱,竟自悬于宫中,丽人去也。
废太子刘荣请旨,为母亲守灵至翌年三月。
第二年年初,王夫人被策为皇后,十二日后,刘彘被封为太子,改名“刘彻”。
彻,“心彻为知,知彻为德”,语出《庄子·外物》。我仰首朗笑,喜悦之下更觉满心酸涩,走到这一步毕竟不容易。
二月初,长安城积雪尚未消融,春意迟迟,废太子刘荣便前往江陵。
长安城落雪纷飞,白帷遮住秀色,渭水流波似也凝滞。我高高立于城墙头,俯仰天地,灰蒙蒙一片。
想起那个祭天的日子,我也处在这样的高处,看着下方的列阵,那时的自己虽是砧板上的鱼肉,心里却是极其得意——我打心眼里看不起立于我脚下的人。
刘彻立于我身侧,他以新储君尊位睥睨天下,而我是离他最近、相伴他最亲的人,此时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马车声响,刘荣背影萧瑟。车辙碾过的土地,雪水混杂泥浆,凛冽气息中充斥着泥腥味。
我转身,背着刘彻,不再言语。
刘荣走的那夜,雪夜月光冷,我一人独住漪兰殿偏室。我未曾料想的是,我竟在这一天来了月信!
腹间绞痛,我惊忧害怕不已。在匈奴时,师傅便有意告知提点我,我未觉有所难处,可当它来时,我仍有些不知所措。
“丹心,今夜我们一起喝酒去,可好?”赵信迈了进来,我慌忙将染上血污的衣裳藏在锦被之下。
“不去了,不去了!”我坚决道。
“丹心,你身子不舒服?”赵信望着我,心下疑虑。
我未回答,岂料赵信却为我圆起了场,“也罢,这几日太子殿下想着出去走动走动,你不愿去也不打紧。不过,等太子殿下回来,肯定会来探望你的。”
“好!有劳大哥,望郊游尽兴。”我极是感激地送别赵信。待他走远,我方觉锦被上沾染一点血红,形如腊梅。
刘彻回宫后,果是疾奔着来探我,一并来的还有赵信,他望我的眼神并无异色。述完长安民风,刘彻更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道:“南越这块,匈奴这块,还有这——西域,我要断匈奴右臂!”
“丹心,你怎么不好好听?”看我思绪游离,刘彻扬眉呵斥。
“是呀!”一侧赵信也提醒,“说到匈奴了呢,丹心不想听听大哥意见?”
“且说。”我心不在焉。
“大哥。”我唤刘彻,“丹心近来精神恍惚,想换个地方好生休养,不知大哥能否施舍丹心一亩三分地,由着丹心耕作去?”
是啊,漪兰殿不可久居!
“哈哈!”刘彻大笑,“大哥怎舍得丹心受此等委屈?你若要清静,自然可以去清和殿,丹心可是愿意?”
“清和殿?”我默念,风清云和,好名字。
“丹心谢殿下!”我承情接受,自然不敢怠慢。
刘彻故作嫌弃,“丹心真是,才几日功夫,就这样见外!”
我巧笑,“大哥多虑了。该有的礼节是不能失的!”
赵信望我,嘴角噙着一丝笑意。我回望他,勉力笑笑,心里却暗骂自己——刘丹心,你还真是不识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