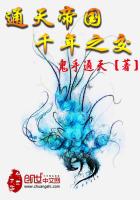一雨便成秋。
淅淅沥沥的细雨终于停住,天已放晴。
风轻云淡,远山如洗。
此时的西湖,已带有几分初秋的景象。
陆惊鸿仔仔细细地数了数口袋中仅有的二十三两五钱碎银,哼着小曲踏出船舱,溜上了岸。
他摸着瘪瘪的肚子,下定决心要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光,好好享受享受。首先当然就是“西湖第一厨”的东坡肘子八嫂鱼,麻婆豆腐烧乳猪,还有……陆惊鸿美滋滋地想着,口水忍不住流了出来。
——这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肯亏待自己。
至于钱花光了以后怎么办,他更不去想。
城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一切出奇地平静。
直到晌午,陆惊鸿才带着填得满满的肚子和一身崭新的衣服,慢慢地踱回了小船。
他一跨进船舱,就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鼻息均匀,睡得正香。
这个人竟然就是金浣花。
他身上还穿着昨夜那身湿漉漉的衣服,竟似没有回家换过。
金浣花一听到他的脚步声,立刻睁开了眼睛,笑道:“你终于回来了?”
他仿佛已等了许久。
陆惊鸿这时才发现,这个骄傲的年轻人笑起来的时候,模样还是很讨人喜欢,他的眼睛里,也流露出少年的率直与纯真。陆惊鸿的心中,已渐渐对他生出些许好感。
金浣花已经跳下了床,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了!”他看起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你为什么不回家去?”陆惊鸿突然问道。
金浣花面色一变,笑容似乎僵在了嘴角,半晌才道:“我不想回去。”他看着陆惊鸿:“因为这些天来,我在自己家中,根本就没子合眼。”
陆惊鸿有些吃惊地看着他。
金浣花摇了摇头,苦笑道:“我知道这话说出来,你又不会相信。”
他又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别人都以为金二公子的日子,一定过得很逍遥快活,其实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些天来,我每天都是寝食难安,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梦见自己被一根丝杀死。”
陆惊鸿皱眉道:“一根丝?”
一根丝也能够杀人?这种荒唐的事,恐怕只有在梦中,才会碰到。
他看着金浣花,道:“这件事你为什么不跟你大哥讲?”
金浣花面色变了变,半天才道:“我大哥这段时间以来,几乎很少跟我说话,他每次看着我的时候,脸色阴沉,眼睛里也阴森森的,不知为什么,总是让我想起梦里那个用一根丝杀人的恶鬼和尖脸无常来。我总觉得,他好象要对我不利。”
陆惊鸿摇摇头道:“我看你最近休息不好,所以脑子里总是会出现幻象,看到自己的亲大哥,也会疑神疑鬼的。”
金浣花看着他,颤声道:“你还是不相信用我,我大哥他,他……”他的话还没说完,小船忽然轻轻一晃,似乎有人踏上了船,金浣花如惊弓之鸟般,立刻跳了起来,飞快地走了。
陆惊鸿甚是奇怪,走出舱门,一直走到了船尾的甲板上。
舱外阳光明媚,一颗光光的脑袋,在船尾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陆惊鸿一下子跳了过去,大声道:“喂,你是谁?你到我的船上来干嘛?赶快给我下去!”
光光的脑袋转了过来,眯起一双眼睛看着他笑道:“四海之内,皆有缘人,红莲白藕,本是一家。施主又何必生那么大气呢?”
陆惊鸿看着面前这个和尚,忽然眨眨眼道:“我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和尚找我做什么?”
“和尚不要钱,和尚是来化缘的。”和尚答。
“化什么缘?”
和尚转过了身,一张苦瓜脸上笑得象是在哭:“和尚是来化坐缘的!”
“坐缘?”
“暂借施主小舟一隅,歇息片刻,是为坐缘。”
陆惊鸿简直是哭笑不得,他从未听过如此稀奇古怪的名词,便又问道:“和尚叫什么名字,打哪里来?”
和尚垂下眼睛,双手合什道:“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施主难道没有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杭州城飞来峰不动寺的苦大师?”
陆惊鸿哈哈大笑:“大名鼎鼎的苦大师?是大名鼎鼎的哭大师吧?”他笑得捂住肚子,仿佛连肚子都要笑破。
和尚的一张苦瓜脸果然象是在哭:“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皆苦,和尚我又怎能独乐乐?原该为世人一大哭!”他竟然真的大哭三声,却又大笑三声。
陆惊鸿不解道:“和尚哭什么?笑什么?”
苦和尚答道:“和尚哭的是有人贵为王侯,一夕殒命,反不如一个普通百姓平安快乐;和尚笑的是有人居然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去割死人的肚子,死人的肚子有什么好看,你说这事好笑不好笑?”
陆惊鸿皱眉道:“和尚说的可是官府已派出仵作在解剖小康王的尸体?”
耳边忽然风声响起,一个人身形一闪,已笑嘻嘻地落在了船上,道:“你若连京城十大名捕中的老七无情手吕钦到了杭州都不知道,消息就未免太不灵通了吧!”来的正是聂乘风,他的肩上,还背着一个看起来沉甸甸的包袱。
聂乘风一转眼看见苦和尚,又嘻嘻笑道:“陆惊鸿,这回你要倒霉啦!你知不知道世上最惨的事是什么?”不等陆惊鸿回答,他已经抢着道:“就是一个和尚撞上一个穷鬼,两个人都穷得响叮当!”
苦和尚用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聂乘风。
聂乘风道:“苦和尚,你的脸上,怎么总是一副哑巴吃黄莲的苦相?”
“和尚此刻腹中饿得咕咕叫,没有饭吃,就只好吃苦了。”苦和尚道:“聂施主一向劫富济贫,出手大方,所以和尚想向聂施主化一顿几百两银子的斋饭。”
聂乘风一下子跳了起来:“和尚这是化缘还是打劫?”随即学着苦和尚的样子苦着脸道:“软红赌馆的大门,真是万万进不得的!我每次从里面出来,浑身就好象洗了澡一样输得干干净净。”
陆惊鸿故意板着脸道:“你知不知道世上比一个穷和尚撞上一个穷鬼更惨的事是什么?”他不等聂乘风开口,马上道:“就是一个和尚撞上两个穷鬼,三个人都一样穷得响叮当。”
聂乘风叹了一口气,道:“真是世道艰难,民不聊生啊!连我神偷都有一文不名的时候!”
陆惊鸿忽然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你身上虽然洗了澡,但是身上背着的包袱里的东西,说不定很值钱,可不可以让我看看?”
聂乘风连忙后退一步,摆手道:“没什么没什么,你看了说不定会很失望,还是不看的好。”
他的话还未说完,忽然觉得背上一轻,包袱已到了陆惊鸿手中。陆惊鸿将包袱用力一抖,里面的东西就唏哩哗啦的全落在了甲板上,其中的每一样,竟然都可以算得上是价值连城的珠宝。
聂乘风连忙蹲下身,看看这个,又摸摸那个,一脸痛惜的神情:“这些珍宝古玩都是我从小康王寿宴上辛辛苦苦工作换来的,摔坏了你赔得起吗?”
陆惊鸿也蹲下身,忽然眼前一亮,从一大推玉石里拣出了一件东西,揣进了怀里。
聂乘风匆匆忙忙将甲板上的东西收拾妥当,又道:“这两天城里外松内紧,我带着这么多东西很不方便,想来想去,还是放在这只船上,比较安全。”他又盯着陆惊鸿道:“你一定要好好保管哦!”
陆惊鸿大笑道:“你自己做贼还不够,还要把曲兰衣的船当贼窝!”
苦和尚忽然插进来道:“陆施主装聋作哑,我和尚可是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聂乘风眼珠一转,笑道:“出家人六根清静,不理俗务,这件事又与和尚有什么相干?”
苦和尚还未答话,忽听船舱内传来一声重重的叹息:“和尚可以不理红尘俗事,我吕钦身在公门,却实在没法子这么逍遥自在!”
聂乘风一听到“吕钦”两个字,忽然象只中上箭的兔子般高高跃起,窜下船头,接连两个跟头,就不见了踪影。
苦和尚叹了口气,道:“阿弥托佛,看来陆施主的霉运很快就要来了,和尚还是离得远点比较好。”说完这句话,他立刻跳下了船,看也不看陆惊鸿一眼,仿佛他已经是一块又霉又烂的臭豆腐。
陆惊鸿只有苦笑。
他一走进船舱,就发现舱内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皂衣黑靴,一双浓黑的剑眉之下,双目闪着利剑般的寒光,紧盯着他,脸色沉得就象个捉鬼的钟魁。
陆惊鸿笔直走了过去,就在这个人的对面,伸直双腿,舒舒服服坐了下来,道:“阁下可认得十大名捕中的老六黑刀吴缺?”
“天底下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这个人,”吕钦从鼻孔中冷哼了一声:“此人一向装模作样,目中无人,居然还排在我的头上!”
陆惊鸿这才知道十大名捕中的老六黑刀吴缺和老七无情手吕钦,一向是谁都不服谁,暗中较着劲。看来他搬出黑刀吴缺的名头来,实在是表错了情。
吕钦忽然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天杀’?”
陆惊鸿道:“‘天杀’?江湖上倒是流传有这么一个神秘奇特的杀手组织,不但它的首领从没人见过,而且凡是与天杀订了生死约定的人,只要天杀一动,永无更改,要杀的那个人也就死定了。”他笑了笑,又道:“但那也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既然天杀如此神秘,别人又怎么会找得到它?”
吕钦沉着脸,道:“不是传说。”
陆惊鸿奇道:“哦?”
吕钦道:“天杀有一名鬼使负责与外面联络,我们已经查出是个名叫‘麻衣鬼算’的瞎子,他每晚都会换一个地点,接受一个约定,然后在第二天清晨燃起一道紫色的炊烟作为信号,不出三天,他们要杀的人就会出人意料地死去。江湖上很多成名人物的突然死亡,其中十有七八,就是天杀所为,就好象这次小康王的死。”
陆惊鸿发现事情已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趣。
吕钦接着道:“仵作已经验过尸,刺杀小康王的凶手,是个惯使左手剑的杀手,与以前‘天杀’作案的手法同出一辙。”
陆惊鸿忽然笑了笑,道:“原来一向铁手无情的吕大人肯费这么多口舌跟我讲天杀,原来是想试探我陆惊鸿跟天杀有没有关系,只要我稍微有一个动作不对,吕大人就要出手拿人,可是?”
吕钦冷冷看了他一眼,道:“事发前后,你一直在明月楼外的船上,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辑捕你归案的证据,但你的船上有一批与凶案有关的赃物,我想请你跟我回去走一趟。”他的话说得斩钉截铁,绝无商量余地,说到“请”字的时候,也丝毫没有请的意思。
陆惊鸿看着他,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丝不易捉摸的笑容:“我现在很想说一句话。”
“什么话?”吕钦仍是冷冷的道。
陆惊鸿微笑着,慢慢道:“吕大人若是肯笑一笑的话,样子一定会比现在好看得多。”
他的人似乎还坐着一动未动,却忽然平空而起,穿破顶蓬飞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