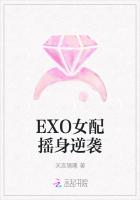距离皇后千秋已经过去三天,在这三天里发生了太多的事。
比如北蛮使者闹着要大秦给出个交代;比如朝堂上众臣纷纷上书对她进行弹劾;比如秦帝虽然仍坚持让她暂代五城兵马司的总指挥使,但还是迫于压力罚了她三年俸禄,在家闭门思过半个月;再比如,今日是大壮与翠缕下葬的日子。
京都一连多日的艳阳天,今日却罕见的飘起了毛毛细雨,打湿了路面的青石板,也模糊了远方的景色。
顾长歌难得穿了一身白色的缎袍,幼年时,她爱穿一些红色、粉色的衣衫,后来她习惯穿青色、蓝色,白色她却是极少穿的。曾经龙霂言好奇之下问过她,换来的只是她的笑而不语,久而久之他也就不问了。
其实,哪有那么多理由啊,只是记忆里有个人曾捂着她的眼笨拙的安慰她,让她别哭,可却没发现她残了的红妆污了他的衣衫,那红色朱砂趁着白色的衣衫真是刺眼的很,也是暖的很。所以她极少穿白色,因为哪一身也没记忆中的那身好看。
今日……
顾长歌斜靠在长廊的柱子上,长时间的驻足让纷飞的雨丝渐渐润湿了她额前的鬓发,不远处的侍女注意到了这点,但却并没有上前,她们只是安静的站在原地,低垂着头。
此刻没有人打扰她,甚至一向热闹的将军府今日也格外的,寂静。
不知道多久,久到顾长歌都以为时间仿佛静止了般,在烟雨朦胧处终于出现一个身影,他也穿了一身白色的布衣,打着素面油纸伞,一步一步,越走越近。
走到近旁,末影弯身行了个礼,冷淡的面容下是一丝难掩的惆怅:“公子。”
顾长歌将手探出长廊,雨水滴在掌心,是一股凉凉之意,沉默片刻,她还是问道:“他们,走的可还好?”
“北蛮使节还在京都,而且最近朝堂上前对公子很是不满,所以······”
明白末影的为难,顾长歌冲他笑了笑,只是那笑意还未到达眼底便散去,“你又有什么好惭愧的,大壮的最后一程,我甚至只能在这个偌大的将军府里舒服的呆着,比起我,末影你无需自责。”
末影轻声安慰:“公子,这也怪不得您,毕竟皇上下旨让您闭门思过,如果偷跑出去被发现,恐怕又是一场弹劾。等您解了禁再去看他们,大壮他们想来也不会怪您的。”
“不会怪我吗?”顾长歌喃喃,随后又像是想起什么,追问道:“他们葬在哪,那可是个好地方?”
末影道:“属下将他们葬在了南山一处高坡上,从那正好能看到京都,公子,在没请示您的情况下,属下斗胆将他们合葬在一起,还望公子降罪。”
顾长歌摆摆手,道:“也好,这样的安排想必也是大壮想要的。”
话题暂时告一段落,他却几番踌躇,又再次开口:“大人,府外有个自称是刘根生表叔的人求见,门外的侍从说,他等了许久。”
见顾长歌微侧着头,脸上露出迷惑的神色,末影解释道:“刘根生就是大壮,这是他的大名。”
顾长歌怔了怔,半晌才轻轻点了点头:“让他进来吧。”
待长廊又只剩她一人时,顾长歌却低低笑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笑得她喘不上气,笑得她眼泪都止不住。
她原以为虽然她常常忽视他,但终究心里对他有一丝爱才之意,但何其可笑,这个人在她身边这么久,原来她连他的名字都没记住。
顾长歌啊顾长歌,你的所做所为,真的如同一个笑话。
入夜,大街上的铺子已经纷纷上了门板,打烊歇息,但是京都的烟花之地依然莺声燕语,人来人往,京都最为著名的烟云楼更是人声鼎沸。
烟云楼的后门,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叩响了门板,不一会儿,一个小厮打扮的人从门内探出脑袋,在打量了四周,见无异状便侧身将来人请了进来,之后大门合上,后门处又恢复了寂静。
“殿下。”
屋内琴音戛然而止,龙霂言眉头微皱,冷淡出声:“进来吧。”
来人从屋外进来,绕过屏风,兜帽揭下后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庞:“我躲躲藏藏来看你,语气可真冷淡。”
龙霂言也不理他,只在一旁的净盆中将手洗净,然后从云起手中接过干帕擦干,才坐下不紧不慢端起一杯茶,道:“嫌冷淡就滚回你的驿馆,没人让你来。”
来人嘿嘿一笑,开口:“我偏不。好云起,快给你家宋公子也端盆热手来净净手。”
云起抿唇一笑,知道两人有要事要谈,笑着应了句是,就端着净盆出去了,还不忘将门带上。
“啧啧啧,好歹云起从小就跟在你身边,对你一片痴心,也不见你给她个名分。”
龙霂言冷声道:“宋迟,不要让我找人把你丢出去。”
宋迟也不在意他语中的威胁,自顾自的将身上的斗篷又裹紧了几分,开口抱怨:“你这怎么冷的跟个冰窖一般,也不加几个炭盆。”
只不过十月底,宋迟却已穿上棉衣,况且大秦远比西齐气候温和,扫了一眼他的脸色,龙霂言眸色闪过一抹暗色,心里浮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你······”
宋迟将手指放在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笑着开口:“龙星彦,别大惊小怪,你知道我一向怕冷。”
龙霂言伸手拽过宋迟的手臂,无视他的抗议,探了探他的内息,霎时,面色铁青。
宋迟还在娘胎时,他的母亲曾经一时不察中了别人的暗算,这导致宋迟出生时体质孱弱,即使后来他的母亲带着他遍访名医,得到的还是他活不到成年的断言。
宋迟的家族是西齐的贵族,他虽是嫡子,却不是唯一的儿子,身体虚弱再加上外祖家早已式微,幼时的他过得并不像别人想的那么风光,而他的母亲也在父亲不断纳了一个又一个新人的日子里,抑郁而终。母亲早逝又得不到父亲的重视,没有人知道宋迟那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别人提起永安侯家的公子,永远只有二公子、三公子,而没有嫡出的大公子。
在宋迟十五岁时,他的名字却响彻西齐。
因为他是西齐建国以来,唯一一个在志学之年继任爵位的人,而他之所以能继任永安侯,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其他能与他争夺爵位的人都死了。纵然后来西齐皇帝下令彻查此事,得到的结果仍是这些人的死亡与宋迟并无关系,他只是好运的,活的比他们久点。
何其可笑,却又何其讽刺。
随着宋迟被正式册封为新一任永安侯,西齐贵族圈里开始人人对他避而远之,纵然以前也没人与他有过来往,但也不像现在这样,避他如蛇蝎。即使已经调查出所谓的真相,可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坚信自己眼中的真相。
宋迟就是个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人。甚至就连街头巷尾的百姓都常常拿他吓唬不听话的孩子:“你要是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永安侯府,让宋迟天天陪着你!”
只是七年时间,再提起宋迟,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年少有为,惊才绝艳。
虽出身武将世家,但因身体虚弱,宋迟走的是文官的路子。从无实权的翰林院侍读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他用七年时间走了别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走的路。
不管是大朝会上提出的种种治国良策,还是出使番邦凭一己之力争得种种利益,亦或者随手做的文章诗篇就让秋山先生推崇备至赞一句才华横溢,每一项,都非常人所及。
世人都说大概只有昔日的大秦第一才子顾君行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只可惜他英年早逝,而宋迟虽身体孱弱,不是长命之相,但所幸目前看来还能为西齐尽一份心力。
可没人知道,他早已病入膏肓,这么多年不过全凭龙霂言上天入地为他找着各种续命的灵药,现在,也终是撑不住了。
安慰的拍了拍好友的手臂,宋迟道:“何必生气,我早已是个一脚踏进鬼门关的人。”
从十岁起,龙霂言就很少表露自己的情绪,因为从小他就被教导着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情绪,这样,才不会被人抓住弱点,但此刻,他却有些失态的咆哮起来:“药王谷的人不是答应出手了吗!你告诉我,你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
“世上人人都说没有药王谷治不好的病,只要药王谷出手,即使那人在鬼门关他们也能拉回来,可是,星彦,我却独独是那个例外。”宋迟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瘦削、白皙,仿佛能看到隐在皮肤下的血管,“其实这么多年与药为伴的日子我也过够了,我终于,要解脱了。”
话音刚落,原本暴怒的龙霂言像被人一下子定在了原地。
幼年相识于西齐皇的寿宴,他是远离宫廷被人遗忘的九皇子,他是身体孱弱不被重视的侯府公子,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在年少的时光里,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远离西齐的那些日子,他不是陪在小小身边,就是在全天下找着各种灵药,他总是想着怎样去延续好友的性命,却忘了问他,这样活着,他愿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