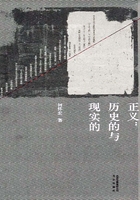1786年8月17日,在位46年之久的腓特烈大帝离开人世,普鲁士的百年启蒙运动也宣告结束。现在,康德的学生普莱辛在1783年10月15日发自柏林的信中向他提到的担忧已经应验了。当时听起来仿佛是在柏林启蒙思想家中间流传一种密谋理论,据说,狂热、迷信和愚昧的悲惨时代即将来临,而且面临限制思想自由的极大威胁。对于这种担忧,康德马上作出反应,在1784年《柏林月刊》上发表了《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回答》中,他首先要求学者享有公开使用自己理性的无限制自由。康德在文中首先认为,启蒙运动的重点,即“人们摆脱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是“宗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与腓特烈二世是一致的。腓特烈二世认为,“在宗教问题上不为人们设置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是他的义务,让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幸福地生活。
刚开始的时候,事情似乎并不很糟糕。人们已经厌倦腓特烈二世。这位君主深居简出,默默无闻地执政,似乎只有少数人对他的逝世感到悲痛。现在接替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国王,这位年轻的国王虽然也愿意执政和履行他对普鲁士的义务,但他更愿意享受生活。老弗里茨这个侄子还是王储的时候,身边就小妾如云,而漂亮但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威廉明娜·恩克已经给他生了五六个孩子。“胖子威廉”的风流韵事是家喻户晓的。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性情与老腓特烈完全不同。人们认为他仁慈、好说话,没有清规戒律。在普鲁士的历史编纂学中,他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对待。不容忽视的还有,在他的统治下,“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甚至贫穷和野蛮的国家开始了一个文化繁荣和天才涌现的时代,这个时代延续了50年。人们不能抹煞这个国王的任何一个功绩。”
1786年9月17日,国王来到柯尼斯堡,以便以腓特烈-威廉二世国王的身份参加加冕仪式并宣誓效忠。他不是一个瘦弱的禁欲者和玩世不恭的自由思想者,而是一个感性的、虔诚的男子汉,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康德在这一年第一次担任柯尼斯堡大学的校长,理应主持大学里相应的庆祝活动。他必须安排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以大学的名义欢迎新国王。9月18日,康德在大学评议会几位成员的陪同下,在王宫里被介绍给了国王,并且受到了国王的隆重欢迎。那场不久就开始的,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斗争,并不是直接由腓特烈-威廉二世发动的。甚至到了1798年,康德在回忆起他和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时,还赞扬这位国王是一位勇敢、正直、热爱人类、非常杰出(禀性刚烈除外)的君主,“他也认识我,不时地让人带来他那仁慈的问候。”在他的任期内,康德被任命为柏林科学院院士,并于1789年3月3日起领取每年220塔勒的额外津贴,以贴补他相当微薄的教授收入。
反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主要是由一名神职人员策划的,此人已经将年轻的王储诱入唯灵论和神秘主义的歧途,1783—1786年,他还是王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老师。早在1781年,他争取王储成了传奇的玫瑰十字会这个怪异的修士会成员,1760年,共济会一些分会采纳了玫瑰十字会这个炼金术的秘密同盟的形式。在他的影响下,王储将感性的生活乐趣与假装虔诚的信仰融为一体,这种信仰经常使腓特烈-威廉痛哭流涕。有时他会长时间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沉溺于神灵世界,还硬说好几次看到过耶稣。
约翰·克里斯托夫·沃尔讷(1732—1800)是一位宗教视灵者,腓特烈二世将他称为“欺骗成性、诡计多端的牧师,此外什么都不是”,拒绝了他成为贵族的申请。他的侄子刚掌权,沃尔讷就被封为贵族。两年后,1788年7月3日,腓特烈-威廉二世解除了开明的普鲁士宫廷国务大臣冯·策德利茨男爵的职务,任命约翰·克里斯托夫·冯·沃尔讷为枢密院国务大臣和司法大臣、“宗教事务部首脑”。沃尔讷和他的手下们已急不可耐,仅仅6天以后,7月9日,沃尔讷的《关于普鲁士国家的宗教状况的谕令》就正式生效,下令新教的任何牧师、传道士和学校教师都不得传播那些败坏道德、已被驳倒的谬论,违者必将予以严惩。“有些人竟敢大胆放肆、厚颜无耻地冒用启蒙运动的名义,在人民中间传播这些谬论。”这起初似乎并没有给柏林的自由思想者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在围绕宗教谕令进行的争论中所使用的武器,就是采取严格的书报检查措施。1788年12月19日,颁布了“普鲁士国家新的书报检查令”,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家的书报检查,就是要查禁那些反对由国王和教会颁发的宗教和国家的基本原理的言论。1791年5月14日,第三个反对启蒙运动的斗争手段是,柏林最高教会监理会成立了一个独立检查委员会,由它决定哪些神学院毕业生能得到教会职位,哪些书籍能够在普鲁士出版。沃尔讷的追随者们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一名传道士和一位教义问答手册的作者外,中学教师、视灵者哥特洛布·弗里德里希·希尔默和神父赫尔曼·丹尼尔·赫尔梅斯取得了这个书报检查机构中的要害职位。这个由腓特烈二世任命的自由思想者公务人员组成的自由主义的最高教会监理会终于寿终正寝。
自1791年起,希尔默和赫尔梅斯任普鲁士最高书报检查官。1791年10月19日,通过内阁令,他们将杂志、报纸和不定期出版物也纳入他们的检查范围。于是,《柏林月刊》首当其冲。正如该刊编者约翰·埃里希·比斯特后来在其《自传》中所说的,这家杂志首先成了沃尔讷大臣的眼中钉:“这位大臣对编者本人说:他的杂志有伤风化,因此他已经没有希望成为赫茨贝格伯爵举荐的科学院院士。”在这种文化政治氛围中,晚年的康德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沃尔讷也许对康德的《论一切哲学无以圆释神正论》一文已经感到不满。该文发表于1791年《柏林月刊》9月号。几年后,当比斯特徒劳地试图拉拢著名的康德一起制造舆论,批判沃尔讷的政策时,康德终于表明了立场。他的文章的宗教政治背景表露无遗。康德选择的是他几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二重性主题:如果说存在仁慈和睿智的造物主,那么,怎么可能存在道德的邪恶?如果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面临被犯罪和邪恶征服的危险,那么,怎么可能存在上帝?这个早为人知的“约伯问题”首先由莱布尼茨做了现实主义的解读,他的《上帝之仁慈、人类之自由及恶之起源的神正论论文集》1720年用德语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逐字借用了莱布尼茨的概念(“上帝”,希腊语“theos”;“法”,希腊语“dike”),并一开始就将上帝的仁慈和现实存在的邪恶之间的复杂关系理解为“司法行为”,事关起诉和辩护。但是,根据康德的看法,无论宗教信仰,还是神学教条都不能对这场法律诉讼作出理性的判决,必须由“理性的法庭”对它进行批判的检验。康德一步一步地、一个论证接一个论证地进行了明察秋毫的检验。他再一次举例阐释了他的解决方案。正如人们在康德早期的道德哲学著作中已经看到的,在那个“诚实的人”身上,现在出现了约伯的影子,约伯的痛苦促使他进行“尽管如此”的沉思。
《旧约全书·约伯记》记录的是一场“争论”。因为,约伯是一个善良、虔诚和敬畏上帝的人,他不行恶,但尽管如此还是遭受了最不幸的厄运和最可怕的疾病;他的朋友们似乎试图安慰他。于是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争论,双方在争论中都表明了各自的神正论和思想。按照康德的现实主义解释,约伯的朋友们的态度,就像宗教法庭或“最高教会监理会”的“独断主义神学家”一样,因为公正的上帝惩罚一切有罪之人的罪行,所以约伯必定是有罪的。可见,这些自以为深谙上帝裁决的宗教谄媚者们就先入为主地作出了他们的判决。相反,约伯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自己勇气的来源。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罪的,过的是讨上帝喜欢的日子,而且对这种生活也没有任何不甘,所以他不能同意朋友们的说法。相反,他不知道自己这么一个诚实的人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多苦难。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意志造成的,上帝即意志。“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这场争论中,康德完全站在约伯的一边。约伯那些控诉自己的朋友都自称知道他们不能知道的东西,而约伯却勇敢地承认对上帝的意志不甚寥寥,并觉得他的痛苦就是对他道德上的诚实的检验。因此,他反对任何宗教的肯定性和神学的独断论,就证明了他“心灵的诚实”,同时也说明这种诚实面对神正论时,“我们的理性是多么无能”。谈到司法行为这个问题时,康德对约伯的问题作出了革命性的裁决:“他以这种思想意识证明,他不是将道德建立在信仰之上,而是将信仰建立在道德之上:在这个案子中,尽管他孤立无援,但他却唯一具有真诚和实在的特点,也就是说,他具有这样的特点:确立了善良生活品行的宗教,而不是献媚争宠的宗教。”这种反叛性的攻击矛头已经直指沃尔讷及其持信仰独断论观点的书报检查官。康德将自己的道德沉思解释为善行的基础,而他们必定会在约伯的朋友们扮演的无耻角色—只能装腔作势地维护宗教问题,伪善地对自己想象中的上帝顶礼膜拜—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康德在给1791年《柏林月刊》所写的《神正论》一文中虽然为符合自己的性格和道德哲学信念的、世俗化的“善良生活品行的宗教”辩护,但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个问题自1785年《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出版以来,就像一个互补性的对照物一样伴随着道德上的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与堕落的生活品行、恶的意向,即“道德上的恶”是什么关系?没有这种恶,善难道是不能设想的吗?康德一直没有轻易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康德相信,每个人都在共同思考感性和理性、他律地体验到的爱好和自律地希望的道德法则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自然的辩证法”中,实践哲学提供了帮助,并为人们指明了能够拯救因这种二重性而“导致丧失一切道德原则”的危险的道路。可见,这些角色有了明确的分配。在理性者的概念世界,人是自由的、自律的,道德上也是善的。而由于他的感觉爱好和自然欲望,他变成不自由的、他律的,道德上也是恶的。甚至“最无耻的恶棍”也是受了“感性领域的欲望”的诱惑而行恶,他们只要使用自己的理性就能意识到自己的善良意志。
但是,如果不是感性欲望诱使人们行恶,而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恶,那又会怎么样呢?康德自己也不否认,人们完全有可能按照那些他们不愿意将其作为普遍立法基础的准则行事。他们完全自由地、不靠他人的引导就决定行恶。这种邪恶意志的自律值得反思。康德的主要伦理学著作研究了善的道德准则和客观的道德法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他自1792年起主要研究人们可能故意规避绝对命令的道德因素。
康德计划,作为宗教哲学家为《柏林月刊》撰写一组文章,以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他设定的重点非常明确。与宗教信仰相比,良好生活品行的活跃思想具有绝对优先权。但是,如果说宗教起源于道德(康德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只有道德哲学才能提供批判地研究信仰学说的基础。1792年,康德开始在实践理性的法庭上审判自然宗教和基督教信仰。2月,他将《论人类本性中的极恶》寄给比斯特。不过,现在所说的“本性中的极恶”不再指人的自然冲动和感性欲望,而是只指人在行善或行恶时使用自由的主观原因。这是康德试图用以解决道德上的恶这个问题的新思想,因为只有人才享有遵循善的准则或恶的准则的自由,他既不像动物那样凭本能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也不像上帝那样凭绝对的善在超验中逗留。“人性本善,或者说,性本恶。这无非意味着:他拥有接受善(对我们来说不可琢磨的)或接受恶(违法的)的准则的第一因。”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人类自决的一种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说为恶的习气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人类在道德意义上是什么样,或应该成为什么样,为善或为恶,这必定是他自己正在或已经造成。”可见,在诱惑性的本能驱动和纯粹的善良意志之间已经不存在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人类意志活动的自律为基础的。道德上的恶是“彻底的”,因为它败坏了一切德行的根源,同时又符合人这种活的、理性的、有责任能力的存在物的生存。说得尖刻一点,一方面,防止恶行的不仅有理性,而且还有人行恶的前提;另一方面,人类道德上能够行善,“这不是因为他有理性,而是因为他不仅有理性”。
书报检查官希尔默还是让这篇文章通过了检查。1792年4月,康德的文章在《柏林月刊》上发表。相反,下一篇文章《论善的原则同恶的原则为统治人而进行的斗争》却没有获准发表。7月18日,比斯特写信给康德说,他非常生气,“一个希尔默或赫尔梅斯竟能规定世人应该还是不应该阅读康德。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做”。他干预书报检查官们的工作,甚至还给国王本人写信。他的抗议按照宗教谕令的说法,以没有根据为由被拒绝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康德决定,将他原计划为《柏林月刊》撰写的4篇文章作为一本独立的书出版。然而,他为此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首先,他让柯尼斯堡大学神学系出具证明,说明这样的著作应该由哲学系进行审查。然后他将著作交给耶拿的萨克森—魏玛大学的哲学系,得到该系的批准后,还得在普鲁士境外印刷。《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伊曼努尔·康德著—于1793年复活节出版。
康德的这部宗教学著作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高潮。任何其他一部著作都没有如此清楚地表明,启蒙运动的批判性任务是什么。康德以他的智力、道德意识和源自苏格拉底的不可知论,即上帝的存在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转而批判基督教的信仰学说。康德在这部著作中是最后一次使用那个他在与视灵者斯威登伯格争论中,为了解释理智的使用,曾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过的比喻。如果说他今天是在哲学上研究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那么,他的重点不在于“从纯粹理性(无须启示)”中推导出宗教。有人说,宗教学说出自“超自然的、得到神灵启示的人之手”,是从事实上说明上帝的无法理解的超验性,康德虽然认为这种说法不能肯定,但也认为是可能的。康德只是想说明,并在哲学上验证,“也能通过纯粹理性认识得到启示的、已经信仰的宗教,即圣经文本中的内容”。这就是引导现代宗教批判话语权,反对任何假想的原教旨主义的革命转折。圣经不是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守的神圣教义,它是一本衡量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标准的书。因此康德论述了(1)“极恶”方面的原罪学说;(2)善的原则和恶的原则之间的斗争方面的救世观念;(3)教会,信仰机构,他称之为德行团体的教会;(4)宗教仪式(如祈祷、做礼拜、牺牲、苦行和朝圣),他以挑衅性的、用斜体字母印刷的基本原理要求这些仪式掌握分寸:“除了善良的生活品行之外,所有人们自以为能博得上帝欢心的说法,都是纯粹的宗教幻想和歪理邪说。”根据这条准则,任何牧师制度也都不过是教会的安排,“在这种教会中拜物教仪式占统治地位,而拜物教仪式随处可见,在那里,构成牧师制度的基础和基本内容的,不是道德原则,而是清规戒律、信仰规则和各种教规”。
在该书第一版《前言》中,康德强调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使他有权和有理由构建批判性宗教哲学和道德神学。首先,他为那些只会使启蒙运动的任务得以完成的公开性再次进行坚决的辩护。1784年的公开性纲领具有的现实意义,就是直接反对普鲁士国家的宗教法令和书报检查令。那些关心拯救本教区成员的灵魂的神职人员,虽然服从那些他们不可侵犯的教会规定,但是他们作为在公众面前公开使用其从科学中学到的理智的学者和进行哲学思考的神学家,就必须享有完全的自由。书报检查机关不得在科学领域制造任何麻烦。其次,康德再次强调了他在对约伯问题的解释中已经阐述的思想:道德优先。在道德的基础上,信仰才能发展。只有这样,信仰才能最终发展成真正的虔敬,而这种虔敬不会在仪式化的歪理邪说中变得僵化。相反,如果宗教优先于道德,那么,宗教就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就会被信仰独裁者们当做国家政权的工具加以使用。
毫无疑问,70岁的康德挑起了与书报检查机关的冲突。一段时间以前,他就已经意识到,柏林的宗教法庭将要采用一切手段反对他的学说,甚至要禁止他公开发表任何东西。国王本人也打算终止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的活动。康德发表于1794年《柏林月刊》6月号上的《一切事物的终结》一文为此提供了最终的口实。康德首先讥讽性地解释了诸如永恒、世界末日、末日审判和永久宁静等“终极事物”这种独断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学说,然后,在文章结尾转而攻击新的宗教政治课程的愚蠢。如果基督教作为全民宗教由权威和戒律来维持,那么,它最终必将丧失“道德亲和力”。一旦走到这一步,那么,“那些本来就被视为世界末日的先驱者的反基督教者就会开始他们(可能以恐惧和自私为基础的)虽然短暂的统治。”这里指的是谁,每个读者想必都是清楚的。柏林的基督教信仰独裁者就是反基督教者!在他们的统治下,道德方面的一切事物都将终结。
书报检查当局必定要采取行动,首先是因为读者已经对康德的《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产生极大的兴趣,而该书于1794年复活节已经出版增订第二版。康德早在1793年5月4日给哥廷根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司徒林教授的信中就已经预言说,“教廷的云雾笼罩下的绝罚”是不可避免的。1794年10月1日,一份内阁令以“王室批复”的形式下达给康德,他于10月12日收到批复。沃尔讷“根据最仁慈的陛下的特别命令”规定,康德今后不得在宗教问题上犯任何错误。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国王和他已经极其厌恶地发现,康德“滥用哲学,篡改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和基本教义”。这是不负责的,而且“违反了你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君王的意图”。他在作了这个提醒以后,就进行直言不讳的威胁:“我们要求尽快看到你们认真负责,并且希望你们不要强迫我们采取极不仁慈的措施,将来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而是要尽到你们的义务,运用你们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君王的意图不断得到实现;如果你们继续执迷不悟,那等待你们的肯定将是令人难堪的命令。对你们已经够仁慈的了。”
四年后,他将自己的答函同国王的特别命令一起在《学科之争》的前言中公之于众。这份答函表明,老年康德对争论的兴致有增无减,而且具有极强的责任意识。他没有将国王的命令看做必须绝对服从的命令,而是看做他进行自卫而必须驳斥的指控。康德绝对没有打算放弃启蒙运动的准则,作为学者他只服从科学理性的规则。在批判地检验宗教的过程中,他只遵循这些规则。他虽然“极为尊重基督教圣经的信仰学说”,但条件是,这种学说要和最纯粹的道德理性信仰相一致,并且适宜于“建立并维持一种确实能净化灵魂的国家宗教”。康德再次强调了他心目中的优先权。启示录和历史流传下来的论据知识是“偶然的”,对于真诚和严肃的虔敬并不重要。因为只有实践理性和它的道德准则才能导致形成信仰学说的普遍性、统一性和必然性,“信仰学说构成一般宗教的基本内容,而这些基本内容存在于道德实践(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中。”唯有居于我内心中我自己制定的道德法则才是信仰的源泉,信仰只有从这种源泉中才能获得它的力量和尊严。至于王国内阁令对他提出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他以轻松调侃的口吻进行了驳斥:“我已经71岁了,为什么思想还很容易升华,这很可能是因为不久之后,我作为一个心灵倾诉者必须在世界法官面前对这一切作出总结,这是我的学说目前要求我履行的责任,我会极为认真地撰写这个总结并真诚地提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