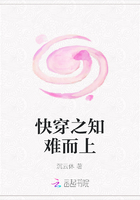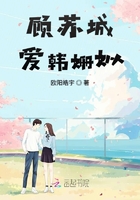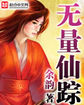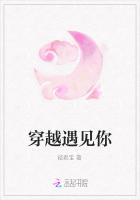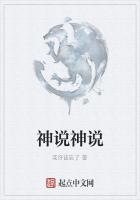康德迈出那些大胆的步伐是需要时间的,他一步一步缓慢地、起初是几乎无意识地摆脱了人类行为的可感觉的现象及能够感受到善的单纯情感,以便能够向纯粹的道德法则稳步过渡。康德的伦理学将人从那个熟悉的世界请出来,让他们进入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和“一种与决定性原因完全不同的关系”。
倒叙。柏林皇家科学院1763年的有奖征文活动使康德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也能像几何学真理一样得到明确的证明吗?如果不能得到证明,那么,怎么能有肯定性和说服力呢?为了赶上1762年12月31日这个截止日期,康德奋笔疾书,许多东西只是一带而过。当然倾向性非常明确,那就是打算进行一场道德哲学的革命。为了解决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概念的说明和分析。因为首先由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于1720年在《德国伦理学》中提出的实践哲学,还远远没有“提供为证明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所必需的明确性和可靠性”。人们只有了解了“义务”这个核心概念,才能看到普遍存在的模糊性。沃尔夫将职责定义为“我们有义务完成的”行为。每个法则都是义务。人们应该有义务做这或做那!但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
正如康德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所证明的,这个概念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我应该”一方面涉及我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明智的命令,命令你去巧妙地选择手段。比如,我在学校里应该勤奋学习,争取或得到好成绩;我应该体育锻炼,以便保持身体健康;我应该勤俭节约,以便能够缴纳税款。但是从中推导不出行为的真正的道德义务。另外一方面,“我应该”也可以直接指向目标。唯有这样,这个命令才有道德的分量。这个“我应该”,在绝对表达道德的第一因和“全部义务的直接的最高规则”时,必须以目的本身的必然性为取向。但什么东西一定能够作为“我应该”的必然目标,使义务具有道德内涵呢?
所有这一切都还非常抽象。可是康德已经以他的回答隐隐叙述了他后来在伦理学中将要阐述并进行直观论证的基本思想。“而我现在只能向少数人指出:我对这个问题作了长期思考以后,已经确信,把你能做的事情做得最完美这个规则就是全部义务的第一个形式上的根据。”康德的《关于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明确性之研究》虽然没有获得一等奖,一等奖1763年5月31日由门德尔松摘取。这部著作1764年由科学院出版,科学院的评价是,这部著作与一等奖作品“难分伯仲”。
1763年,康德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每一种义务的“应该”的“第一个形式上的根据”。为此他调动了感情的因素。每个人都能直接感觉到,什么是善。人的道德直觉就表明了科学院所询问的那种证明性。他1764年发表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一文证明,康德那时向感情的转变是与自己的个性和性格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篇文章是他在孤寂的莫蒂滕森林中,在他寒暑假常去的护林员沃布瑟尔的小屋子里写成的。这里非常安静,他可以首先弄清感情的问题并找到一种描写感情的新形式。总之,这篇文章让人认识了一位对人的特点观察细致入微、描述丝丝入扣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善于分析、富有思想的自然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者,而且他还能敏锐地洞察人的内心世界的错误和混乱。他仔细观察各色人等在面对复杂多样的事物时所产生的不同感受。为什么一个人感觉是享受的东西,另一个人会感觉恶心?为什么有些事情能让一个人感动,而让其他人捧腹大笑或无动于衷?“观察人的本性的特点这个领域非常广阔,而且还有诙谐风趣而富有教益的宝库等待发现。”
首先,他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和《试论大脑的疾病》表明,40岁时的康德是人的行为和精神生活的极其敏感的分析家。我们可以感觉到卢梭对康德的影响,康德1762年开始阅读卢梭的著作。年轻的大学生康德曾经接受牛顿的自然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并在《天体理论》中第一次达到顶点。从卢梭那里他学会了重新审视人。特别是卢梭的悖论有助于他观察人的灵魂的隐秘角落。人的本性和文明社会之间、自然的人和带着面具的同时代人之间看似不可解决的矛盾也感染了康德。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阴谋和虚伪的手段”已经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准则,并且使人的行为变得极为复杂。与无赖和骗子相比,“好人”被视为幼稚的傻瓜。
可是,卢梭不仅让他看到了人的各种弱点(康德也善于找出这些弱点的有趣的方面),还完全唤醒了他对人的实践他的认识兴趣。1765年,他在1764年出版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的页边空白处写道,以前,他喜欢研究的倾向差一点把他引向蔑视人类的骄傲自大的歧路,他把一切都押在对物理世界的认识上。“那时,我以为这一切就能构成人类的荣誉,我瞧不起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下层民众。卢梭及时救了我,那种盲目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敬人。”康德不想再像独眼巨人那样只满足自己对世界事实的理论兴趣。卢梭给他安上了第二只眼睛,以便让他观察和认识人的生活的实际的深层次层面。
如果说康德像哈曼所说的那样,在1764年就已经“满脑子道德”,那么,首先也是以原理或准则这个决定人的愿望和行动的主观原则的形态出现的。对他来说,关键一开始就在于主观特性的经验心理学。康德《观察》的目标就是道德原则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性格,不管是体现在好人还是坏人身上。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心境与“出于原则的真正德行”密切相关,康德认为德行是高贵的、值得尊敬的,它不同于爽朗活泼的乐天派,一味地变着法子找乐。显然,康德的性格喜欢让自己的感受和情感服从原理。
康德用了20年的时间为按照准则生活的各种崇高品质,寻找道德论据。他觉得光有经验的精神学说还不够。最后,他在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发现了道德形而上学。早在1765年12月31日,康德就在给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柏林科学院院士约翰·亨利希·兰贝特的信中说,终于到时候了,可以抨击“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无休止的打情骂俏和现在那些蹩脚的著作家们喋喋不休的饶舌”,澄清形而上学的独特方法,并由此开始人们期待已久的“自然科学的革命”了。他说他已经为此写好了草稿,“其中《自然的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的初始原因》和《实践的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的初始原因》将是第一批著作”。这些著作都没有出版。也许康德自己还没有把握,一方面是经验地研究人的实际行为,另一方面是形而上学地论证迫使人从本性转向道德原则的东西,这二者怎么融会贯通。5年之后,即1770年9月2日,他就这方面的问题告诉兰贝特,他现在终于找到了那个也能应用于广大道德领域的形而上学概念。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康德写道,他打算尝试“整理和完成有关纯粹道德的世俗智慧的研究,其中不掺杂一点经验原则,暂且就叫道德形而上学吧。”
1770年前后,康德终于明白,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必须超越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这个范围,才能找到“初始原因”;它不能局限于只作诙谐风趣而富有教益的发现;而且它也不能停留在准则上,因为准则只不过是各个主体的意愿和行为的主观原则。康德身为道德形而上学者,试图静下心来透彻地思考“道德法则”,因为这是经验现象不起任何作用的整个道德的最高原则。
可是,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得需要10多年的时间。因为康德于1770年3月31日由王室内阁令任命他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他提出的伦理学教授职位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其他事情也非常多。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用了10年时间,他在这部著作中只能简单叙述实践哲学,而着重论述了经验形而上学和幻象的辩证逻辑学。只有在完成对纯粹理论理性的分析之后,康德才能再次转向他的真正使命—实践理性的研究。
1785年4月8日,他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终于面世,并很快在他的朋友中传阅。康德4月9日星期六到希波尔市长家里“参加了一场盛宴”,同时送给市长一本作为礼物。第二天,市长把这本书借给哈曼阅读。哈曼在4月14日给他的“最贴心的朋友”魏玛的赫尔德的信中写道:“这本书我用几个小时就看完了—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当天我就把它还回去了。”他继续写道:“书中没有论及纯粹理性,而是阐述了另外一种幻影和偶像—善良意志。康德是我们当中最具洞察力的人,这一点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但遗憾的是,这种洞察力使他着了魔。”
哈曼1785年4月22日给军事顾问舍弗奈尔的信,语气比较友好,在拜访了希波尔,并且在他家里“很遗憾,大大地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像圣约翰那样在这一天既不吃也不喝—之后,他去了康德那里。这一天是康德的61岁生日。在康德那里,他“无偿得到了一本《基础》,这让我感到受宠若惊,高兴不已,虽然不是完全受之有愧,却完全超出我的意料”。3个星期之后,5月12日,哈曼又给舍弗奈尔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从康德那里得到的《基础》。他在信中说,自己想再认真地读一遍,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看懂。“纯粹理性和善良意志对我来说还是单词,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它们的含义,而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因此我得耐心地慢慢揭开这些秘密。”
正如哈曼在《关于理性的纯语主义的元批判》中和对康德的启蒙构想提出的指责中所说的那样,指出了康德伦理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今天仍像1785年一样争论不休。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似乎将这个世界一撕两瓣,从此再也不能弥合。“道德领域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一直是人们反对康德的道德观念的理由。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康德的道德观念也仅仅是常人的理智不能理解的哲学抽象;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是一种与生活毫无关系的纯粹的捏造。特别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指责康德的道德概念是空洞的偶像,是“柯尼斯堡这个古板的人表达自己的失败和苟延残喘的幻觉。……生命的本性所强制的行为都乐于证明是正当的行为:而那位虚无主义者用基督教教义的‘内脏’将欢乐理解为异议”。有人说,康德只不过是热衷于空洞、纯粹的形式,是一个畸形的概念低能儿。因此这种指责并不新鲜,只不过人们总喜欢提出这种指责:“道德理性是由感性的排他性能力构成的。这种招法在各种幻想体系中是屡见不鲜的。”
康德《基础》一书的“前言”想必就已经深深刺激了哈曼。因为康德在“前言”中明确区分了经验和纯洁性。在实际生活中,各种不成规矩的行为方式和模糊不清的信念起着重要作用。康德并不否认,实践哲学也可以涉及经验现象;甚至也不否认,人的意志也“受到自然的影响”。人的意志毕竟不能摆脱人的具有感觉、欲望和兴趣的躯体。不同的秉性发挥着经验的灵魂学说可以研究的作用,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能低估。康德完全承认,伦理学也有他称之为“实践人类学”的经验的成分。实践人类学研究感性、快乐和不快的情感、情绪和激情,还有人的性格。可是,康德认为纯粹道德哲学也是可能的,是值得研究的。正是在一个道德普遍堕落的时代,他认为值得尝试纯粹地、实事求是地挖掘道德法则。但是,在这方面,只能是“可能的纯粹意志”的观念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道德形而上学,同时也是纯粹的“善良意志”,因为这里的关键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