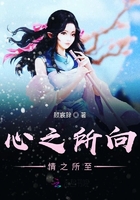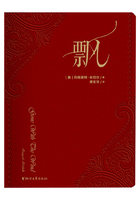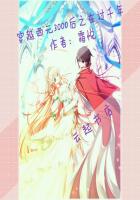在马丁·克努岑的启发下,康德发现了牛顿的宇宙大厦,并且将之扩展成在当时来说十分惊人的想象。他自信地谈论自己的成就,并且将自己的大胆行动当做创造世界者“我”的行动。他头顶的星空唤起了他孩提时的好奇,而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重叠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星系连着另一个星系的无法测量的大世界,它们在无限的时间中周期性地毁灭和重生。康德引入“上帝”,作为混沌的原始物质及其内在固有的力的第一因,这些力作用的结果是宇宙碎形的自我安排。有了这个上帝,康德不仅摆脱了他是无神论者的骂名,而且也使自己面对头顶星空时的极度兴奋上升到了宗教的层面。
康德曾反复谈到内心的“敬畏”、高度的“尊重”、“真正幸福的享受”,或深深的“钦佩”。这种心理使他的情感始终处于亢奋状态,结果产生了那些超越一切经验上可把握的现实的观念。灵魂深处的所有这些谓项的宗教声音是听不见的,但它仍然与主项相关。康德的情感总是充满敬畏和钦佩,这是由于对星空的观察,而不是由于受到顶礼膜拜的上帝。说到天体,关键在于人。自然哲学著作《天体理论》在结束的时候将对上帝和世界的关注转向了对一切事物的中心—灵魂的关注。30多年后,1788年在《实践理性批判》著名的结论中,康德再次想起了这一点,这个结论最后也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反复地加以思索,
它们就越是给人心灌输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
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不愿在他的“视野以外”探索天空,或者超越这些天象提出单纯的假设。他观察“头顶的星空”,并且将之“与自己的存在意识直接”相联系。他自己的此在,他的经验能力和认识能力,他作为人的存在的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康德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的能力方面也作出了无神论的论证,这说明了他的宇宙论研究的特点。作为肉体的生物,他认为自己是渺小的,不能将自己作为灵魂的存在提高到无限。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结尾得出结论说,“只要看一眼多得数不胜数的世界,作为一个动物性的人的重要性就仿佛荡然无存,这个动物性的人在短期内(不知怎样)被赋予生命力以后,又不得不把它所由以造成的那些物质还给它所在的那个行星(宇宙中的一个点)”。因此,他又一次表达了那个他在早期宇宙学研究中已经独创性地解决了的矛盾。这就是尘世的有限与宇宙的无限、肉体的短暂与灵魂的不朽、感觉经验与精神的认识能力之间的矛盾。《天体理论》的第三部分就是首先论述这个问题,而且描述了“各星球的居民”和“未来生活中的事情”以及贯穿康德生平事业的主题—对崇高的审美感。
地球以外的生物。哥白尼革命的结果是宇宙大厦的重构,而要重构宇宙大厦,人就必须进行非比寻常的自我贬低。由于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的失败,人似乎也变得微不足道了。人在无尽的宇宙中只占据一个渺小的、非中心的地位。人面临跌入“一个真正无法测度的深渊”的危险。布莱茨·帕斯卡尔死后于1670年出版的《思想录》中记录了他面对宇宙的无尽空间和客观冷漠所突然感到的“恐惧”。人似乎在任意一个点上迷途了,在冰冷而空洞的宇宙中感到孤独。
追寻古老的旧观念有助于抗拒这种恐惧。德谟克利特已经用人类生存的无数的世界填满了他的宇宙的虚空。上帝创世的神话没有迫使他承认地球是唯一的家园。18世纪,人们再次发现了世界的众多,当然前提不一样。人类不是独自居住在这个无尽的宇宙大厦中,因为不可理解的是,说上帝独自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的这个离心点上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被驱逐出宇宙的中心点,到恒星定居作为补偿。1686年,牛顿将其数学原理运用于对宇宙体系的力学解释,同年,极为畅销的《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一个女人和一个学者之间关于不止存在一个世界的谈话》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风度翩翩的启蒙思想家贝尔纳·布维·丰特奈尔充满想象地描绘了新的日心说宇宙观,并将其他星球上的居民生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1698年,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在《已发现的天上的世界》第一卷中描绘了各星球居民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特性和活动,甚至详尽地对细节加以说明。他甚至还认为,这些居民也搞天文学研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于1726年撰写了《对自然事物的意图的理性思考》,认为地球和行星的目的在于被居住,因为只有这样,上帝才能到处实现他的完美的启示。这里还必须提到亚历山大·蒲柏。蒲柏是康德最喜欢的著作家之一,康德喜欢引用他1740年出版的形而上学诗集《论人》(1733年)的德译文。全部宇宙在感觉和观念上虽然是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我们的家园,因为一个又一个的世界上居住着与人类相似的生物:
谁能看透遥不可及的距离,
一个又一个世界是怎样构成宇宙的,
一个星系是怎样转向另一个星系的,
一个个行星是如何追随太阳的,
每一个恒星都充满着何等繁多的生命,
我们也许能够揭穿天体的计划。
康德感觉指的是他自己,他实现了蒲柏的愿望。他透过一望无垠的宇宙,观察到“一个又一个世界是怎样构成宇宙的,一个星系是怎样转向另一个星系的”。他设想了在遥远的恒星和行星上生活的不同居民的情景。康德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甚至还能设想没有生命的、由于无限的空间而产生重力作用的虚空而荒芜的天体的存在。但对于他的同时代人所确信的东西,他丝毫也不怀疑。“然而,绝大多数行星上肯定有居民,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
也许是瑞典博物学家伊曼努尔·斯威登伯格启发了康德,使他在拜访其他星球的居民时多少“放任”幻想。因为斯威登伯格不仅在1734年出版的《自然界的原则》第一卷中设计了与康德的混沌理论极为相似的宇宙形成模型,而且后来还同遥远的恒星上的居民的神灵建立了假想联系,并对他们作了相互比较。在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们那里仅仅是假设的事情,据说斯威登伯格都有亲身体验。他梦游般旅行了太阳系,拜访了遥远的神灵。这些神灵不仅具有人的模样,而且一起构成了至人,宇宙中的万能人。
康德远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虽然后来以他的名字发表过有关亡灵在冥府旅游的报告:《关于我在太空旅行的真实报道,伊曼努尔·康德撰》。在报告中,他警告身后的追随者:“不要沉湎于我们对彼岸的希望这种幻想,谨防对希腊人的研究”。他停留在地球上,并且将人视为他思考问题的一般出发点。他从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出发,推断出地球以外的生物在肉体、精神和灵魂方面的可能的特点。他推测了不同星球上居民的共性和差异,同时以“自然关系的主线”为指导。
由于宇宙空间的引力作用,行星同它们所环绕的中心星体之间的距离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康德选择重力作为独立的变量,以便对宇宙居民不同状况作出比较和分类。他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出发,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一般来说,不同的行星距离太阳越远,构成其居民乃至动物和植物的物质就必定越轻巧、越精细,纤维的弹性连同其肌体的优越配置就越完善。”在这种自然的关系中,轻巧度、精细度和弹力都同行星与太阳的距离成正比地提高,这种自然关系不仅同物质的身体有关,而且同与身体有关的精神能力和灵魂质量有关。康德对精神能力作了一种宇宙唯物论的解释。重力增加,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惰性也会增加;感觉动力越来越强,精神的灵活性和弹性就会消失,而灵魂也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和无力。相反,生活在天空最上界内心充满喜悦的生物一定很优秀,他们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
康德认为他的一般思考虽然可信,但不可靠。不管怎样,他的思考开辟了“一个从不同居民特性的比较出发作出适当猜想的广阔领域”。首先,人的本性可以从宇宙论的角度去考察,因为,人的本性在我们的太阳系占据中间的位置,仿佛处于接近太阳的行星的完全重力和惰性与远离太阳的天体的运动的灵巧之间的中间横木之上。人是生活于中间行星上的中间生物。就像康德所思考的那样,人的道德状况及其特点也许也可以这样理解。他认为,在迟钝的无理性和思想的明晰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在那里美德和罪孽混合在一起。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因为他处于“危险的中间道路”,在这里,他的犯罪的能力处处都伴随着他,不过他的道德意识并没有完全丧失。
灵魂转世。康德自己曾考虑过,他穿越天体的冒险旅行可能会陷于偏离理性信仰轨道的危险。他知道,他在大胆地提出人的道德能力、犯罪和遵循美德的能力是否也取决于牛顿精密计算的万有引力这个问题时,会放纵自己驰骋于幻想天地。可是,如何限定一个人想由此提高自己认识的道路呢?“谁能够给我们指出持之有据的可能性终结而任意的虚构开始的界限?”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我们对人这个灵魂存在物的真实了解:只要人活着,他实际是什么样的。在我们思考人的本质的时候,在智慧和无理性的宇宙中间状态不存在最终明确的解释。“至于人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更无法猜测了。”这说的不是人类的未来,而是人在肉体丧失生命力以后其灵魂的命运。康德以一种想象作为他的《天体理论》的结尾,对于这个想象,他不要求科学上可信,而是要表达一种希望。康德作为按照牛顿的数学原理和哲学原理为指导的自然哲学家,设计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并且在想象中一直深入到遥远的时空。但作为一位灵魂的形而上学者,他在梦幻中漫游,将自己带向了作为研究人员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地方。他使灵魂脱离地球,以便让它们能够接近宇宙天体。“谁知道,能不能设想人类灵魂有朝一日可能切近地认识从远处就如此吸引着其好奇心的世界大厦那些遥远星球及其美妙部署。”因此,康德似乎首先让灵魂移居宇宙,以便能够真正认识他青年时期就喜爱的自然哲学。正如一次考察旅行一样,他想最终发现他的目光在晴朗的夜晚所搜寻的东西。
崇高的内心喜悦。无穷的宇宙空间看上去像是密集的粉尘,它不仅唤起了康德认识宇宙的兴趣,而且激励他创作《天体理论》。与此同时,他还不时地感受到那种能够上升为伊壁鸠鲁式的“内心喜悦”的享受,这种享受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体验得到,但却无法名状。那么,“不朽的精神的隐秘认识能力就会说出一种无法名状的语言。”在宇宙的精神世界中,精神只使用“一些未展开的概念,这些概念也许只可意会,不能言表”。康德以这种提示结束了他的《天体理论》。不朽的灵魂超越一切有限的、能够明确而清楚地描述的事物,一跃上升到“提高了的物种”,以便在那里找到永恒的幸福。
康德1755年开始追寻的东西,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在他晚期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判断力批判》(1790—1793)中,他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孩提时就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与“美的分析”相反,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崇高的分析”。头顶的星空景象被用作这种崇高分析的直观材料。这种观察没有对科学天文学的好奇,也没有关于天体上是否有理性存在物的思考。如果说天空的景象是“崇高的”,那么只是由于天体的无穷大。天体是“囊括一切的宽广的苍穹”。作为无限的宇宙大厦,天体大得惊人,因此使人产生冷静的赞赏和深深的敬畏,而这种赞赏和敬畏又将人面对宇宙深渊可能产生的恐惧转变为令人喜悦的乐观情绪。
康德要利用“崇高的分析”,在哲学概念上说明令这位年轻的自然哲学家激情涌动的事情。同时,他要阐明在《天体理论》的结尾没有展开的、还非常模糊的思想:整个宇宙大厦在感觉上是无法理解的,是概念的语言无法描述的,对于人的想象力来说,它又是硕大无比的。但是,人如果对无法言说的又不想保持沉默,那么他怎么办呢?康德认为,除了他不太擅长的诗外,他只能作形而上学的自我提升。人作为理智存在物必须意识到自己精神世界的伟大。这个精神世界使人超越一切感官感觉、语言描述以及荒诞的想象,对无限的天体产生纯粹的理性观念,克服人作为地球这个渺小的点上的自然生物所感受到的一切危险和恐惧。对崇高的审美感是主体的感觉,而主体的感觉是由无法把握的数量上的大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自然引起的,而且恰恰带来了主体对自身精神的伟大的领悟。康德在自己关于无限宇宙的宇宙学理性观念中融入了他十分内行的形而上学。
不过,康德在1755年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尽管他十分自豪地阐释他是如何可能将自己创造的混沌变成一个有序的整体。他谈到其他星球上的居民,是为了在宇宙中不感到毫无希望;他谈到灵魂转世,是为了在死后周游遥远的宇宙。当然,这位年轻的充满热情的天体观察家已经认识到,他谈到的精神和神灵、灵魂转世和天上的住所,只是浮现在他眼前的想象力的梦幻般的表象。能够为充满他内心情感的、难以理解的东西找到可靠的根据吗?或者,他也是整天幻想那些子虚乌有的事物的人吗?这就是伊曼努尔·康德在后来几年集中精力研究的问题。他想划清实际知识和梦想、清醒的理智和梦中的愿望、可靠的理性小径和无边无际的幻想领域之间的界限。他选择世俗智者伊萨克·牛顿为他进行宇宙冒险的向导,而当考察“持之有据的可能性终结而任意的虚构开始的界限”时,他以神灵世界最著名的视灵者斯威登伯格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