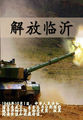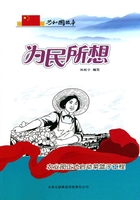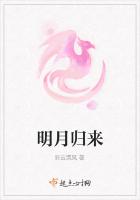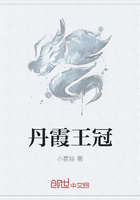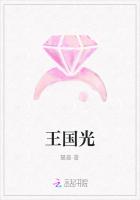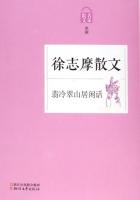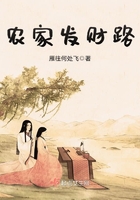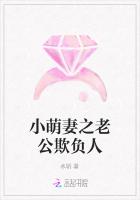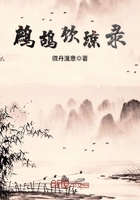因此在一次次政治风暴中,她们手足失措,她们痛苦万分,她们像看到突然倾翻的童车一样,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她们的生命永远是绿色的,她们以自己的爱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构成一片博大的绿荫……
1、女部长告别共和国
张琴秋对纺织工业不算陌生。20年代,她在上海长期从事纺织女工的工运活动。留学莫斯科时,又到附近的纺织厂当过几个月的织布工。也许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建国后,她被派到纺织工业部担任副部长。
身居这样的高位,她依然不改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在机声隆隆、粉尘飞扬的车间,在工人简陋的居室,在工人排队买饭的行列里,都能看到她不知疲倦的身影,听到她爽朗亲切的笑声。在风风雨雨的政治运动中,她力所能及地保护着周围的同志。部里一位副处长林颖是革命烈士彭雪枫的遗孀,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保定化纤厂“劳改。”张琴秋借一次出差机会,特地去看望了林颖。当她径直走进林颖的工作场所,林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惊问,张部长,您找谁?
林颖同志,我还能找谁?我就是特意来看望你的!张琴秋故意提高了声音说。一直被周围冷淡、回避和疏远着的林颖,自此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不久,经张琴秋四处奔走,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颖摘掉“右派”帽子,调回部里工作。
女大同事、50年代曾担任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厂长的郭霁云,也受到张琴秋的多方关照。郭霁云被打成“右倾分子”。张琴秋鞭长莫及,无法保护她,只能通过写信给她一些安慰。经刘少奇干预,摘掉“右倾分子”帽子的郭霁云很难在黑龙江继续工作下去了,经张琴秋力荐,郭霁云调入纺织工业部任化纤工业局副局长。
张琴秋的前夫、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任的陈昌浩在西路军惨败后逃回延安,不久便以养病为名去了苏联,在那里与一位苏联妇女同居,自此他有国不归,一去14年。1943年,年已39岁的张琴秋与小她1岁的苏井观在延安结为伴侣。结婚那天,战友们笑着把一副对联贴到粉刷一新的窑洞门上:“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1952年,陈昌浩与苏联妻子回到中国。在徐向前元帅的家里,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如今低头弯腰,向昔日的属下、今日的将军和部长们一一拱手作揖,表示歉意。他与张琴秋握手时愧疚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经张琴秋向党中央推荐,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陈昌浩与结发之妻生的两个孩子陈祖涛、陈祖泽,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一直受到张琴秋的关心爱护。
张琴秋的妹妹张兰抗战时期英勇牺牲,女儿张克宁流落乡间,生活十分艰难。建国初,张琴秋回乡探亲,把她带回自己家,自此张克宁成了张琴秋的女儿。
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巾帼女杰,中国妇女运功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女将领,“文革”中竟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与折磨,长期被监禁在纺织部大楼。1968年4月21日晚,浑身狼籍、疲惫不堪的张琴秋服了一粒安眠药便上床休息,两位看管人员没有像往常那样锁住她的房门,便回自己的房间了,整个大楼一片漆黑。
第二天清晨,看管人员发现张琴秋住的351号办公室空空如也,人不见了。他们惊慌地大喊大叫,四出寻找,最后,在大楼西侧墙根下的水泥地面上,发现了横卧在那里的张琴秋,身体已经僵硬了。经法医鉴定,张琴秋是自杀,她“侧身下去,右臂先着地,大面积骨折,大骨折已穿出到衣外。”“面部苍白,下侧有红斑,两只手背有红斑,口唇青紫,口腔出血……”
1976年,张琴秋与第一任丈夫沈泽民(中共党员、茅盾之弟)的女儿、出生于莫斯科的张玛娅,因同情天安门“四五”运动,公开表示对周恩来的怀念,被打成“反革命”。因不堪忍受折磨与屈辱,5月17日,她服下大量安眠药而辞世。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长达10年的最黑暗的日子,这对母女显然绝望了。一生饱经忧患的张琴秋、张玛娅母女,先后以自杀的悲惨方式,向“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最后的抗争!
2、最简单的名字:“一”
文漪(原中科院农业机械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出生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的一个孤岛上,她是偷了嫂嫂4块大洋跑到延安的。年轻时的文漪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是个漂亮女孩。后来冯文彬看中了她,百般追求。两人结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冯文彬为革命做出许多贡献,但对妻子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无奈,文漪下决心同冯文彬离了婚。此后她把热情和精力全部献给了共和国的事业,觉得工作是那样的美丽,精神是那样的充实。
女大毕业后,文漪曾在陕北的两个县里当了7年的区长、宣传科长和宣传部长。目睹农民艰辛困苦的生活,她感慨万端,立志要为广大农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奋斗一辈子。在看过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生活的苏联电影之后,她觉得当个拖拉机手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50年代,她和江泽民同志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归国后拖拉机手没当上,倒当了万人大厂天津拖拉机厂的副厂长,一干就是20多年。迈进工厂的第一天,她是拖着两条又黑又亮的辫子出现在同事面前的。她觉出大家都用一种善意而又略带讥讽的眼光瞅她,好像都在暗笑,怎么来了个小辫子当厂长?当天晚上回家,她就把辫子剪掉了。
和平时期,很难遇上什么赴汤蹈火的考验,需要的倒是那种朴实而长久的敬业精神。文漪一辈子没请过病假、事假,没迟到早退过。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厂,先骑自行车全厂转一圈,下班前再转一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科学知识,靠老八路打仗搞战役的那套办法是不行的(建国几十年,我们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来自延安的文漪以可贵的自觉精神,走进大学校园。万人大厂的副厂长,白天的工作千头万绪,晚间揣上两个馒头又匆匆赶到天津大学夜大学,与年轻人坐在一起攻读机械制造系,这太不容易了。因成绩优秀,她又转入天津大学机械系学习,硬是拿下本科毕业证。一次罗瑞卿陪毛泽东到天拖视察,高大魁伟的罗瑞卿瞧着个子矮矮的文漪,笑着说,这么个小女人,竟能当万人大厂的厂长?
毛泽东笑眯眯说,小个子也能办大事,你罗长子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当公安部长的。
“文革”后,文漪调到农机院,成年累月跑农村。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蒸蒸日上,她无比地欣喜。看到那么多地方的人民在建国几十年后,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她热泪盈眶。与农民和农村干部交谈和交朋友时,好些人不认识她那个“漪”字。那么好吧,她把自己的名字顺着谐音改成“文一”。
文漪的二女儿嫁到德国,婆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一生最反对共产党。文漪去会亲家母前,女儿担忧两个老太太吵架,来长途电话暗示妈妈,你要不要说自己是共产党呀?
我当然要说,文漪答。
你到了德国,可不要和人家吵架呀,女儿千叮万嘱。
这事儿你担什么心,共产党人要是到处和人家吵架,不成了孤家寡人么!
在女儿家,在绿荫如盖的庭院里,在草坪如茵的甬道上,来前自学了一年德语的文漪,通过女儿同德国亲家母做了许多次倾谈。她说,你们基督教义要大家行善,目的是为了死后上天堂。共产党人的宗旨也是要行善,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亲家母听了文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工作中的许多故事后,竟对这位经历非凡的中国老共产党员敬佩得五体投地,两人情投意合,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她再三挽留文漪在德国定居。
文漪婉言谢绝了。
3、“正义路上正义难”
丁汾是块“石头”,搬不动、砸不烂的“石头”,硬是让那些以势欺人的家伙不能顺顺当当迈过去。
建国后,丁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了几十年。她最深的感触就是“正义路上正义难”,在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土地上,权与法的较量是那样的激烈、复杂和艰巨。她不能忘记,在1943年的延安,在那场“抢救运动”中,她被打成所谓河南“红旗党特务”,饱尝了被冤屈的滋味。走上检察官的位置,她就发誓这辈子绝不给自己的历史抹一个污点,绝不办一件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