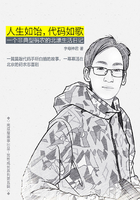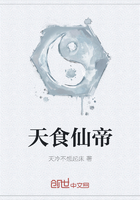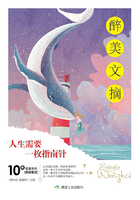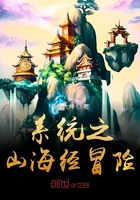只过了两年清白生活,1959年,郭霁云因对“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有看法,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这时44岁的郭霁云已经是屡遭磨难的“老运动员”,不再是延安那个只有热情又充满稚气、一切都那么驯服的小姑娘了。
她死不悔改,拒绝改变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意见。每次有人拿来“反对三面红旗”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结论要她签字,她都一笔一划,严正地在上面写上“不同意”3个大字。
但是,或许是一种疏漏,或许地方官在整人时,因为理亏,不敢把她的事情捅到北京去,郭霁云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幸运地保留了。1962年,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新落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进入灯火辉煌、气氛热烈、有着星空般巨大穹顶的会场,郭霁云的心情很不平静。在黑龙江,不仅她,还有许多同志戴着“右倾”帽子,丧失了为党工作的权利,整个黑龙江几乎是万马齐喑……
她悄悄写了张条子,交给大会工作人员,请他们转交给国家主席刘少奇。上面写道:
少奇同志:
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现在哈尔滨还没有给许多老同志平反,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有关情况,时间请您决定并通知我。
郭靖
她用的是延安时的名字。当初她在女大学习时,刘少奇就很熟悉她,有人甚至还向刚离了婚的少奇同志保媒,说郭霁云如何如何思想纯正,才貌双全。少奇当时就表示,对郭霁云甚有好感。事情回到郭霁云那里,却遭到她的婉言谢绝,她说她当初立过誓言,一定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谈“个人问题”,女大同学们因此送给郭霁云一个绰号叫“马其诺防线”……
一天下午,大会休息时,黑龙江代表团成员、曾在延安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的林纳,跑来找到郭霁云说,主席团有人要见你,好像不是一般人,你快点去吧!
郭霁云的心怦怦直跳,一溜儿小跑到了大会主席团休息室的门口。她站下来定了定神,敲门进去。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坐在沙发上交谈着什么。
一见郭霁云进去,少奇风趣地说,好啊,郭靖同志,你来了,好大的一个“右倾分子”啊!
郭霁云一一向阔别多年的领袖们问了好。
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少奇点燃一支烟,和蔼地问。
过的不太好,郭霁云气鼓鼓地说。
写过什么好文章没有?
刘少奇这句话把郭霁云问糊涂了。她说,没写,写了也没人敢发表啊。
少奇接着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不是说了嘛!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刘少奇的湖南口音很重,说的又是古文。郭霁云被撤职之后,没资格看文件,所以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无所知。加上当时心情的激动,她只能傻呆呆地睁着眼睛,一副茫然不懂的样子。
周恩来笑了,他插嘴说,少奇同志讲的是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引用的司马迁的几句话。主席说,古代也曾错误地处理过一些人,这些人后来大都发愤读书做学问,写出很多好文章。
郭霁云恍然大悟,怪不得少奇刚才问她写了什么好文章没有。她说,我可没古代圣贤那么大的学问,只好读点书来安慰自己。
刘少奇知道郭霁云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他看看手表,对朱德和周恩来说,开会的时间到了,你们去吧,我请假,同郭靖在这里谈谈。
郭霁云好像遇到终于可以倾诉的亲人,一下子整整谈了3个小时!少奇听着,脸色愈来愈沉郁和严峻。他问,黑龙江和哈尔滨一共斗了多少人?
全省我不清楚,哈尔滨大约批斗了70多人,都是老干部,至今没有一个人获得平反。
刘少奇生气地说,看来,庐山会议之后,不应该再在下边开展运动,让你和许多同志受委屈了。放心好了,我会很快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再有什么后遗症,你可以直接给我写信。
大会早已散了。郭霁云乘大会秘书处派的车子回住处,此时,夜幕已经降临,车驶过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望着车窗外灿烂的星空和辉煌灯火,郭霁云心中的愁云一扫而空。她仔细回味着刚才同少奇同志的谈话,她真想兴奋地大喊,想唱歌,又想痛快地放声大哭一场。问题解决得如此好,如此出乎意料地迅速,这是她没想到的。
当天夜里12时许,当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的李范五派秘书把郭霁云找到他下榻的房间。李范五的夫人黎侠也是延安女大的学生,所以两人很熟。
李范五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把我们告了?
郭霁云坦率地直视着李范五的眼睛,我没告你们,只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我不是“右倾分子”。
李范五笑了,他说,告了也不要紧嘛。少奇同志找我谈了,要我们抓紧平反工作,要成批成批地办,不要留尾巴。我已经给省里打了长途电话,要他们赶快落实。他又说,你这一状告得好,替我们省里立了大功,否则还可能拖下去,为什么平反这么难?因为整人的人面子上不好看啊!
此时是1962年。想不到4年之后文革浪潮席卷而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连同整个国家,都陷入更大的灾难。
阎明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天是明朗的天……
阎明诗这样想,许多从延安走来的战士这样想,千千万万迎接新生活的人这样想。她和他们太美好,太纯真,太理想,太透明,又太爱这个无数次梦想过、亲手描画过的共和国了,完全想不到共和国的天空仍会有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更想不到自己也会亲身经历那样深刻和悲怆的惨痛。
像孩子用积木堆成一个美丽斑斓的城堡,阎明诗和她的战友们用生命和爱心建构了这个共和国,那时她和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共和国怎么能给自已的缔造者带来无尽的痛苦呢?
人,领袖,政党,包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很难避免犯错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聪明绝顶的政治家迄今还没找到一种可以完全避免犯错误的决策机制和社会制度。少数服从多数是伟大的民主,而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又是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文明突进的前奏。但历史证明,民主虽然有许多缺欠,但迄今为止是人类创造的缺点最少的制度。
1957年,燥热的夏天,《中国妇女》杂志社的总编室里,气氛相当祥和。几位领导,还有在中国革命历程中著名的“阎家店”中成长起来的阎明诗——那时她是总编室秘书兼群众来信组组长——她们正在研究上面布置下来的反“右派”问题。阎明诗叹口气说,把编辑部的那位大学生定为“右派”,我觉得有点过分,我听了他提的一些意见,都是诚心诚意的,是对党有利的。
领导们也叹气,说我们也没办法呀,上头给了3个“右派”指标,现在还凑不上数呢。
实事求是,没有就没有嘛,阎明诗说。
不行啊,上面天天打电话来催,说这是党性问题立场问题,真把我们难为死了。
在延安女大时,阎明诗就有大姐之风,待人慈祥,吃苦在前,肯干助人,是她一贯的风格。会上,她沉吟一会儿说,“右派”就算我一个吧,反正我不当也得让别人当,革命几十年,这次右就右一下吧,下次再左过来就行了,共产党员总得有黄继光堵枪眼的精神吗!
没想到这辈子她再也没有左过来的机会了。
几位领导与阎明诗同为延安战友,相知很深。想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行啊,就你吧。“阎家店”一窝子共产党,世人皆知,党内同志都很尊敬你一家,谅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阎明诗自愿顶个“右派”的事情就这么轻轻松松议定了。她像往常一样,拿了一叠稿子回家,一直工作到深夜。她家的台灯是那一带居民区有名的长明灯。
黑云遮空,惊雷炸顶!当公开宣布阎明诗为“右派分子”、名字上了《人民日报》,当决定开除她的党籍、行政级别从17级降到21级,又把她像罪犯一样押出群情激昂的会场时,阎明诗目瞪口呆,双泪长流。什么苦处她都能忍,唯有开除她的党籍,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了。走出会场,她一下晕倒在押送人的臂上。她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会是这样严重的后果,一颗赤诚的心被抛在地上辗碎了。
领导们全傻眼了,同为延安女大校友、编辑部领导之一的董边(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夫人),眼瞅着阎明诗踉踉跄跄被拉出会场,她的肠子都悔青了。她们也没想到“反右”会搞得如此惨烈。
父亲阎宝航很难过,对女儿说,运动搞得这么猛,爸爸也无能为力,事已至此,今后就好好改造自己吧。
阎明诗被撵出《中国妇女》编辑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孩子也被撵出幼儿园。那个年代的革命者都是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做母亲的大都把孩子都送到整托幼儿园,20天甚至1个月才让保姆接一次。孩子在家里呆的这一天,母亲也常常不在家,或是去全国各地组稿,或是找作者商谈。在孩子的幼小心灵中,对母亲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现在阎明诗没工作了,孩子也不能继续呆在幼儿园了。当她最后一次走进这里,接孩子出园时,对母亲十分陌生的孩子死死抱住阿姨的腿哭喊,我不跟她走,我不跟她走!
儿不认母亲,党不收这个女儿,这就是她革命几十年的代价么?
阎明诗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农场种地。在延安,在战争年代,她无数次跟老百姓打交道,那鱼水般的亲情始终温暖着她的心。这次,把行李搬进一家农户,她像当年老八路一样,坐在炕头上刚要跟那家的小媳妇拉话,一口唾沫喷到脸上:滚,没人理你,臭右派!
收割庄稼时,对她这个大“右派”也严加管束。在她前头安排一个生产队打头的,干活儿飞快,负责带她。后面跟着一个,负责检查质量。左边安排一个,负责观察她的左脸。右边安排一个,负责观察右脸。只要阎明诗干活的质量稍有问题,或者稍稍流露出疲倦、委屈或不满的表情,这几个人立刻围上来拳打脚踢,嘴里还骂着,臭右派,不好好改造打死你!
3年困难时期,阎明诗为了给孩子节省些口粮,每顿饭只吃那么一点点。一天,她饿得昏倒在垅沟里。那些人以为她跑了,疯了一样到处找,漫山遍野喊,抓坏人啊,坏人跑了!一个小子在庄稼地里到处窜,一下在她身上绊倒了。那家伙大喊,我抓到她了,我抓到她了!村干部们平时本来就吃不饱肚子,又因找阎明诗累得屁滚尿流,憋了一肚子火气。他们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拳打脚踢把这个不老实的“右派”揍了一顿,说她是故意躲在那里的。
几年下来,阎明诗被折磨得枯瘦如柴,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夜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爬上炕,她不能不常常想到延安。延安的日子也是很苦很累的,但她的生命是那样的热烈和昂扬。她忘不了延安女大那个温暖而团结的集体,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有一次行军途中,战士们口渴极了,经过老百姓种植的葡萄园子,望着那紫微微、绿莹莹的葡萄粒儿,大家虽然馋得直咽唾沫,可谁都不伸手摘一个。休息了,大家坐到葡萄架下,抻着脖儿眼巴巴等着葡萄粒儿往下掉。有掉下来的,才你一粒我一粒地分着吃,这还让连排长们一顿臭骂。
她忘不了毕业后,奉命到重庆做地下工作,表面上是艺专的学生,暗地里担任苏联大使馆的译电员和秘密交通员。有一次,她高烧十几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可突然来了紧急任务,要她把一份机密文件迅速送到地下交通站。她勉强支撑着站起来,双腿软得直打哆嗦。父亲担心地说,你要办什么事,我去帮你办吧。她心里暗想,你这个老顽固,党的任务我能交给你去办么?她固执地摇摇头,还是自己去了,一路上几乎是扶着墙走的。建国后她才知道,那时整日周旋于国民党上层的父亲阎宝航,原来就是她的直接领导。那时的革命者,无论怎样苦怎样难怎样危险,都充满昂扬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因为党同人民在一起。但是现在呢,她却成了人民眼中的“坏人”。这种远离人民、远离党的队伍的孤独感,是最令阎明诗感觉痛苦和无奈的事情。
人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心还是善良的。
房东老太太与阎明诗朝夕相处,认定北京城里发配来的这个女“右派”是好人,心疼她了。那天晚上,阎明诗收工回来一进门,忽然一个热烘烘的东西杵到她嘴上。阎明诗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房东的哑吧儿子,手里拿着一大块喷香的熟猪肝,用手比划着让她快吃。
阎明诗紧忙推让。老太太抽着烟袋发话了,让你吃你就吃吧,我家杀猪了,你跟着沾点光也是应该的,一天到晚活计挺累的,补点营养吧。
阎明诗明白了。房东大娘不愧当年是支前的老模范,有经验有道道。让哑吧儿子送东西给她吃,是怕万一被别人发现,谁从哑吧嘴里也问不出啥来。阎明诗接过热乎乎的猪肝,眼泪串珠似地往下落。
后来先后转到鞍山玻璃厂、农机厂劳改。一位老工人苏汉才身子骨弱,常常干着活呢,扑通一声就昏倒在地上。每次,都是阎明诗自告奋勇,风里雨里雪里,用手推车送他到医院去。长街上,人流中,阎明诗吃力地拉着推车缓缓而行,老苏头躺在车板上,瞅着阎明诗弯腰蹬地的背影,感动得不行。“文革”开始了,一帮造反派呼啸而来,把阎明诗揪到会场上去批斗。苏汉才正在家里养病,听说了,气喘吁吁爬起来,拄着双拐急匆匆赶到批斗会上,一进门便跌坐在地上哭天抢地地大喊,求求你们,不能斗阎明诗,她是大好人啊!
整个会场顿时沉寂下来,只有苏汉才的哭喊声在回荡。他双手着地,一步步朝台上爬去……
几十年的摧折磨难,阎明诗的丈夫、富有才华、精通德语和英语的油画家曹酉一直默默陪伴着她,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安贫若素。我们去采访时,老两口那种相敬如宾的温情,说起种种艰难困苦时的平淡口气,令我们潸然泪下。
我们慨叹不已,说,你们全家都是革命者,你从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没想到遭遇了这么多的磨难。
阎明诗平静地说,行啊,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要不自愿来当这个“右派”,也得有人来当,我这个人心胸宽,好歹能挺过来。要是别人,也许就给整死了。
一个白发的女性普罗米修斯,在晚霞里静静地凝望着过去和未来。
新时期,阎明诗的问题平反了,她也年过花甲,应当离休了。一个革命战士本应高扬的生命旗帜,就这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黯然沉落。平反后,在十分不景气的农机厂,阎明诗的待遇与工人们一样,医疗费有时都无法解决。鞍山市委要把她调进机关,以使她的工资收入和基本生活有个保障。但阎明诗拒绝了。她说,几十年在农机厂,和工人处下很深的感情,她不想离开他们,反正她也做了大半辈子的工人,大家怎样,她就怎样罢。
这就是我们的延安女战士!
我们去采访的90年代中期,阎明诗已经朝夕与轮椅相伴了。告别老人的时候,晚照正透窗而进,映着她如银的白发和慈祥的微笑。
我们觉得她就像一座雪山那般圣洁。
严昭:浴火重生的金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