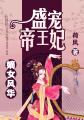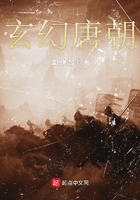那时的中国布满了干柴烈火和隐蔽的火种。没想到,在这所死气沉沉、不问政治的教会学校,竟也隐藏着革命的种子。旁坐的雷定芬同学发现了吕璜的苦闷,她就经常拉着吕璜一起散步,给吕璜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有志气的女子一定要奋斗,争取自由平等,而眼下,国家面临危亡,青年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民族解放事业,打倒卖国汉奸,推翻腐败政府,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仿佛沉沉黑夜射来一道曙光,吕璜眼前豁然开朗。她的目光从小我的苦难转向行将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在雷定芬的引导下,吕璜毅然投身救亡运动,在秘密的读书会里苦读和研讨,在抗日民族先锋队里接受洗礼,在城镇乡村奔走呐喊宣传抗日救国……
1937年5月7日,学校前厅的张贴板上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公布了开除甘佩文、禁止吕守廉(吕璜的原名)等6名学生出校活动的处分决定。吕璜和这几位受处分的同学愤然找到校长室,要求说明理由。答复是:你们不好好读书,不经请假,擅自参加社会活动。
7名同学慷慨陈词,救国抗日,何罪之有!
消息传开,全校师生和成都教育界为之大哗,各进步团体和学生界纷纷组织示威和声援活动,满校园贴满了声援的大字报和标语,琳琅满目的慰问品潮涌而来。所有这一切,使吕璜等7名被处分的同学看到了岩层下喷突的地火,听到了茫茫夜空里滚滚而来的雷鸣。她与几位小战友昂首挺胸在校园进出,照样大摇大摆地进教室听课。这些热血青年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自认为是抗日救国的仁人志士,只怕那些醉生梦死的家伙不知道呢,现在公诸于世只能使他们感到无尚光荣,无比骄傲!
进步报刊把华美女中这一事件称为“小七君子运动”。吕璜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民众的伟力和民族的希望。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这年11月的一天深夜,吕璜与几位同学偷偷把行李带出学校,第二天,她便踏上通往延安的烽火里程。
也许她出生之际差点儿成为溺婴的事情是命运的一种昭示,在此后的人生里程中,吕璜注定了要经受比别人多得多的苦难。
康岱沙:轰动“陪都”的豪门闺秀
90年代,我们多次去拜访康岱沙。
身材高挑,眉眼清丽,气质优雅,一头黑白相间的卷发,浑身透着从容不迫的大家风度,这就是康岱沙(原驻外使馆政务参赞)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那时,她穿一件黑色条绒茄克衫,谈话间不断到里间去照料卧病在床的丈夫陈叔亮(原外交部副部长),又倒水又拿药。说起她和丈夫的恋爱和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一往情深。看得出,在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中,夫妇两人情深意笃。
抗战时期的山城重庆。畸形的繁华,如潮的喧嚣,匆匆来去的人流,满街的军警宪特,每天被疯抢一空的“号外”,夜深人静时牵动千家万户的电波,不时响彻全城的空袭警报,这一切仿佛就是中国战事与时局的缩影。
康岱沙脸色潮红,明眸闪闪,穿着打网球的白色短衫短裙,像燕子一样飞回家。正在客厅接待客人的父亲康心之见心爱的女儿回来,面露微笑说,回来啦?天这么热,快去冲冲凉吧。
岱沙应着,匆匆跑进自己的房间,坐到梳妆台前瞅着镜中的自己,心头怦怦激跳,久久不能平静。这是1938年6月1日,是她终生不能忘却的日子。她对父亲谎称去打网球,实际偷偷跑到一间小饭铺的阁楼上,面对画着镰刀斧头的党旗,进行了秘密的入党宣誓。
新的更有意义的生命开始了。
在30年代后期被称为“陪都”的重庆,康岱沙的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大家族。早年去世的大伯父康心孚曾留学日本,是老同盟会员,与辛亥革命中的知名人士徐锡麟、章太炎、李大钊、吴玉章等都十分相熟,并曾任孙中山大总统府的秘书、北京大学的教授。二伯父康心如、父亲康心之、叔父康心远也都曾留学日本。抗战期间,康心如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岱沙的父亲康心之在经营银行、电力、煤矿、地产等企业的同时,还主办有相当影响的《国民公报》。
岱沙一家那时住在重庆豪华而宽大的前美国领事馆楼内,有仆佣十余众。父亲性情豪爽,喜好结交,在重庆上流社会有“食客三千”的孟尝君的美誉,国民党许多党政要员和岱沙父辈都有很亲密的交往。国民党著名人士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及其家属和副官等,长住在康家专门为亲友准备的客房里。《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全家长年住在康家的汪山别墅,直到他患肺病去世。1941年夏,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立会议就是在康家召开的。西北军的高级将领高桂滋、邓宝珊等人每到重庆开军事会议,也都必到康家来看望于右任先生和岱沙的父亲康心之。岱沙的姐夫张正群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人,也和姐姐住在这儿。每逢开饭时间,偌大的餐厅总是摆下几张大圆桌,少长咸集,高朋满座,笑语喧哗,一派豪阔气势。
少女时代的康岱沙便生长在这样的大家族中。她美丽活泼,无忧无虑,放学之后就是骑马,打网球乒乓球,练钢琴。未来对于她,不过是一个伸手可及的金色梦,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一切都无须她担忧。
但是,岱沙不仅是父母的女儿,更是时代的女儿。
她忘不了在上海读书时,从报上看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前往参加葬礼,同唱挽歌,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当时,她悲伤得伏在铺满报纸的床上,恸哭不已。
她忘不了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时,在嘉陵江畔看到的那些贫苦的水上人家,瘦弱的幼儿拴在船头,饿得哇哇直哭,稍大的几个孩子衣衫褴褛,挤坐在舱里,用惊惧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做母亲的蹲在船尾那儿烧饭,一掀锅盖,竟是掺了许多野菜的糊糊汤。这是康岱沙第一次如此近切地观察社会最底层的悲惨境况,想到自己养尊处优、挥金如土的生活,想到家里一桌席足够贫苦人家活上一年的奢靡,她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震惊与愧疚。自此,要救中国、也要救老百姓的强烈愿望,成了她生命中永远不熄的火炬。
她更忘不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东三省的沦陷,流亡学生声泪俱下的控诉与呐喊。也许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为什么而斗争,但起码知道了为反对什么而斗争。
年轻的岱沙如火如荼地投入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之中……
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女校长就像她从不调换的黑礼服一样,十分保守落后,对学生参加社会运动极为不满,控制极严。那天,她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读好书,今后谁要再打着什么“抗日救国”的旗号到街上乱跑乱叫,就请把自己身上的校徽摘下来!
校长脸若冰霜,全场鸦雀无声。稍顷,一个,两个,五个,十个,几十个学生站了起来。当康岱沙站起来的时候,深知她家庭背景的校长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康岱沙与同学们一道,默默地、坚定地走上前,把校徽摘下来,放到校长面前的桌子上。
秘密入党不久,康岱沙便向父亲郑重表示,她要去延安参加抗日队伍。父亲当然舍不得这个宝贝女儿,再三劝阻,并许诺很快安排她和哥哥去美国留学。父亲说,抗日也不缺你一个人,女孩儿家家的,上不了前线,学成归来再报效国家也不迟。
岱沙当然不肯退让。过了几天,父亲退了一步,说世伯邵力子答应设法送她去苏联留学,那里和延安一样,也是共产党掌权嘛。岱沙激动地说,眼下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危亡,生灵涂炭,要是大家都跑出去,中国亡了国,我留学还有什么用!
父亲恼怒地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政治?现在国共两党虽然合作了,但重庆和延安的关系很微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如果你去了延安,我在重庆的处境你想过没有?我还怎么做事情!
现在抗战救国是最大的事情,别的事情都可以放弃!岱沙倔强地站起来,目光直视着父亲。爸爸,我决心已定,请你不要阻拦我。
父亲拍案而起:黄毛丫头,不知深浅!你真要去,我就在报上声明脱离父女关系!
父亲从未对她如此严厉过,岱沙伤心极了。但是,一只渴望着暴风骤雨惊雷疾电的海燕,是任什么也拦不住的。
一个月后,在一个雾茫茫的早晨,康岱沙悄悄打点好行装,同家人不辞而别。她乘长途汽车先到了成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与一位“表姐”同行到西安。在这里,她喜出望外地遇到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班好友阎明英(后改名高玲,解放后曾任南京市科委主任)。她们和一批进步青年集结起来,徒步行军穿过八百里秦川。康岱沙这位千金小姐哪儿走过这么长的路啊,脚上磨破的血泡和袜子血糊糊粘在一起,痛得不敢沾地,只能一瘸一拐地勉强跟着队伍,边走边一脸苦相地对身边的战友说,我的天!还没等上抗战前线呢,这会儿已经成伤兵了。
最后一天,当她远远望见延安的宝塔山时,禁不住欣喜若狂,跳着脚欢呼起来。那时她全然不知,她离家出走、奔赴延安的举动,成为当时重庆上流社会轰动一时的新闻。
周盼:受气的将门虎女
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细眉长目的小周盼噘着小嘴,含泪走出祖母的房间,望着夜空中的昏星寒月,望着空阔的院庭和公馆门外肃立的卫兵,她觉得自己的心孤独极了,悲凉极了。她多盼望这时候父亲魁梧的身影能翩然出现在门外,她一定会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扑进父亲的怀中。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杨虎城将军。
这是1936年的清明节之夜。清晨时候,12岁的小周盼一头钻进汽车,跟家人一起到三原东里堡给生母上了坟。一路累得腰酸腿痛,晚上早早上了床。刚朦胧入睡,女仆慌里慌张走进来说,快起来,老太太发火了!
迷迷糊糊走进祖母的房间,见叔叔婶婶跪了一地,祖母在床上盘腿而坐,满脸怒容,周盼立刻吓得睡意全无了。
跪下!祖母怒喝。
小周盼跪下了,祖母接着絮絮叨叨数落开来,你们好糊涂啊,怎么能让丫头给她妈去上坟?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你们不懂吗,女儿上了坟,全家断了根,你们想让老杨家绝了后啊!
小周盼不服地说,我给我妈上坟,尽女儿的一份孝心有什么错!
祖母怒喝,住嘴,你个小黄毛丫头还反了天啊!
全家人战战兢兢,谁都不敢吭声。父亲常年在外忙于军务,家里是封建意识极为浓厚的老祖母一手遮天,女孩子不许听戏唱歌,不许骑自行车,不许打乒乓球,不许大声说笑,整日被管束得像刻板的木偶。只有父亲回家,才能给小周盼带来短暂的自由和愉快。多少次她梦想自己快快长大,好尽早冲出这封建的囚笼。没想到,就在这年年底发生的一场大事变,彻底改变了她和她一家人的命运。
1936年10月,13岁的周盼明显感觉到家里的气氛变了。以往,父亲总拿她当小孩子看待,见了面逗逗乐子开开心,很少和她说大人的话。自蒋委员长亲自来西安督战,部署“剿匪”,父亲的心境变得分外抑郁起来。每日长吁短叹。后来又经常夜不归宿,回家也是行色匆匆,稍有闲暇,便把女儿当成大人,一本正经地谈些救国救民的道理,还不断地问,你懂吗?小周盼就说,我懂,我懂。父亲便露出一丝苦涩而慰籍的笑。一天,父亲拿回一张绿色的传单,以往脸上的阴云一扫而空,表情异常兴奋。他从传单内容谈到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看来只有共产党能识大体,顾大局,不计前嫌,为全民族着想啊。沉思良久,父亲又颇有深意地说,我杨虎城此生此世能做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事,足矣。
数日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但自此张学良将军失去了人身自由,杨虎城将军被免去绥靖主任之职,接着又被迫出国“考察”。因受兵变的巨大震动和压力,祖母一病不起,继母一度精神失常,弟弟杨拯人也因病猝然离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抗战风起云涌。杨虎城将军觉得自己身为中国军人,长期逍遥于海外于心不安,便匆匆返国请缨抗战。没想到归国后便被蒋介石投入监狱。一位骁勇的战将不能捐躯于抗日战场,却从此身陷囹圄12年,于1949年在重庆渣滓洞惨遭杀害。
偌大的杨氏家族,突然之间只剩下小周盼和继母相依为命了。
那时周盼在西安兴国中学读书,这所高级中学汇集了一大批国民党官员的子弟。因为是“罪臣”之女,周盼成了学校的眼中钉,她的抽屉和书包常被翻查,一举一动受到严密监视,“有其父必有其子”,“斩草必须除根”之类的辱骂时时响在耳侧。但是,父亲和张学良将军所发动的“事变”使周盼一夜之间长大了,她从父亲的行为中懂得了救国救民的道理。不久,她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日里横眉冷对那些三青团骨干的挑衅;入夜独处闺房,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一切进步书刊。那些抗日救亡的道理,仿佛就是父亲慈爱的教诲,那些有关延安抗战生活的描写,激起她无尽的向往。当她看到中国女子大学的招生启事后,不能不怦然心动了。
哥哥杨拯民已先她去了延安。周盼也向地下党提出,她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烦透了,想去延安学习。
共产党没忘记杨将军,没忘记杨将军的儿女。一次晚自习,训导主任突然气势汹汹来到讲台上宣布,你们班里有共产党,限3天之内去自首,否则别怪学校当局不客气!
事态已十分紧急,当天夜里,党组织通知周盼立即转移,并决定把她送往延安。临行前,周盼想到她一走,家中只剩下善良的继母张蕙兰,不禁黯然神伤,难舍难分。周盼3岁时,生母就去世了,继母待她一直如亲生骨肉。现在她要离家远去,母亲能承受得了吗?
深明大义的继母镇静自若。那些天,周盼总想和继母说说心里的不安,可只要她一走到继母身边,继母便拿起活计走到院子里。晚间躺在床上,她刚要说话,继母却把灯吹熄了。周盼看出继母是在躲着女儿,她不愿因为她的伤感而影响女儿的选择。
娘俩一起度过沉默而心酸的7天。那天清晨,周盼出发了,母亲递给她一个早已备好的包袱,里面是老人亲手织的毛衣裤、用土布做的衬衣裤和一双布鞋。周盼走出老远,还见瘦弱的母亲在门前频频拭泪招手。
1941年11月,周盼到达延安之际,为实行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建议,她所向往的中国女子大学已与其它几所院校合并为“延安大学”,她没赶上。
倪冰与赵志萱:一条木板过黄河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怒愤,
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吼声惊起了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肃曲)
《五月的鲜花》是“一二九”运动中最流行的一首歌。“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是“一二九”运动中最震撼人心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