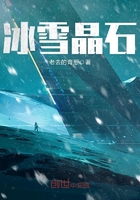凌轩出了皇宫,见天色还早,便循着昨夜的记忆想去寻那间酒楼。街道上窥不见一丝热闹的痕迹,让人忍不住去揣测不久前的种种繁华皆是一场虚幻。大多店门都是紧闭,唯有一些食馆酒楼茶坊仍旧开门接客,少不了有些富贵人家的年夜饭是要在那里吃的。
走着走着就到了一处府邸,石阶下两只石狮威武,石阶上被扫的看不见灰尘,金漆的“凌府”二字被伸出的屋檐遮住了清晨的光芒而显得有些暗淡。朱漆的大门也褪色了不少。凌轩双手抱胸在门前站了许久,绕进了门前十几步路的距离的一条小巷子。凌轩施展轻功一跃而起,酒壶在腰间也不安分地动作了一下又贴回了腰间。
仍旧是假山环绕细水长流,连后院中的那一棵老槐树都没有再长高过分毫,只是为了应和冬日的肃杀,褪去了身上的所有翠叶,在寒风凛冽中尽显苍老之态。伸出的枝桠如同鬼魅般,丑的让人不愿去看却又不忍不看。
老槐树正后方是一个仅容一个人爬过的狗洞,十岁那年,就是从这个洞里爬了出去,然后恣意江湖。老槐树上挂着的秋千已经不见,毕竟现在的凌轩不再是那个荡着秋千吵嚷着要飞起来的孩子了。
中院内是各种盆栽,冬日的腊梅在空气里散发出孤芳自赏的骄傲气息,满树的画编织成一个美好的梦境,仿佛还是十年前的样子,一切都没有改变过。凌梓然的书房,府里的厢房,都坐落在中院内。幼时总爱钻进书房,缠着凌梓然非要摘后院那棵老槐树上开出的白花,气的凌梓然眉毛都挤成了一条线。
今日是腊月三十,府里的下人大多在后院忙碌,偶有一两个经过的,也被凌轩很好地躲避了去。
“啊!你是谁?”凌轩犹豫着要不要敲开书房的门时,被一声惊呼扰乱了思绪。转身就看到一个十六岁的女子被惊得花容失色,张大了嘴巴颤抖着说。
凌轩慌着捂住那丫鬟的嘴巴,一时忘了藏起来。有几个家丁拿着棍棒就围了上来,连凌梓然都颤颤巍巍地上来,府里顿时乱作一团。
“孽子啊孽子!”凌梓然单手靠背,另一只手的食指伸出恨铁不成钢地对着凌轩所在的方向点了几下。不过是十年,凌梓然的背已经弯曲,声音里透出的沧桑,任是谁都无法想象出面前的人曾在咫尺朝堂中进谏过多少次,又被打入天牢多少次后安然归家。
凌轩腆着脸笑笑,手从那丫鬟的嘴上拿开,又把那丫头往前推了几步:“爹。”
“行了行了,都散了。”老头子挥挥衣袖,将府里的下人都打发了去。
“倒是知道回来了?又是从狗洞回来的?”老头没好气地说,但逐渐舒展开了的眉眼泄露了心底的惊喜。
“爹,我那屋子还替我收拾着呢吧,我去歇息了。”凌轩却是脚底一溜烟跑了。
凌轩推门而入,逐渐暖了的日光透过窗户站在房内的地面上,透露出斑驳的影子,黑白交错的光景里,连记忆都是美的。屋子里的摆设依旧简单,却不见一丝凌乱。不过是一张床,一方塌,一套桌椅,多余的都显得累赘。亲切之感如同洒在了背后的阳光般暖人心怀,到底还是归家了。
太阳渐渐沉入西边的山巅,天空也由蔚蓝色转变成了深灰。不知街角的哪户人家燃响了第一挂爆竹,耳边似乎回荡着一家和乐围坐在一起的嬉笑。随后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最初能够分辨是哪个方向,到后来只能听见一声声一阵阵的声音响彻在耳畔。凌轩来了兴致,非要从管家手里抢过自家的爆竹放在门前燃响,身后站着的是凌梓然和夫人林梦琪。
凌梓然早就吩咐了下人在天井里放了十几个火炉,几张长桌拼在一起,府里的下人们家在本地的都在早些时候放他们归家过年了,如今还剩的都是没了爹娘或是路途遥远。凌梓然平日里待下人就亲厚,今日特地吩咐府里未离开的下人共坐一桌。一时间,气氛更是融融。凌梓然夫妇毕竟是老了,也爱见这样的热闹,望着满桌的人双眼里盈满了笑意。
凌轩的手指不自觉地抚在腰间的酒壶上,嘴角的笑似乎是凝固了般未见一丝变化,心却已经飘回了那家酒楼。那么大的酒楼,只有两个人住着,过年也是冷清的。
府里的下人对凌梓然都有着一丝恐惧,当朝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即便素日里再是和蔼,骨子里的威信也是难以掩饰。下人们只是低头坐着,双手在桌下紧紧攥着衣角,两只眼睛带着胆怯与畏缩忍不住瞟向那个满头华发的老人。
“爹,你平时把府里的人管的太严了,瞧这一个个都不敢动筷。”凌轩若无其事地将筷子咬在嘴里,满脸鄙夷地说。
凌梓然的嘴角动了几下,气愤地看着凌轩。从凌轩小的时候开始,这个儿子就没让他省心。小时候读《论语》,他非要拿出《聊斋志异》;后来习武,用竹棍将树上的马蜂窝捅了下来,人却跑到房间里躲着。后来那个武师带着一脸的脓包来到凌梓然面前告状:“公子天赋过人,我技艺不足,唯恐日后误了公子。大人还是另请高就!”;再后来拼死拼活要闯荡江湖,就让人没日没夜地守在他房门口,他倒是直接一棍子闷在了看门的小厮头上,从后院的狗洞里钻了出去。
“不不不……老爷平日里待我们很好的……”一个轻细的声音传入耳中,凌轩看向说话的人,是白日里那个丫头,现在正红着脸,咬着下唇看着一脸无事的凌轩。
“这样吧,谁说出老爷一个不好的地方,我就给谁夹一次菜~”凌轩放下筷子,站起身来对经掉了下巴的众人说,说完还不忘对凌梓然眨眨眼。
凌梓然气的将摆在面前的酒一饮而尽,回给凌轩一个恶毒的眼神。
“哈哈,老爷和少爷一见面就拌嘴。少爷明明就是回来看老爷和夫人的,还嘴硬。老爷呢,平日里总要问我轩儿离家几年了。你们这对父子啊~”说话的是府里的管家福伯,是在府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人,也是最了解凌梓然脾性的人,说话也少了些许的顾忌。
“福伯多嘴!”凌轩和凌梓然父子俩难得的默契一次,两人一起拍案而起,吓的福伯乖乖地不再说话。
“噗……”林梦琪看着这一对冤家父子,忍不住笑出了声,底下也有不少丫鬟用衣袖遮住嘴巴轻声地笑着,府里的小厮则是交头接耳。凌梓然冷哼一声,不得不承认,被凌轩这么一闹,气氛登时轻松了不少,有胆大的已经拿起了面前的筷子夹菜送入了嘴中。
凌轩坐回到椅子上,轻轻地端起酒杯,仰头将酒都灌入喉中道:“老头瞪来不心慌,自称儿是酒中仙啊,哈哈哈!”凌梓然好不容易平复下的怒气再次被激起,瞪着凌轩。
凌轩皱眉饮下了那杯酒,手又不自觉的摸到了腰间的酒壶。原来饮过了极品佳酿,便是御赐的仙品,也只是过眼云烟般穿喉而过罢了。凌轩见下人们都吃的欢了起来,也动筷吃了几口,酒却不愿意再多饮一口。
年夜饭足足吃了两个时辰,府里的下人们才把碗碟全部收了下去。凌梓然和林梦琪年纪大了,身体也比年轻人畏寒,用过餐后就回了房。
火炉的炭火烧的毕毕剥剥,偶尔跃起一两寸高的火焰,橘红的火苗根部是蓝色的焰火,哄闹的院中忽然安静了下来,众人望着炭火发起了呆。凌轩也不再说话,只是打开了腰间的酒壶,往口里灌着酒。视线从众人中间跳过,到了不知名的远处。苏修墨,这个名字,在哪里听过?
“大伙吃的尽兴,不如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说这话的福伯,他的脸不知是方才饮酒上了脸还是被火光照映的通红,显出了几分可爱。
年轻的姑娘小伙已是乐开了花,都用手托起下巴眨着眼睛满含期待。凌轩挑起嘴角,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说的是前朝的旧事,说起来倒也是巧了,大家可知前朝的第二位皇帝仁宣帝的名讳?”福伯扫一眼面面相觑的众人,最终实现定格在了仰头饮酒的凌轩身上。“嘿嘿,可是叫做凌轩,与我们的少爷同名呢。”
众人的视线一齐落在了凌轩身上,见他歪斜这身子,一只胳臂搭在桌沿上,漫不经心地说:“继续。”
“我再问大家,每次上街时走到长华街口,有没有注意过有一家破败的酒楼?”福伯看着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露出了手到擒来的笑。
福伯憨笑一声:“我们还来说那仁宣帝,不说他生前琐事,只说他身后事。仁宣帝执政六十多年,一生无后,所以死后把皇位传给了异族轩辕氏。”福伯年纪大了,听的故事也比旁人多些,知道在何处停顿能够激起听故事的人最大的兴趣。
“那那个皇帝为什么不立后?要是我是皇帝啊,我一定是要三千佳丽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痞笑道。
“胡闹!”福伯厉声呵斥一句,转而又换成了慈爱的眉目看着凌轩:“那皇帝爱的是他的国师,可惜那国师在他即位后一年就死了。”
众人一阵唏嘘,能够被皇帝爱上的人,又身居高位,无论是才华或是样貌一定是出色的。凌轩淡淡地听着,脑海里却毫无来由地跃出了一张脸。那张脸是温柔的,但他的声音却好似仍旧嫌弃不够,非要增几分温润才肯罢休。两人说过的话连十句都不到,凌轩不知为何就记得那么深刻。
“据说那国师生前与皇帝有约,先走的人一定要在奈何桥边等着另一人的。”福伯微不可闻地叹一口气,继续说:“现在,两人怕是已经遇到了吧。”
“福伯,那跟那家酒楼有何关联?”又有人带着疑问提出了问题。
“你想啊,我们说那位置,那可是几条街的入口处,人来人往极热闹的,在落败后没人接手,不奇怪么?”福伯到了关键处又抛出了一个问题,引的众人猜想连连。
“那长华街在何处?”始终沉默的凌轩突然开口。
“呃,离府有些路程,少爷好些时候未回家了,改天我找人带少爷四处逛逛。”福伯一脸恭敬地说,看到凌轩点头后,接着先前的话头继续说:“前朝也有人盘下那间店铺想做些酒楼营生,起初几天也好得很,但就在开始装修时,有位伙计就在门槛跌倒了,后来听说那伙计是看到了一位穿着白衣的鬼,被吓得摔倒了。”
凌轩听到了众人的抽气声,几个胆小的丫头挤在一起,揪着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的衣角,紧抿着嘴唇不敢出声。
“这当然是没人相信的,那伙计拿了工钱,只能继续做活。后来在里面拖着旧桌椅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连门都被风吹得打不开。那位伙计吓得跌坐在地上,不知什么时候,那些桌椅所在的地方都悬挂起来了一条条的白绫,被风吹的一直跟在那伙计身后。那伙计行地上爬起来,想要开门,刚一转身,就看到那个穿白衣的鬼,舌头一直拖到了地上,嘴角挂着的血还是鲜红的,像是刚饮过的活人的血液。跟白纸一样透明的脸,双眼瞪得老大紧盯着那个伙计。”福伯一边说着一边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几个挤在一起的丫头已经搂在一起发抖。
“那伙计只能把眼睛闭着,眼不见为净嘛,可是再睁开眼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连那些白绫都不见了,风也停了。那伙计赔了工钱,还吓破了胆。后来也有人想要那家店铺,每次都有人被吓得爬回家,时间久了,那酒楼也没人问了。”福伯说完了故事,一脸深意地看着众人。
“那家酒楼,”凌轩将酒壶重新悬回了腰间,看着福伯说,“仁宣帝和国师跟那家酒楼有什么关系?”
“呃,这个说法多得很,有人说是国师没有等到仁宣帝,心有不甘,就寻了个落脚处,留在阳间看仁宣帝的下场,也有人说那酒楼是仁宣帝生前与国师把酒言欢的地方,国师在那里等着仁宣帝。具体是怎样,怕是没人知道了,那都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福伯老实地回答。百年前的纠葛,后人如何评说都只是后人而已。任凭百年前如何的惊心动魄生死难解,落到后人口中,不过是云淡风轻的寥寥数语。
凌轩的心莫名被抓紧,连思绪都变得迷离,头昏昏沉沉,身体如同飘在半空中寻不到半分未结。他站起身,对仍旧惊魂未定的众人说:“喝的酒有些多,出去醒醒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