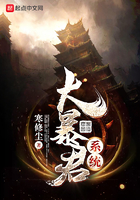暴行沿着这片原先江南锦绣般的水田周边开始,是一种由边沿向着中心的偷袭。包抄和蚕食以非常诡秘的方式进行,难道这竟是由于屠杀者感到了自身行为的不义?然而,掩埋却是非常坚决地进行着:满载的垃圾和渣土从不可知的阴暗处驶来,又空车向着阴暗处驶去。它们的使命和动机都是无须隐瞒的,即以污秽和肮脏埋葬良田沃野。来往匆忙的运载只是为了制造死亡。
这儿原系旧日皇家苑囿,曾经是河道纵横、堤陌桃柳交映的地方。历经岁月沧桑,那低洼的水面淤积而变成了稻田,这些稻田又逐渐被人为地堵垫成废地,终于只留下这最后一方水田。现在,连这“幸存者”也要遭受不幸,这最后的绿色也要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我们不需要朱垣碧瓦,也不要雕梁画栋。平民的生活原本不需要奢华的装饰。但是我们需要蛙鸣、流水和稻花的香气,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我们需要十里荷香。我们不能离开这一方供养我们粮食和水的家园。然而,这一切将不再留下,这一切将冷酷地为废墟所取代,一如既往的掩埋已经开始。
那鹏着水花的田间沟渠呢?那夏晚乘凉的树荫呢?那秋夜可以望星的场院呢?这里将要变成庞贝!
但这毕竟不是庞贝。掩埋庞贝的是火山灰,是燃烧的岩浆,是距今一千九百年前猝不及防的火山爆发。而我们此刻,不是由于火山,不是由于泥石流,不是由于地壳的断裂,我们是用自己的双手制造毁灭。东方庞贝的制造者是我们自己。这里的人不断接受那些阴暗的指令,不断以人为的掩埋制造一个又一个庞贝,这种制造已经在这座昔日皇家禁苑上进行了数百年,剩下的、仅仅剩下的,就只是眼前这一方最后的水田。而此刻,连这也要宣告消失!
真正的庞贝不仅仅是掩埋的故事,而且还是发现的故事。某日清晨,那里的农夫在种植葡萄藤的时候发现了旧日的街衢、广场、政府大厦和可容五千观众的露天竞技场。意大利用了二百年的时间,使这埋藏地下的城市重现人间,让那里重新生长橄榄树枝和无花果叶,以及常春藤。而我们不是,我们以庄严的名义拆毁我们的城墙和牌搂,我们堵填生产稻米的田园,我们让整条淮河的鱼全部死去,我们让自己变成失去空气和水、最后失去家园的无家可归者。
就是这几日,就是我此刻为新出现的庞贝哀悼的时候,在这片稻田即将消失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这片变得越来越小的地面放起了风筝。那寂寞的风筝依恋地上升和游移。它是在凭吊这不可避免的消亡。到哪里去找流脂的京西稻呢?到哪里去找流水潺潺的农家柳岸呢?
那片秋日打场夏晚乘凉永远散发着田园温馨的晒场呢?晒场边上的农家小溪呢?那里狗的欢跳和人的喧闹,那飘着柴火香气的黄昏呢?
我们难道竟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祖先留下的园林和田野被制造成一座又一座新的庞贝吗?我们难道真的无力制止这蓄谋已久的谋杀和掩埋吗?
电话亭上的招贴
北京这座古城日益呈现出现代风采。今年北京的街头又增添了新景致,就在我居住的海淀中关村一线,每隔数十米便并排竖起两座公用电话亭。这些由加拿大太平洋传讯公司修建的亭子,用橘红和湖蓝两色的现代材料造成,洁净典雅,不落俗,富有现代气息。行走在绿树荫下,远望那鲜丽的红蓝两色的跳闪,仿佛置身欧美城市的街头。
但在这里几乎所有的美好都会走样。曾经的美好,不用多久,就会成为现实的丑陋。例如,满街的台球桌被用来赌博,电子游戏机被用来毒害儿童,而随着电脑进入家庭,色情也随着进入中小学生神秘的空间,等等。
这个城市有随意张贴的习性,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建筑物,也无论那是多么华贵和精致的墙面,那些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往上刷糨糊,让那些粗俗的语言随意涂污。这些张贴,大自公家制定而且常变常新的宣传品,小至各色人等的各色“文告”换房的、求职的、促销的,到处泛滥的“价格面议”、“实行三包”、“致富捷径”。反正那些建筑物已失去尊严,谁都可以任意肆虐。可是,临到太平洋传讯公司为市民竖立的漂亮的电话亭,事情就有点不一样了。
记得人们说过,谁敢在纽约的华尔街或是香港的中环光洁如镜的地面吐一口痰,此人便算有胆。我想不会有。而在这里,却到处都有这类勇夫。就以此刻我们谈论的电话亭子来说,当人们为它的出现只感到眼睛一亮还不及熟悉它的光艳时,甚至那些亭子里的电话机还来不及安装时,这社会的丑陋习性便一反它慵懒和颓唐的常态,那些“苍蝇”便黑压压地爬满了那些光洁晶莹而让人目眩的亭子的四壁!
贴了又撕,撕了再贴的,是那些“包治性病”、“一针就灵”的广告。这个城市某些层面的龌龊和无耻,它的“旁若无人”的行径简直让人吃惊——似乎什么最见不得人它就起劲地来什么。在众多的招贴中,这类花柳病广告最来劲,原因就在于它最肮脏。
这些苍蝇般的宣传品毫无顾忌地飘飞和粘贴在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甚至大学圣洁的院墙上,每次经过总感到恶心,羞耻感使人总想闭目侧身而过。但积习总不由自主,总要用余光搜寻那些无耻的张贴,从橘红和湖蓝的鲜艳中去发现那些污浊。
撕了再贴的痕迹,让人想起这民族的劣根性,它的冥顽和麻木说明痼疾的深重。前些时阅香港某报,有散文写“钢琴里的老鼠”。那些鬼鬼祟祟的家伙竟然在肖邦和莫扎特的“家”里做窝!但那是文学作品,事实也许竟不如是。由此联想到此刻这座城市的崭新的电话亭上的张贴,它的厚颜无耻胜过了那些老鼠,鼠类只能偷偷摸摸,而那些花柳病广告却是堂而皇之的张狂!
有关北京城墙的话题
在北京出版的《中华读书报》,1995年8月9日有一篇由记者红娟采写的人物故事。她写的是作家林斤澜,题目叫《话说北京的城墙》,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本是浙江温州人氏的林斤澜,言语里已觅不到几许乡音的痕迹。在北京四十多年,最怀恋的却还是那老北京的城墙。他说城墙在中囯是很大的建筑格式。北京的城墙存在了八百多年,中轴线、九个门……城墙与里面的格局融会贯通、交相辉映,这样典型的都城建筑世间绝无仅有。只可惜,拆了!那时梁思成就疾呼:难道不能在拆与不拆之间想办法吗?而今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呼吁甚是英明。城墙是封闭的,可城墙里面有凝聚力,封闭是糟粕,凝聚是精华,它们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存在,这一点,过去考虑得太少了。
记得林斤澜表达对北京城墙的怀恋和惋惜。不止这一次,他还写过一篇叫《城墙》的随笔登在《光明日报》上。文章也回忆了梁思成反对拆城墙的往事。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梁思成教授有一个诗一般的倡议:广阔宽厚的城墙,正好是一圈高架花园,别的国家花多少钱也不能有这么大的规模。它是绿化带,又是环城花园,还是星星点点的歌厅、舞场、棋局、茶室、酒吧、健身房。是八百年的苍翠和现代的花朵,你里有我我里有你,别时别地无法替代的文化。
梁教授这番设想很有诗意。可惜,诗是诗,事实是事实。诗代表的是文明,脆弱的文明敌不过愚昧和专断。结果是“拆”,“拆它个稀巴烂!”
后来,到了“文革”,城墙拆得差不多了,又在明西直门的门墙下面,发现还夹埋着一个稀世之宝——元大都的旧门。这当然也不能留。也是义无反顾地、彻头彻尾地拆了,平了。
回到作家那篇叫《城墙》的文章上面来。该文最后感慨于时下人们热衷制造假古董的风气,有点幽默,又颇有学者风度,讽喻适度。令他更为感慨的是,“破四旧”的英雄们,毁灭文物的勇士们,竟然不知道有叫做梁思成的这个人的。作家的感慨还在于人们对当年批判梁思成这件事依然缺少足够的反省。当年建筑师们和文物专家们对拆毁城墙的痛心疾首之情,未曾引发人们沉痛的共鸣。
写这篇文章的作家没有用激烈的言辞来谈论这件大事。但我却从他的轻淡中看出了他的沉重。中国人,现在都关心别的什么去了,谁还关心城墙的拆与不拆这些陈年旧事?像这样对于“与己无关”的事物耿耿于怀的人,现在是很少了。而我们的作家,不仅讲梁思成,由梁思成引发开来,还讲马寅初,还讲这些忠言陈上而终遭灾祸的文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爱讲温柔敦厚,遇事前思后想,好像是周到完备了,往往是温水一杯。所以近于迟钝的行事不果断,可说是中国人的“集体形象”。但若以拖泥带水或优柔寡断来概括中国的国民性,这可有点错失。就以拆城墙这事来论,梁教授请求考虑在拆与不拆之间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回答他的却是更为坚定的行动:拆!
北京的城墙经营了几个朝代,达八百佘年。经历了许我兵燹和地震。其中包括本世纪中叶那次政权转换,数十万守军和平接受改编,那次的炮火也避免了。但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到底还是下了决心把这古城墙给平了。
“文革”是干了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单说“破四旧”改地名这一桩,一下子,全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是一例的“反修”、“卫东”、“工农”……甚至国际通例的交通信号绿灯通行也被改为红灯通行。那时有很多举止均令全世界感到诧异。
但若说“文革”空前,却也未必。北京的城墙,就拆在“文革”之前。而且还不止毁城一例,云南的鸡足山是与普陀山齐名的佛教五大圣地之一,也毁于“文革”之前。那些动手毁灭这名山的,用的也是“革命”的名义。不是盗匪,不是溃兵,也不是刁民,而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工作组”带领,有组织地将其夷为焦土的。
这鸡足山位于滇西宾川县,南北7·5公里,东西15公里,海拔3240米,始建于三国时期,唐时极盛。该山有寺庙百余座,现在仅存一修于清代的寺,一门、一塔,其余都葬送于“革命”了。了解情况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还触目惊心。据说,那些被伐倒的巨柱,其横断面竟有一张宴客的圆桌面那么大!都说国人生性保守,但是对待祖宗遗留的东西,来了狠劲可也挺吓人的。
为区区北京城墙悲怀郁结于心,这在现世毕竟是十分难得了。现在的人们很少关心这些事,大小人物有各自大小不一的关心。人们很难想起屹立了近千年的城墙怎么一下子从地面消失了,也很难想起如今的废墟就是祖先的光荣和艰辛!写《城墙》这样的作家真是越来越少了!只是这时,我们方才想起红娟笔下的这位作家的耿耿之心,方才想起这颗心的跳动实在是可贵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