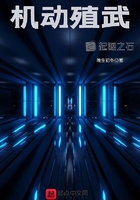至于第二条你在感情上让人不放心,你可真是领教了老古对你的不放心,有一年春节,老古一个人回他的老家去了,你因为父母去美国哥哥那儿探亲,又不愿去老古的老家,就只好决定一个人在学校里过。老古拖到年二十九才走,你说,你怎么还不走呀,家里人都等急了。他说,我看是你等急了,巴不得我快走,我走了你想干什么?你只好不说话了。老古走后,一天打八个电话,用电话遥控你,还疑神疑鬼地说电话这边屋里有动静,并问什么人在那里?你说,是风。只要有一次电话没人接,他就要在下次电话里问你几点几分的时候为什么不接电话,到底干什么去了。你说,那时候我在厕所里拉屎,行了吧?年初三老古就从老家匆匆赶回来了,进门后就在屋子里察看,最后拣起一块烟蒂,问是谁留下来的。你气得要命,那烟蒂很可能是过年前老古自己扔在地板上的。你吼道,我不知道,我还想问你呢,是谁留下来的?我们拿到法医那里化验一下签定一下好不好?你真是气坏了,就算是要通奸,哪个中国男人肯在年三十年初一来找你?未婚男人要去找他妈,已婚男人要带着老婆孩子去找他妈,这神圣的日子是留给家族、伦理和道德的,相信全中国都不会有人在年三十年初一通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天天都有可能,这时候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了,就是小偷强盗也要放假的,也要有张有弛劳逸结合。
在感情上让人不放心,你想那首先大约是因为你长的这副模样不够本分,你的下巴太尖,你的眼睛太亮,你的鼻梁太挺,你的嘴唇太薄,你的两颊也不够厚实,连你的身材看上去也不是那种忠心耿耿的类型,躯体线条的拐角处不够浑实,是无端地让人觉得小而尖刻的那种。你和叶如意虽然长相不同,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同一类,即机灵有余敦厚不足的那类,长成这个样子很吃亏很折本,容易让人以貌取人了,以为心里头的想法和念头也跟外表一样不安分守已--可见好女人的长相还是有一定之规的。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说你长得很筘,从小到大就是表现再好也评不上三好生,你想这跟你的长相不是全无关系的,在你看来那种回回都能当三好的女孩子长得真的跟你很不同,把她们的长相归纳一下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可以说人家天生就长了一副三好生的模样,谁见了那副模样都会忍不住在民主选举的时候投上一票,就是你也忍不住要投上一票的。工作以后每学年评先进工作者或者教学先进之类,你和叶如意每次差不多都是各得一票,你那一票是她投的,她那一票是你投的。你仅仅从长相上就没有博得这个社会的信任,也没有博得老古的信任,你们如果离了婚,大家仅凭直觉就都会同情他的,觉得他是被侮辱与损害的,毫不犹豫地站到他的立场上来,因为他长得多么中正、忠诚、无私、谦逊、理智、纯朴呀,简直就是正人君子的一个标本。他认为你长得这副模样就是一副随时想有外遇的样儿,你觉得老古他真是抬举你了,你想,我那么有风情么,我那么有资本么,我幸亏不是美女,幸亏不是,否则日子一定会更加难过了。他对你那么不放心,除去你的长相因素,还有别的,他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你和他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这没法隐瞒,你应该想到中国男人多多少少都是有那么点“处女僻”的,你应该做点小动作小手脚,比如找点红墨水来,还可以花点钱去做一个处女膜修复手术,这是女人为了更好地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为讨好男人而根据他们的心理需要想出来的一个欺骗手段,说不清楚到底是女人的悲哀还是男人的悲哀,说不上究竟是谁在掩耳盗铃,说不上谁比谁更可怜。
老古,有一个前妻的老古,丧妻的老古,他自己又不是童男,怎么偏偏要在处女这个问题上这么执著和纠缠呢,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处女膜那么重要么,他要个处女膜有什么用,那个玩艺究竟有什么用处,它是纯洁的象征吗?纯洁和处女膜之间可以划上等号么?他总是逼着你一遍又一遍讲述第一次性经验的具体细节,用那些细节来折磨他自己的神经,然后对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男人在想象中一遍遍施以绞刑。他觉得你在感情上让人不放心还有一个极其重要原因是你写诗,尤其擅长写爱情诗,就是不写爱情的诗里面也影影绰绰地有着爱情的影子。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利比多比别人要多得多的人,写诗就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发疯,为了给身体中的那些能量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和公允的排出渠道,既不害人也不害已,就像让试验之用的新型导弹在公海里爆炸。其实你今生今世最想做的并不是写诗,而是投身革命,做一个五四青年,你要把红头绳般鲜艳的青春交付给一个伟大时代,把年轻的血勇敢地涂抹在历史底版上。
你从小到大一直有这种滚烫的念头,你想象自己穿那种带蝴蝶盘扣的对襟小褂,配上喇叭形的黑裙,脚上是系带的方口布鞋或皮鞋,梳着蓬勃的短发,手执一本《新青年》杂志,急匆匆地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街巷里。你该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你的故乡在遥远的江南或齐鲁,时代的声音已经淹没了个人的情绪,只有在清风明月的夜晚在摇曳着榆树影子的木格窗棂前心中才会泛起淡淡的乡愁。你该是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娇惯、任性、一意孤行,从小就不肯缠脚,逼得母亲只好让步,在十七岁上因反对一桩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和顽固粗暴的父亲闹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带足盘缠,与相爱的中学男同学私奔,辗转来到京城,最后你还想象着生命这样收场:时光转眼到了1926年,到了三·一八惨案,你在请愿的队伍里倒了下去,永远地倒了下去,倒在了血泊里,鲁迅先生为你以及像你一样的青年写了一篇文章,一篇像《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章。
可是你没有出生在那样的时代,现在不是1919,而是1999,是世纪末,映入满眼的是物质,是欲望,是隔岸犹唱的《后庭花》般的曲调,你风水宝地般的年华呵在这委顿的光阴里一点一点地消磨,终于变得荒芜,你热烈的、革命的激情白白浪费着,像海浪冲刷沙滩那样徒劳地冲刷着血管管壁--既然不能投身革命,那就谈恋爱吧,你今生今世想做的第二件事是恋爱,你一直认为恋爱跟革命的性质相仿,你可以把身体中本来想用以革命的那部分能量用于恋爱,可是你结婚了,丈夫老古认为结了婚的女人还恋爱就无异于女流氓,他像极有责任心的监狱看守那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你,提防你越狱,他每次出差回来都说你胖了,瞎猜一定是什么男人请你吃饭了,他还要数数床头柜里的避孕套,他大概是小学算术没有学好,总也数不出个确切数字来,数着数着,刚开始说少了,再数下去又说多了,无论少了还是多了,只要不是原来他想象的那个数目,那都是够可怕的,其实原来究竟有多少个老古自己也未必清楚,于是你建议他最好是给每个避孕套编上号码,立个档案,真正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某个电台节目主持人让你去做嘉宾谈婚外恋和第三者插足问题,你以“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我可以立贞节牌坊”的理由给辞掉了,你对这样的狗屁话题实在不感受兴趣,就是感兴趣也没法谈,你要是谈了,老古就会问从哪来的这方面的经验呀,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的呀。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还想恋爱,那必须要炼就一副地下党的功夫才行--既然不能恋爱那就只好写诗吧,永远写诗,永远写诗,把想投身革命和恋爱的能量统统用到写诗上去,在诗里过一种风光旖旎的生活,可以永远没有具体行动。但是你很快就发现写诗也不行,你的家里不知何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每首诗都要经过老古这个新闻检查官锐利目光的审查,他的目光力透纸背,把每一个字都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从最含糊的词语和最隐晦的句子中揣摩和臆想出你的图谋不轨来,然后按图索骥,到现实生活中去对号入座,不是说你旧情难忘就是说你正在暗渡陈仓,原来他就是这样搞文学评论的,真不知这样的文学评论属于什么派别,给它起个名字就叫窥阴派好了--既然写诗也不那么自由了,那就只好为这部分能量重新另找渠道,有一段时间你迷恋上了吃,你一直都是一个爱吃的人,而现在被迫索性将所有欲望都转化成食欲,你简直成了一个饕餮,走在街上你的目光只注意饭馆,除了饭馆你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了,为了吃最好的海鲜你不惜从城市的大东南跑到大西北,划一个大大的对角线,但是老古很快提出了抗议,他认为这样花销太大,每次和他出去吃饭他都恨不得领你去吃那种以传染肝炎为已任的路边小摊或者去那种门头比最小的公厕还小的拉面馆,他说同样的钱在那样的地方可以吃一顿在这样的地方能吃五顿。
有一次他领你去一个下等的小馆子里吃饭,要了一份清炒白菜,一片叶子也没有,全是老得不能再老的白菜帮子,纤维粗得可搓绳子,就是牛吃了恐怕也要发火的,正是因为太难吃所以你会对此终生难忘。老古他忘了他结婚前是怎样拿吃来讨好你的了,你爱吃鱼,你真怀念那段他常常请你吃鱼的日子,你有时候想你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和老古结婚,跟他频繁地请你吃鱼有很大关系,你简直是被他用鱼收买了,你的终身大事和前程就毁在鱼上了,你和老古是鱼的姻缘,记得你们俩刚认识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一起去逛水族馆,你一边在玻璃缸前观看鱼们在水里悠悠地游弋一边浮想边翩,这种产于太平洋的铅笔鱼红烧应该比较好吃,那种产于南美亚马逊河的美人鲈则适合清蒸。
从水族馆出来你就条件反射地拉着老古直奔一家鱼馆,由老古请你大吃一顿,吃完后你就昏头昏脑地对老古说,我们结婚吧。没想到结婚后反而再也没人请你吃鱼了,只有当你跟老古大闹离婚时,为了安抚你,他才咬咬牙跺跺脚和你到海鲜城去一次,于是每次恶吵之后,为了和好,老古一般都会建议去吃鱼,他知道你太爱吃鱼,一吃鱼就会丧失原则,向他让步,向他就范,向他投降,所有抗争最后总有一个俗不可耐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吃鱼。一鱼而抿千仇,鱼能化干戈为玉帛,鱼轻而易举地将乾坤挽回。你已经和他在餐桌上签订了一大堆丧权辱国的条约,比如《微山湖鱼馆条约》《大观海鲜城条约》《潭鱼头酒店条约》等等。有时你盼着打架,打架时你就提出离婚,你知道老古最怕离婚,你离婚的决心越大,和好之后吃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是这样,必须在闹离婚闹得天翻地覆之后才有可能去吃鱼,你已经习惯了在这种背景下吃鱼,极偶然的情况下风平浪静地就能去吃鱼,你难免要受宠若惊,并且浑身不自在。就是这样,最后连吃也变得无法随心所欲,连用自己的钱去吃都有人看管着,既然吃也不行了,那就不吃了,那就只好给多余的利比多能量另找途径发泄,最后就只剩下了吵架,有且只有这一个途径了,就是吵架吵架再吵架,生命中所有该去干别的事情的能量如今一古脑地全部用来吵架,可想而知,这样的架吵得该是怎样登峰造极,可歌可泣,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青春在吵架中闪光,放射出夺目耀眼的光彩来。有一次在打架的时候,你们像掷铁饼或投铅球那样把锅碗瓢盆扔来扔去,场面惨烈,你的脑海里竟忽然间冒出一连串《红梅赞》的音符和歌词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在这样的伴奏下,你的动作英勇并且优美。你甚至想,要是你的腰间挂着一排手榴弹说好了,你会拉响它们,你要与你的婚姻同归于尽,你要把所有一切炸得血肉横飞。你想你和老古一定是因为恨才走到一起来的,为了打架这同一个目标才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这样无休止地打下去,总有一天你非得成为烈士不可,不是革命烈士,是婚姻烈士。既然不能投身革命,那就恋爱吧,既然恋爱不行了,那就写诗吧,既然写诗也不自由,那就吃吧,既然吃也不能满足,那就吵架吧,拼命地吵架,永远吵架,没完没了地吵架,吵累了歇歇再吵,一直吵到生命最后一息。你认为婚姻,婚姻真是一种让两个人在一起等死的制度。
有一年冬天在你们打架打得最凶的时候,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你的专访。记者在文章里还提到老古,并且让你自己站出来说了说话,你的话是放在冒号引号里面的直接引语,李洁抒喝了一口茶,微微笑着说:“我有一个知心爱人……”报纸出来,你气得肚子疼了一整天,你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嘛,怎么能这么写?没想到老古却说,这样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第二天你去办公室,有好几个同事向你提起这篇文章,提起那段有关“知心爱人”的话,你这才知道有一首正在流行着的歌就叫《知心爱人》。当有人问起你胳膊上的青色伤痕是怎么回事,你真想如实相告,是知心爱人打的。
你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邵乙,辗转来到现在你所在的这座城市里打工并成家,你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你们是有一年都回父母身边过春节时在你们上过学的那所高中附近的一个超市不期而遇的,你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你们都远离父母在同一个遥远的城市里生存着。你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和地址。等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邵乙就主动而频繁地和你联系起来,每次打电话或者见面邵乙就痛诉革命家史,说她丈夫如何如何坏,令人发指的坏,竟公开领着什么烂女人回家骈居,花邵乙打工挣来的血汗钱给别的女人买首饰……邵乙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她把你这里当成了妇联或者街道办事处。渐渐地你发现自己其实特别喜欢听邵乙说她丈夫怎么怎么坏,她越说她丈夫坏,你就越喜欢她,因为对比一下邵乙的坏丈夫,你的丈夫老古就显得好多了,简直成了模范丈夫了,老古永远不会是世界上最坏的丈夫,不管怎么样总还有邵乙那样的丈夫在垫底呢,于是对比之下你就觉得自己的不幸减轻了一些,有那么一瞬间你甚至在邵乙面前都觉得自己其实算得上是个幸福女人了,应该好好珍惜才对,能够找到这种幸福的感觉真是不容易呵,是邵乙帮你找到了这种感觉,用她的更加不幸来衬托出了你的相对幸运--好比生活水平不太高的时候,就应该想想万恶的旧社会,现在总比旧社会要好吧,或者想想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现在总比自然灾害时期要强得多吧。邵乙每次向你骂完了她那个狗丈夫,你就感激啼零地对她说,我请你吃饭吧,我请你吃饭吧,我一定要请你吃饭,我非请你吃饭不可。
可是大多数时候,邵乙不向你诉苦的时候,你还是认为你是世上最不幸的女人,你还是想离婚。你去学校总务处开离婚证明开了多次。那个拿公章的中年女人用解剖刀一样的眼睛盯着你,免费给你上了一堂伦理道德课,最后是不肯盖章。你说,当初我结婚时你那么痛快地就盖了章,为什么离婚时你就不给盖了呢?她说,让你丈夫单位盖了章,我们再盖吧,后来又说,让你们系主任签字再来盖吧。你说,我看用不着了,离婚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全国人民都答应,你不给我盖可以,把我逼火了,我找块橡皮泥来自己刻个公章就是了。
前不久,从来都愿携夫人出门的老古突然决定独自出门。先是去了一趟百里之外他上大学的那座城市,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同学。那座城市以牡丹闻名,老古说去散散心,看看牡丹。其实牡丹早在老古去之前很久就谢了。然后老古从那座有牡丹的城市又去了相邻的一个有一个大湖的城市,那里有不少你们共同的文友。再以后老古又从那个有湖的城市去了一处油田,那里也有不少你们共同的文友。老古这样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地跑下去,近半月以后才回到家里来。他这一趟出去估计是由于他觉得婚姻大势已去,看来不想离也不行了,不如出去清清心,所到之处控诉一番,为离婚做舆论准备,就像为竞选总统做巡回演讲一样,当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
至于他看牡丹,也许他不清楚牡丹的花期,真的是奔牡丹而去的。牡丹在你眼里是一种很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花,她简直是一种没有缺点的花,她看上去非常贤良,她生就了一脸福相,艳丽得那么本分、性感得那么实用,吉祥得那么体贴,一副既上得了厅堂又下得了厨房的架势,她很适合栽培在地主的庭院里,盛开在封建士大夫的水墨画里,挂在那种规规规矩的小康人家的堂屋八仙桌上方。她使你想起薛宝钗和袭人。老古不辞劳苦、毫无功利地去看牡丹这个事实,如果用弗洛依德的理论来分析,那应该是折射出了他对某类女人长期存在着强烈的性幻想。
这些年来,在老古眼里,你一直都是女人里面的异类和叛徒,你在水平线以下,那他怎么还不答应和你离婚呢?你真想不明白。你想求求他,再求求他,赶快对我弃之如敝履吧,赶快去当陈世美吧,你看我这个黄脸婆,我已人老珠黄,我已步履蹒跚,我的心理年龄足足有一百二十岁了。
那个叫苏画梁的男人,他在那座南方城市里生活着,他有如花美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