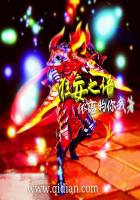“我想去爬山。”月底的某一天,小雨对陈默说。
我看着小雨,忽然失落着发现迷宫的出口已经近在眼前。
“刚才在想什么?”出了上真观的正厅,小雨问陈默。
“在想你想什么。”陈默说。
“是吗?”小雨略显得意地说,“我说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进香的样子看上去很虔诚,让人难免有点触动。”
“什么触动?”小雨问。
“觉得应该真诚地去期待一些东西。”
“你是说应该像我一样跪在神像面前真诚地祈求神医保佑自己永远远离青春痘?”小雨一边走一边做出一副思考的模样。
“好吧,这样想也不是不可以。”陈默无奈地答道。
沿着乾隆御道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两人折向盘山公路,公路绕着山体盘旋而上,外侧是平缓的山坡,内侧是茂密的竹林,偶尔经过一辆载着游人的观光车,也只一会儿的功夫,便如同前面的路一样消失在静谧的山峦之间。
游山的游客聚集在山顶的祈福台上,一眼扫过,人群中有甜蜜的情侣,有幸福的三口之家,还有戴着印有相同旅行社字样帽子的花甲老人。
也许是不想成为别人照片背景的缘故,小雨转过身,趴在拐角处的石栏上顺着山势起伏的方向朝远处望。
看着绵延的林海,我忽然想起穆泽的信,想起她在信中说的那片树林,想起那片树林里她正昂着头盯着头顶上裸露出来的一小片天空。
如果此时的你也和我一样在仰望,那你的视线是否会在我所凝视的地方与我汇合呢?穆泽的问题在我的耳边响起,我抬头望去,只见广阔的天空里了无痕迹。
“谢谢你。”小雨扭过头看着陈默。
“谢什么?”
“谢谢你这段时间陪着我。”小雨说。
“不客气。”陈默说。
“换做别人你也会有同样的耐心吗?”小雨继续望向远处。
“说不准,也许不会吧。”
“为什么?”
“怎么说呢,比如一条线段,需要由两个点构成,起点和终点,可我却连起点在哪都还不知道。”
“起点?你是想弄清楚我怎么会认识你?”小雨问。
“恩。”陈默应道。
“就是说因为好奇才一直陪着我,想弄清楚这个家伙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部分吧。”
“另一部分呢?”小雨接着问。
陈默没有说话,他当然不会站在我的立场把我的理由讲出来。
“好吧,不管怎样,这是我两年来最轻松的一段时间。”小雨笑起来。
“这两年?”
“对啊,对于一个一心想要与众不同却又总是无法如愿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就像……”小雨皱着眉头想了想,“讲不出来,就是很轻松的那种感觉,要不你试着给形容一下?”
“……像是在雪地里打滚,正冻得直哆嗦,然后噗通一声掉进一个温泉里。”陈默想了想说。
“或者?”
“或者像是长满白色的羽毛自由自在地飘在夜空里,随手一摘便是一颗小星星。”
“学得倒是有点意思,总之感觉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其实本来就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地与众不同,更多是相同的,即便是希特勒和爱因斯坦之间,最多也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不同。”陈默说。
“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小雨看了陈默一眼。
“恩。”陈默点点头,接着补充道,“米兰?昆德拉说的。藏在那百万分之一不同里的,才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它,并且好好地保护它,以避免浑浑噩噩地活在那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相同之中。”
“米兰?昆德拉?喜欢文学?”小雨问。
“专业就是这个,再说有的是时间,闲着也是闲着。”
“那说说你的想法呢?怎么才能找到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呢?从你所学专业的角度看。”
“……就以我国当代几个文学流派的演变发展为例吧。”陈默想了想然后说。
“恩。”
“先是出现一个叫伤痕文学的流派,内容多是描写那代人的不幸遭遇。但是写这些痛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后来又出现了反思文学,对这些痛苦加以反思,反思为什么遭遇这些痛苦,从社会到历史到个人,找了很多原因。原因找了很多,可是下面又该怎么办呢?”
“下面就该解决问题了,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小雨接道。
“高中政治一定学的不错。”陈默笑道,“于是接着就出现了寻根文学,光听名字就能大致了解这个流派的宗旨,一批作家试图透过笼罩着这个社会的浓雾找到一种名为根的东西。”
“根?就是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小雨问。
“也不能完全画等号,毕竟他们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他们试图把握的是更具广泛意义上的差异。”
“就是说个人如果想把握到这种名为根的东西,就必须对自己个人的伤痕加以反思?”
“我想是的。”陈默点头道。
“那我们的伤痕又是什么呢?”
“问题就在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伤痕是什么,所以之后的一切都无从谈起。”陈默看着小雨轻声说道。
“寻根文学之后又是什么流派?”小雨问。
“之后是先锋文学,或多或少地立足于所找到的根的基础上,开始试着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强调自我意识。换句话说就是一边努力探寻着自我的外延,一边继续丰富着根的内涵。”
“再后来呢?”
“再后来就多元化了,用一个作家的话说就是发散了,社会在转型,人们考虑问题的重点和方式也在转变,单一的文学类型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了。”
“再后来呢?”小雨问。
“再后来网络就出现了。”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那你在期待什么呢?或者说你希望自己去期待什么呢?”小雨问。
“是啊,我能期待什么呢?”陈默轻声重复道。
两人沿着后山的一条小路往山下走,小路由无数双脚踩踏而出,弯弯曲曲的不时地隐没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或者消失于一片片裸露的岩石上。
夕阳斜下,树影婆娑,顺着山势,两人脚步时急时缓,一会儿手拉手地配合着翻过一道沟堑,一会儿疾步穿越一片平坦的草地。
树丛中夹杂着黄色的雏菊和红色的月季,秋虫在暮色中高声欢唱着自己的歌谣,我回头去看,原先登临的山顶在晚霞的映衬下已经变成了一团灰蒙蒙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