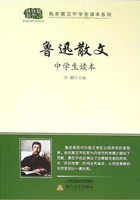我认识赤杰是在2004年的夏天,一见面,这位蓄着络腮胡子的蒙古族汉子就给人以豪爽矿达的印象。攀谈起来,知道他197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1985年底进中水工作,1986年初随造船组去了几内亚比绍,开始是做翻译,1995年起任副代表,在那里干了十多年,加上在西非其他国家“转战”,至2004年春刚刚回来,先后经历了十七年,跑了六个国家。他在中水的工龄和中水的历史一样长,是远洋渔业“元老”级的人物,在几内亚比绍,他的英文名字“奥斯瓦尔多”几乎家喻户晓。可是,在这次见面之前,我却对他一无所知,在我过去所写的关于中水、关于几内亚比绍的文章中也从未提到过他,实在是孤陋寡闻。如今面对赤杰,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愧意。同样的情况如果放在文艺界,难免要碰钉子:“现在才想起来采访我,早干吗呢?”但赤杰不是这样,他丝毫没有在我面前“摆谱儿”,甚至还有些腼腆,好像很不习惯在记者面前说自己的事儿。这似乎也是中水人的共性,他们做得多’说得少,不张扬,不炒作,正因为如此,更赢得了我的敬重。
赤杰和我的谈话,从他所经历的几内亚比绍内战开始。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而他的记忆仍是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
1998年6月7日凌晨4时许,我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几声枪响惊醒。在几内亚比绍,枪声倒也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有时候,连警察抓小偷都会开枪,所以这枪声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见天还没亮,便翻了个身,继续睡去。6点钟左右,枪声密集了,由步枪散射变成了机枪扫射。我感到不对头了,赶紧下床,从窗口往外看,只见满街都是军车和士兵,把马路都封锁了。
代表处的人都起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面面相觑,人心惶惶。自从1990年5月31日几内亚比绍和我国断交,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中水代表处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坚持了整整八年,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好容易等到1998年4月23日两国复交,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我国使馆的房子还在装修,使馆人员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洪宏大使去几内亚开会,前脚刚走,没想到就出了这样的事儿。
好容易等到织网的黑人雇员来上班了,于是急切地向他们询问,说是昨晚有人刺杀总统未遂,剌客当中有几个人被击毙,还有三个人往机场方向跑了。代表处的驻地在机场路,正是他们的必经之途,所以昨晚这里的马路被封锁就在情理之中了。
8点钟,电台的新闻播出内政部长的讲话,说有人对总统行为不端,政府正在清剿,希望市民不要外出,以保证安全。黑人雇员所说大体得到了证实。接下来传出的消息更详细些:六个月之前,尼诺总统解除了总参谋长安苏马内马内的职务,但一直未任命新的总长;本月5日,也就是前天上午刚刚任命了新的总长,今天,原总长安苏马内马内就发动了兵变!
得到比较可靠的消息之后,代表处向拉斯帕尔马斯作了汇报。那时候,代表韩仍已经回国,孙锡江是从毛里塔尼亚调来任代表,我是副代表。拉斯办指示:代表处人员不要外出,静观事态的发展。
上午10点,军队开始在街上布置重武器,82无坐力炮,重机枪都用上了,车辚辚,马萧萧,一片肃杀之气。中午1点钟,大炮轰响,一颗炮弹落在代表处门前,把树都烧着了。街道上乱哄哄的,很多人拖儿带女,头上顶着东西,从乡下往城里跑,据说城外已经被前总长安苏马内马内领导的叛军控制,正在和政府对峙。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看商店的傅健,为安全起见,中午不要回代表处吃饭了,反正商店里有方便面。这个商店是在两国断交之后,于1992年成立的,叫“东方合资公司”,经营水产捕捞和加工业。
就这么惶惶然过了一天一夜,到了6月8日凌晨4时,枪炮声更加激烈了。我和孙代表商量,看这个架势,仗越打越凶了,我们是不是准备撤离?经请示拉斯办,同意我们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决定由孙锡江任总指挥,我任前线总指挥。于是,把代表处的人员叫到一起,采取防火防爆措施:把六根消防水龙带全部铺好,所有泡沫灭火剂、干粉灭火剂都搬出来,放在外头,游泳池里放满水。焊了个大约一立方米大的铁箱子,把代表处的仓库库存清单、财务账目和大家的钱一共10万美金都藏进去,挖一个深坑,埋好了,填上土,上面再作好伪装,以保万无一失。同时,把工作船调到港口外待命,做到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载人撤离。
6月9日,街上的人流明显加大了,我们感到情况不好,决定让家属先撤,留下八个人看仓库:孙锡江、余举文、傅健、王宝旭、褚士杰、刘洪祥、王守水和我。到晚上,战争双方已经出现伤亡,拉斯办指示我们撤到城里。当时,城里的宾馆、饭店都已经被外国使馆、使团租用了,老百姓则拼命往教堂里挤,里里外外聚集了几万人,跟蚂蚁搬家似的。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商定一些当务之急的事儿,赶紧做了一面红十字旗,请示了使馆,同意我们挂国旗,就焊了个旗杆,在车上插上使馆用的小型国旗。使馆也决定除二秘苏健留下,其余的人都撤,销毁机密文件。6点钟,俄罗斯使馆给我们打招呼,他们要进城。听电台广播里说,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城。于是我们决定马上撤,晚饭做好了都没来得及吃,把米饭、馒头、熟食全带上,怕到了城里缺吃的,还分头去买了很多饼干。
我先开车到码头去看看情况,那里已经被两千多名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军队控制,根本不许民用船只靠港。当时葡萄牙的万吨运输船“撒格雷斯”号就被拦住,进不了港,这时候谁发话都不行了,部长、总理的指示都没人听了,就像我们曾经在“文革”中用过的词语,政府机构已经“瘫痪”了。
教堂里的老百姓已经被困三天了,四五万人也不止,岂是长久之计?6月10日上午,他们冲破了封锁线,往码头上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赶紧开车去码头。码头上人满满的,又没有栏杆,当兵的围成人墙,一个挨一个,拦住老百姓,那艘停在海上的万吨轮“撒格雷斯”号虽近在咫尺,却比登天还难。叛军不断往这里打炮,炮弹落在海里,激起一个个冲天水柱,那景象,你在电影里看到是一回事儿,现场亲身经历是另一回事儿,每当水柱溅起一次,你都会暗自庆幸这一炮没有落在自己脑袋上,但是下一炮又往哪儿落?谁知道!12点钟,开始打火箭炮了,每次都是四五个水柱同时开花,真厉害!
我和俄罗斯使馆的人一起到海关去商量:我们的船已经到了,能不能让我们的人都进去?这时,通往码头的一个小门已开了,葡萄牙和法国的车都开进去了,他们是奔“撒格雷斯”号去的。有了这个先例,海关就没有理由再拦我们了,只好让我们提供名单和护照号码,我负责登记,除代表处的人之外,俄罗斯使馆的人,日本使馆的人,都来搭我们的船,此外还有十名中国侨民,是刚到比绍来打工的,就赶上逃难了,加上他们一共是六十九人。
12点半了,我们的船还没有靠岸。我对海关人员说,你现在不让靠,一会儿涨潮了,想靠也靠不成了。海关人员说,给你五分钟,快靠快靠!我赶紧用对讲机通知船上,马上靠岸!这时候,真不巧,一发炮弹“咚”地落下来,离我们的船只有二十米,把船长震懵了!时间不等人哪,轮机长赶紧把船开过来,一靠岸,这边儿赶紧上!妇女、小孩儿、老人先上,最后男的也上去,统统拉走了。
这时候,拉斯办已经派了运输船“海丰”830开往几内亚比绍,前来接应,同时命令在周边国家海域作业的船,单边带二十四小时开机,这边一旦有情况,立刻赶来营救。我通知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转告各国使馆,让他们到达喀尔码头接人。我们的“海丰”830是一艘冷藏运输船,虽然比不上客轮舒适,但在战争时期,那些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的外国人能够得以借此逃生,已是万幸了,不仅免费乘船,连吃饭也不要钱。而据事后听说,那些上了葡萄牙“撒格雷斯”号的两千多人,航行了好几天,竟然无水无饭,也不知是怎么受的。在这次抢险中,我们的“海丰”830上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插曲:一位俄罗斯孕妇上了这艘船,她腹中的婴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逃难途中来到了人间,幸而没出任何意外,母子平安,那妇女感激不尽,给孩子取名叫“海丰”。据说,船到达喀尔时,有关国家的使节都来迎接,码头上飘动着各国的国旗,一片欢声雷动:“中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