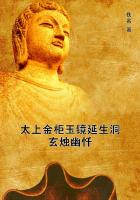自那天大火以后,庭羽时常觉得眼睛疼痛难忍,直到有一天再也忍不住了,才说:“娘,我眼睛又痒又痛。”
“那是药的缘故,你忍着一些。”蝶衣柔声道。其实来到这里后,庭羽的眼睛根本无药可换了,他受的疼痛也没药可止。
“有东西刺眼睛。”庭羽说,用手抠着纱布的下方。
蝶衣仔细检视了一下,发现庭羽蒙着眼睛的布有些松动,边缘翘起,便替他整理了一下,问:“还痛么?”
“不了。”庭羽摇头。
蝶衣立即将庭羽拉到房间暗一点的角落,轻轻用手将纱布再揭开一些,问:“现在呢?”
“痛!”庭羽缩了一下,道:“像刺一样的痛。”
蝶衣心中抑不住一阵狂喜,她用手挡着庭羽的眼前,问说:“好些没有?我帮你拆开纱布试试。”
庭羽点了点头;蝶衣就试着将整个纱布拆得只余一层,庭羽惊叫一声,用手捂住了眼睛——现在,他的眼睛对光已十分敏感了。
蝶衣见状,又是心疼又是惊喜,她赶紧关上窗子,然后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庭羽,颤声道:“小羽,把手拿开,慢慢的。”
庭羽一点一点移开手,闭着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一条小缝。却又用手挡在眼前:“很疼,我不拿开!”
蝶衣见他如此难受,便想着自己是太心急了,连忙道:“好,今天先这样,明天再拆。”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清晨时分,庭羽终于除去了全部的纱布,小心地睁开了双眼,除了针刺般的痛和炫得他头晕的光芒,庭羽眼前的一切还模糊着,但却能看见母亲模糊轮廓。
庭羽伸手摸去,道:“娘,是你吗?”
蝶衣喜极而泣,道:“是我,是!孩子,你看见了吗?”
庭羽伸手过去,方向约摸是对的,他准确地摸到了母亲的脸。蝶衣早已按捺不住,一把握住了他的手抱着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太好了!你终于能看见了,太好了,我的小羽……”
这样的喜悦对于蝶衣来说掺杂了更多的心酸,庭羽能看见了,但现在摆在他眼前是却是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没有亲人,没有自由,只是一个圈禁他们的狭小院子。
从这以后的几天,庭羽的眼力每天都有进步,起先只是看到大概的影子,后来越来越清晰;渐渐也能分辨出远近。
他眼里的母亲一天一天地清晰起来,在完全能看清她脸的那一天傍晚,庭羽贪婪地盯着母亲的脸,足足半个多时辰不愿意移开。
他从小就由母亲亲手照顾,对她极其眷恋,心里总是在想要是眼睛好了,见的第一个人一定要是母亲。现在家人失散,眼前能见到的却只有母亲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矛盾。
深夜的时候,他还会暗想是不是因为自己这样想过,所以才会导致家里其他人都不见了呢?
庭羽并不敢将自己这些想法告诉给母亲,他只是看着母亲的脸说:“娘,对不起,是我不好。”
蝶衣憔悴不已,强作笑颜地道:“说什么傻话呢?好好的瞎道歉作什么?”
庭羽低下了头,仍是放在心里不敢说。然后,他看见了母亲隆起的腹部,立即惊恐地道:“娘,你生病了吗?”
蝶衣心酸地笑了,低头抚着腹中的孩子,安慰他道:“不是,里面有个弟弟,再过一些时日,你就可以看见他了。”
庭羽吃惊地看着,然后道:“就像恪文一样吗?”
蝶衣点点头,突然说不出话了。
庭羽提到恪文,她便想起他们的安危:恪文和小昭还那么小,他们在哪里?是否平安脱身了呢?是否有人照顾他们?还有丈夫是生是死?为什么这么多天过去了还没有来救她们母子?
突如其来地想到这么多,蝶衣终于再也支撑不住,眼前忽然一黑,昏厥过去。
庭羽吓了一跳,摇着母亲喊,却一直不见她醒来。庭羽喊了她一会儿,连忙扑向门边,趴在铁窗栏前大喊外面的护卫求救:“快来人救救我娘,我娘病了,她病了!求你们快来救我娘啊!”
那些御林军护卫每天守在这里也无聊,这石屋又极其坚固也不用担心他们能逃得出去,所以他们通常坐在另一个大院子的花园里吃饭喝酒赌钱,过了很久才听到庭羽在这边的喊叫,那时庭羽已不是在求,而在是在哭喊:“有没有人在啊?听不到吗?快来救救我娘!”
来的两个护卫老早就想将他解决,见此时蝶衣昏倒正好也是个机会,于是打开了门。庭羽顿时如见了救星一般,赶紧回到母亲身边抱着她,还没走两步便听到那人喊他:“小崽子,你过来!”
庭羽自然地回头,还没看清是谁肚子便挨了一脚,踢得他飞出老远跌在地上。他连忙爬起,却只觉得头一沉,他头上结实地挨了一铁棍。
一阵闷痛袭来,庭羽本能地捂着头上痛处,便感觉有一股奇怪热流在手心下喷涌,他恍惚着将手拿下来看。
复明以来,他看到的第一样深入脑海的东西是母亲的脸,第二件便是自己的血——粘腻,浓稠,刺目地鲜红着。
恰此时,昏迷的蝶衣惊醒了,一眼便看到了进来的护卫,接着便看到地上满脸鲜血的庭羽。一种天生母性的本能,令她在瞬间由虚弱恢复到强悍,如发怒的母狮子一般扑过去将儿子抱在怀里,迅速拔出来短刀朝那持铁棍的护卫掷去,正中他左胸,当场倒地毙命!
蝶衣一手抱着庭羽,另一手拔下头上的发钗,尖利的钗尖对着自己的咽喉,对另一护卫厉声道:“不要脸的东西!竟敢动我儿?你再过来试试!滚!滚出去!”
那护卫被刚刚这一幕吓呆了,生怕她自杀,便一步步后退,嘴里还说:“好!我出去,夫人你千万别……”
蝶衣命令道:“把那该死贼人也带出去!”
那人只好又将同伴的尸体拖了出去,关上了门。
蝶衣这才赶紧将庭羽的头放在自己腿上。庭羽已失去知觉,他右额头上被铁棍边缘击破了一个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
蝶衣见他满头满脸的血,生怕他就这么死了,急得边哭边找东西包扎。她脑海回想着段延俊教过她的包扎术,便拿她用来给未出世孩子缝衣用的针线,十个手指抖抖索索,将庭羽破开的头皮缝起来,每扎一针,便犹如扎在自己心上。
蝶衣心疼泪水一再遮住了视线,她边缝边哭,一边不住地对早已昏死过去的庭羽说着话:“小羽,好孩子!你忍着点,马上就不疼了!你一向很听话的,千万不要离开娘……听到了吗?”
摇曳的灯影下,庭羽的血流了蝶衣一身,蝶衣的泪也流了他一身。
但庭羽总算命大,昏迷了四五天终于还是醒了过来。这是他额上第一道伤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