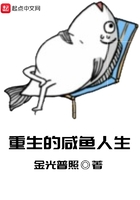天宇三十三年,京城里爆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通天老者的身份查到了!
沉寂了十年的长安城,一朝如同热锅里的水一般沸腾起来,水里的尘土旋转,杂糅,变得浑浊,看不清水底到底埋藏着怎样一个真相。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聚集向那个爆出消息的书坊。在书坊门槛被踩断的当天晚上,书坊一家主人收拾铺盖逃之夭夭。第二天一早又上门的人们,只看到满堂空空荡荡,和留在正堂墙壁上一个雄浑有力的大字。
陆!
陆?通天老者竟然姓陆?说起来,京城里姓陆的神神秘秘的一个家族不就只有哪一家么?
这样一猜测,再对上那句:陆氏不倒,燕国难兴。似乎更加契合了……
莫非通天老者那个陆,正是陆家这个陆?
如若不是,为什么这些年外人只见陆家荣华富贵不绝,却如何也弄不清楚陆家究竟官秩几品,又隶属于谁?
到了今天,原来那个通天的陆家竟然还存在着!并且,他的占卜观星预知未来的本事一定是真的!否则,谁又能解释皇帝一直将他们这样雪藏着的事呢?
一时之间,京城便翻天了。
没过半天,陆府门口便挤得人山人海。
“陆大师,替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捡到金元宝啊!”
“青岚公子,替奴家算算奴家肚子里的是男是女啊!”
“陆少爷,快出来啊,我想知道我爹什么时候死啊!”
不到晚上,陆府紧闭的大门外竟然摆起了香案,供起了香烛,猪头牛羊肉之类的。
信徒们默默跪在外面,紧紧盯着那扇朱红色的大门,眼睛都不敢眨。
其实他们未必什么都信,但是一本许多年前的古书,皇室对陆家暧昧的态度,青岚公子那副得道脱尘的气质……这一切都在无声地重锤着这些老老少少的耳膜,听着,青岚公子是通天老者之后!陆家是奉了上天的命令传达上天的旨意的!哪个不相信就要遭天谴!
不知何时,茶楼酒馆里就出现了许多能说会道的跑商似的人物,大肆散播着陆家通灵的神迹。不知不觉的,这样的传闻就开始广泛流传开来。经由说书人添油加醋地一讲,陆家就变得更加神秘莫测,而那京城第一公子也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却又头顶着神圣的光环,令人只敢仰视,甚至不敢再叫他的名字。
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变得越发厚重肃穆起来,仿佛也染着一圈金光似的,连带着哄他们走人的开门小厮都仿佛是道童一般,变得带着几分高不可攀的仙气。
慢慢的,一直作为忌讳不被任何人提起的嘉建之乱也隐秘地传扬了开来,年轻一辈的人好奇心又重又喜欢显摆,那场鲜血染红护城河的祸事被悄然提起,悄然扩散,悄然地改变了许多人对当今皇室的看法。
原来……帝王之乱可以弑父囚兄,惨烈到如此地步。那现在的这个继承了嘉建帝血统的嘉灵皇帝,是否……应和天命呢?
谣言一起,便如同星火一般,极有燎原之势。
朝野上下表面安宁,底下夹杂着什么泥沙却又是另一番说辞。
龙涎香弥漫的正宫寝殿,昏暗的光线照进室内。穿着蓝袍的青年恭敬地垂首站在床上,明黄的床榻上一个中年男人微微眯着眼,浑身却散发着强烈的慑人的气势。
“儿臣不明白。”那青年道。
嘉灵帝哼了一声,道:“有什么不明白就问。”
“是。父皇,你当初逮到陆印,为什么杀了他,却留下了陆青岚?这岂不是斩草不除根,留下了今日的祸患?”青年焦灼地反问,透出他心中的积郁是多么急切地想要吐露出来。
嘉灵帝道:“陆印不是正统的继承人,他会的,只是卖弄他手里的那几本书而已。但是陆青岚这个人,却极有可能是陆家老祖的继承人。他继承了老祖的卜算能力,十年前那几本泄露天机的书就是从他手里流出去的。”
“是那场来的蹊跷的瘟疫!”青年眼中一亮。
嘉灵帝却是摇了摇头,“包括后面的流民偷袭长安。”
“父皇,”青年皱眉,“流民乱不是妖人作祟么?天帝发难,弄得富庶江南民不聊生,朝廷发给难民的银子被暗中克扣殆尽才引发流民****,这与河川府的瘟疫又有什么关系?”
嘉灵帝斜着眼睛看了他一下,道:“长荣,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
青年一顿,“儿臣不知,请父皇示下。”
嘉灵帝转过头去盯着头顶的熏香小球,“论聪明才智,机关算计,你拍马也赶不上长幸;论阴狠毒辣,用人之术,你比长曜也远远不如。”
青年面色沉了下来。
嘉灵帝嗤笑一声,又道:“但朕却始终觉得你才是做皇帝的料。聪明?又不是考状元。阴狠?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皇帝的资质未必要过于优秀,有时候中庸才是最好的。进一步是聪明,退一步是阴狠,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高深莫测的君主。”
“所以,”嘉灵帝邪佞一笑,“其实你没有必要给我下毒的。”
青年神色一瞬间有些惨白,好半晌才捏着拳头狠狠道:“你也会是我踏上那个位置的阻碍!”
嘉灵帝哼了一声,声音已经比之前那中气十足虚软了很多,“蠢货,你现在只是在斩断所有的助力来源而已。”
青年义愤道:“父皇,儿臣明明就是太子,你早该让位,否则儿臣怎么会需要应对今天的局面?”
嘉灵帝道:“让位?你以为那个位置你坐得稳?”
青年道:“你不让,结果还不是一样?”
这话题已经偏离了。
一个身影从正宫偷偷溜出来,一边注视着周围又没有人,一边快速地往后宫跑去。
“他走了。”皇帝的精神懒洋洋的,但全不是刚刚那副有气无力的样子,那双眼睛里划过的精光已经锐利。
青年垮下肩膀,抱怨道:“他怎么听了这么久,再不走,儿臣就要露陷了。”
皇帝却看着他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不,你演的很好。你让我觉得,你心里就像你嘴上说的那样想的。”
室内的气氛一僵。
一种可怕的感觉震得青年瞪大了眼睛。
“啊,父皇偶尔开个玩笑而已,不必认真。”嘉灵帝哈哈笑了起来,神色间一排轻松和缓。
青年也陪着笑,衣袖下的拳头却暗暗握了起来。
“怎么样,有消息吗?”魏北悠看着疾步走过来的小兵,焦急地问道。
小兵艰难地摇头。一天被嫂子问上十七八遍,他心里也压力特大,他也期待着前面赶紧传了消息回来,然后自己笑眯眯地告诉嫂子,然后劝嫂子去休息,而不是眼含期盼地看着门口,一坐就是不吃不喝地一整天,那脸色苍白的他都看不下去。
天宇三十三年十月,皇帝终于下旨派遣云镇云驿父子俩率领威震天下的镇东军去对抗西疆越来越强大的兵力。临走之前云驿只是深深回望了一眼魏北悠,没有给她任何的承诺,那个时候,她心头就一直跳动着极其不详的预感。仿佛这一别,就成永诀。
小兵不给消息,她只能盼着南桥回来。
镇东军离开的时候,南桥被云驿强硬地留了下来。
南桥知道云驿是什么意思,魏北悠也知道。
只是这样的知道却总让南桥和魏北悠无法对视,这样的知道太残酷。
云夫人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这是第一次云镇去完全不熟悉的地域打仗,东虏和西镜到底是不一样的,一个属于以边境海洋为生的渔业国家,一个属于以游牧业为生的国家,如何出奇制胜,如何善用兵法,全都要从头打算。
这也是第一次云镇已经连续一个月不曾派人送信儿。
仿佛是失踪了一般,两边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样的情况下,魏北悠不可能做出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云夫人也是同样的心情。两个女人守着空荡荡的饭桌,说着口不对心的话,神思早不知哪里去了。
唯有小糖豆故意逗趣的时候,云夫人和魏北悠还会笑笑,其余的时候,两个人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了。
小兵看到小糖豆蹲在地上握着树枝画画,不由好奇地问,“你在画什么?”
小糖豆眨巴着眼睛,低声道:“画爹和爷爷,等娘和奶奶看到了,就不会不开心了。”
小兵听了,当即泪如雨下。却又不敢哭出声来,只是蹲在那里,一抽一抽分外可怜。
小糖豆过去拍拍他的后背,安慰道:“哥哥你别哭,爹爹爷爷都会回来的。他们说了,小糖豆只要乖乖的,他们就会回来了。哥哥你放心,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很想爹爹和爷爷,小糖豆也很想很想很想。但是小糖豆不会哭,小糖豆会很乖很乖的。”
云夫人的泪终于窜入眼眶,打湿了衣襟。
看着魏北悠,云夫人又觉得心疼,把她拉进怀里抱着,眼睛却望着小糖豆,“悠悠,给小糖豆生个弟弟吧,或者妹妹也好,他一个人……。”
魏北悠的眼泪一串串的滚落下来,却勉强笑着,“好,听您的。等云驿回来……等云驿回来……我们就生……。”
一个院子里站着的士兵都红了眼圈儿。
他们只恨自己武艺低微,不能跟随将军上阵杀敌!
“南桥?”魏北悠忽然扫到站在门口的身影,猛地站了起来,疾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目光茫然地在南桥面无表情的脸上扫视着,“他们……。”
南桥对上云夫人,“接到信儿了,云大将军他们一切正常。”
魏北悠却敏锐地抓到南桥话语里的漏洞,“云大将军?那云驿呢?那呆子傻木头呢?”
所有人都急切地望着南桥。
南桥望着魏北悠沉默。
魏北悠退了一步,带了一丝绝望地笑道:“他……怎么了?”
“说啊!”魏北悠嘶叫着哭了出来。
“云驿将军,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