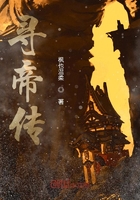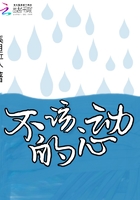且说母亲看罢小儿子寄来的信后,急忙赶来华沙接他回家。离开华沙前,这位崇高的母亲还特地去罗赛琪教授家告别。教授倒是对她抱怨了不少,说什么孩子上课不用心啦,他深感失望啦,这样的学生前途渺茫啦,等等。一席话把母亲说得垂头丧气,连连叹息。母子俩就这样灰溜溜地乘火车返回了罗兹老家。
这时,父亲的手摇纺织工厂在机械化的大纺织厂的冲击下,已经宣告倒闭。他把住房和工厂等家产都变卖一空,偿清了债务,从此贫困潦倒,厄运连连。鲁宾斯坦的父亲被迫在楠山·傅尔曼家借住,屈身在他的工厂里当一名会计。每天除看看书外,变得沉默寡言。鲁宾斯坦的母亲也在一年之内变得苍老了许多。繁重的家务又加剧了她那慢性支气管炎,终日咳个不停。这一对苦难相伴的夫妻虽然痛感家道中落,但对长到10岁的小儿子的教育依然抓得很紧,不敢有丝毫放松。他们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把小鲁宾斯坦送到柏林学艺。
3柏林起步
几天之后,小鲁宾斯坦便跟随母亲到了柏林。母子俩寄住在姨妈莎罗蜜娅家,这位姨妈和姨父赛格佛瑞共生育了四个子女。
柏林,原先是一个小王国的京城,到1871年即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1900年,柏林市在文化艺术生活的品味上已经大大提高,拥有不少的一流戏院、歌剧院和专门上演古典戏剧的皇家剧院,还有一批优秀的歌唱家和名演员,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演奏会。
母亲领着爱子上门拜访了柏林著名的钢琴教授和钢琴演奏家霍夫曼父子,还给他们一一试弹过。由于这些人收费高,负担不起,母亲最后决定再去走访约克琴院长。这一回院长照旧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母子俩,显得和蔼可亲。他用自己特有的浑厚、柔曼的男低音对孩子说道:“请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给我听,好吗?”小鲁宾斯坦欣然应命,弹了一首A小调回旋曲。教授听了微微笑,又点点头,他随后出去,拿来一块高级巧克力。接着,教授又请母亲去另一间房里单独谈话。母亲出来时喜形于色,甚至高兴得淌下了泪水。原来这位院长决定亲自指导小鲁宾斯坦的文化与音乐教育工作。
几天之后,约克琴院长正式通知母亲,说他已组织了一个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四人基金会,凑足了培养“小天才钢琴家”的大部分经费。基金会的其他成员是业余大提琴家劳勃·孟德尔松、银行家劳勃·华绍尔和退休商人马丁·李威。李威爱好谱写弦乐四重奏曲子,还经常举行宴会,参加宴会的多系普鲁士封建王国的名门望族和柏林的外交界人士。小鲁宾斯坦也经常受邀去为他的贵宾们献奏。
约克琴教授并不富有,他纯粹是出于培养人才的道义责任而慷慨解囊的。他订了一项规章,要求母亲不把天才幼儿当成一棵摇钱树,指出在孩子艺事成熟之前,必须完成正规教育。母亲对院长的嘱咐自然是千恩万谢,满口答应了。
经约克琴院长的推荐,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钢琴教授亨利克·巴斯同意接收小鲁宾斯坦为学生,而且不取分文报酬。此外,巴斯教授还主动承担有关培养学童经费的处理事宜。
两位教授跟母亲反复协商,最后取得了共识:不送孩子进正规中学念书,就在家里请老师补习普通中学的课程,学生必须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学同等学力考试,食宿则租用普通民宅。
母亲在把爱子的学习、生活都安排好后,便高高兴兴地回罗兹家里去了。从此,小鲁宾斯坦便开始了独立生活,“小天才钢琴家”也就在柏林正式起步,此时,时间是1898年,他才11岁。
师生达成如下协议:
在音乐教育方面,亨利克·巴斯先生亲自执教,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地点是在教授家里。此外,小鲁宾斯坦还得跟巴斯的学生、西班牙人米奎尔·柯隆智学习大学音乐系的预备课程。经由约克琴院长出面协调,小鲁宾斯坦又获准在该院选修音乐理论、合声和乐器合奏等课程,有时还在约克琴教授主讲的小提琴课上协助伴奏。这就为他进入小提琴的知识领域提供了机会。
在文化教育方面,聘请了席尔多·奥特曼先生主讲全部中学课程,规定每天上课两个小时。
奥特曼先生40岁上下,身材魁伟,一头典型的德式短发,国字脸,眼里闪射出智慧的光芒,高挺的鼻梁上架一块钢丝夹鼻镜片,透溢出满腹珠玑而又慈善温爱的长者形象。小鲁宾斯坦一见就喜欢上了他。在幼小的心目中,这位家庭教师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好人”。
奥斯曼先生主讲的全部中学课程是:德国历史、地理、拉丁文,还有令孩子深感头痛的数学。他讲起这些课来往往妙趣横生,深入浅出,极易理解,经久不忘。他巧妙地将小鲁宾斯坦的眼界循序渐进地边开拓边引导至生活中不断变化着的美景,深入发掘人生那辉煌壮丽的本质,并极力培养孩子勇敢地面对纷争不断的复杂人世。
在上历史课时,奥特曼先生扬弃了枯燥的书本,引领孩子经历了人类各个世纪的长廊,为他揭示人性的弱点对当代所产生的后遗症状,同时鞭挞了人类对权势的贪婪与交往的险诈。
在讲授哲学课时,奥特曼先生为这个天才少年开启了理性的心扉,展示了人类的伟大哲学家们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和叔本华等的卓越成就。师生采用讨论式教学,潜心研读了尼采的《苏路支语录》。小鲁宾斯坦十分欣赏他那优美的散文体。他对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深为赞许,认为作者在书中精辟地阐述了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差别。
在研读文学课时,奥特曼先生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参观人类的文学殿堂,让他去熟悉并品评歌德、海涅、克莱斯特、巴尔扎克、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年方11的小鲁宾斯坦被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所深深打动,心灵的视野大大开阔。
不过,上起数学课时,这个“乐坛神童”便提不起精神,甚至会无端烦恼。小鲁宾斯坦常常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还要我来求证这些伟大的原理?我都完全信服了。”考问急了,他就会大声抗议:“你很了解,我即便对高深数学一窍不通,也阻挡不了我未来理想的实现呀!”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交锋后,奥特曼博士在征得巴斯教授的同意,停止了上数学课了。
小鲁宾斯坦无限崇敬执教自己中学课程的奥特曼老师。是他,开启了这位异乡少年的智慧心扉,提供了妙绝的思想启蒙;是他,让这位热爱自己祖国的波兰少年出席了柏林的各种各样学术讲座和高智商集会。在奥特曼执教的4年期间,小鲁宾斯坦聆听了众多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精辟论述和生动演说。他们都为这位未来的钢琴演奏家灌输了各种学说的精髓,教会了他“如何思维”。他把这一切都视为“天赐洪恩”。
一天早晨,奥特曼先生递给学生一张入场券,是葛哈德·霍普特曼的新作首演入场券。那天上演的新剧是《露丝·伯恩德》,在柏林引起了轰动,人人都以争睹为快。观众席上名流满座,舞台上演员的演技无懈可击。小鲁宾斯坦看了这场新剧后,一时眼界大开。散场后走出剧院时,小鲁宾斯坦却发现奥特曼先生伫立街头守候着他,还要他转告当晚的演出经过。孩子事后才了解到,原来奥特曼先生当天只买得起这一张票,但他情愿自己不看不听,也要让弟子去大饱眼福和耳福。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观看名剧演出,都极大地启发了少年的心智,逗起了他对知识的渴望。这样,小鲁宾斯坦便把大量的心思,都投入到了奥特曼的魔方世界中,同时把德、俄、英、法、意大利和波兰的文学作品都用原文一一啃完。这就必然影响到正常的音乐教育,少年虽然每周两次上巴斯先生的钢琴课,但已是精力不集中,心不在焉了。巴斯一怒之下,辞退了奥特曼,理由是他的能力有限,而且剥夺了少年的正规练琴时间,影响很坏。小鲁宾斯坦被迫与恩师挥泪话别,心里极不痛快。
巴斯教授看上去有60开外,他高大肥胖,须发斑白,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隐隐露出那不容冒犯的威严,令人望而生畏。但他乐业敬业,对鲁宾斯坦那份弹琴天赋,倒是激赏有加。他那张忧郁、严峻的脸上,偶尔也会露出一瞬温馨的眼神和一丝孩子般的虚怯微笑,尤其是当爱徒弹奏精彩的时候。可是,如果鲁宾斯坦没有备好课就冒冒失失地上他的课,那准会挨一顿训的。他每弹错一个音符,巴斯教授的短髭就会翘高一分,等到翘得上齿咬着下唇时,那就要大发雷霆了:双脚跳起,一顿臭骂,拳头砸得琴盖砰砰响,然后跑出房去。稍等一会儿,待心气平和了,他又会悄悄地回来,扳起一副脸,挥手打发小鲁宾斯坦回家了事。
另一位音乐辅导老师米奎尔·柯隆智的教学风格就大不一样了。他才30出头,眸子湛蓝湛蓝的,常常流淌出一泓爱波。他弹奏古典音乐时,绝对没有习见的那种刻意夸饰“感情深度”的忧郁表情,尽管那种表情是德国音乐界所推崇的,也是乐评家们所最为欣赏的。音乐,在柯隆智看来纯粹是一种娱乐,他也乐意与被辅导的学生一道分享。有时,他们师徒俩会兴致勃勃地合奏一曲四手联弹的舒曼交响曲或贝多芬四重奏,而且一边弹琴一边口嚼随身携带的巧克力。最后的压轴曲常常是柯隆智独自弹奏某一西班牙的流行乐曲。这种教法,才使少年鲁宾斯坦感到“十分过瘾”。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能常在。巴斯教授认为这个西班牙约卡岛人的行为出格,也不甘心师徒的关系过于亲密,便找了个借口把柯隆智辞退,换上了一位老处女克拉若·韩柏小姐来补缺。韩柏小姐也曾经是巴斯教授的得意门徒,她遵照严师训导,多方限制鲁宾斯坦的活动,告诫他只能踏踏实实地认真学习,练好那些刻板要命的音阶,“忘掉在弹琴中寻找无谓的快乐”。
巴斯教授的教法就更是严苛古板了,他要求小鲁宾斯坦练习的,都是一些老掉了牙的曲子。这些曲子多半是巴斯年轻时流行的,如今早已老朽不堪,逗不起孩子练习的胃口。在上钢琴课时,巴斯通常要孩子练习蒙特威尔地或舒曼早期并不那么走俏的曲子。作为妥协,接着便教弹一首贝多芬的浅易奏鸣曲;熬到最后,他才准许弹一首巴赫那美妙绝伦的前奏曲和遁走曲。所以对小鲁宾斯坦来说,这种练琴生涯太枯燥乏味,委实愁煞人!
小鲁宾斯坦在柏林的生活始终是紧张而有节奏的。1898年和1899年的夏天,他曾经小别柏林,回罗兹老家度过了两次短暂的假期。全家人见到这个远方游子琴艺进步,身体健康,全家欢天喜地,大搞起庆祝来。父母亲为爱子做了一大堆爱吃的食物,为的是给他补一补身。日子过得特别快,短暂的假期已告结束,小鲁宾斯坦又在一片泪水和祝福声中,被送回了柏林。
从1900年起,小鲁宾斯坦便被剥夺了暑假回罗兹探亲的权利,巴斯教授利用这短暂的假期来强化少年弟子的演奏能力,每天师徒一起练习所有能找到的双琴合奏钢琴曲。当时小鲁宾斯坦满心的不快。多年之后,他才感悟过来,才认识到这位乐坛导师“损己利徒”的高风亮节,为培养自己成材牺牲了个人休息,耗尽了心血。
打这时起,巴斯教授也变得通融了许多。作为习艺的监护人,他不仅对少年弟子更加友善,练完琴后还经常留下小鲁宾斯坦共进午餐,而且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必要改革:针对这孩子不愿学数学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了中学同等学历的鉴定考试;同时采纳约克琴院长的建议,改授法文和英文,分别由巴斯和奥特曼主讲,每周各为两次。多年之后,鲁宾斯坦深感这种教学改革很有必要,因为语言是钢琴演奏家必须掌握好的最重要手段,改革体现了巴斯教授在教学上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