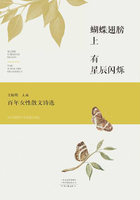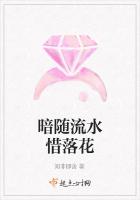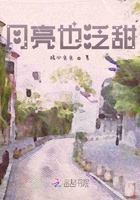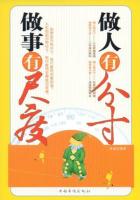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满口白牙。
文化界、美术界的人们都知道石鲁的大名,因为他是着名画家,更因为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也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因为摄影界只能勉强归类于文化界,所以大多数摄影人知道石鲁的大名,是因为这张摄影名作《画家石鲁》。
这张传神之作拍摄于1977年4月。那时“四人帮”刚倒台,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被整死的艺术家尸魂无处,没被整死的刚刚从牛棚里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石鲁在”文革”中被整得奄奄一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77年到通县北京结核病院来治疗,5年后他还是死于肺结核,时年仅63岁。
石鲁,中国现代着名国画家,1919年生于四川仁寿县,1982年卒于西安市。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作品具有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内容多以人民生活和重大题材为主,在美术界影响巨大。曾任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早年曾在延安大学任教,还写有电影《暴风中的雄鹰》,拍摄后受到好评。他精于诗、书、画、印,出版有《埃及写生集》、《石鲁作品选集》、《国画选》,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他的作品以“野、乱、怪、黑”着称。
李江树介绍说,年轻时的石鲁特潇洒。犀利的眼睛,狂放的性格,既为他带来了艺术的人生,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谈到拍摄这幅作品时,李江树印象深刻。
1973年我就认识石鲁先生。1977年4月的一天,我随一位老同志到北京通县的结核病医院看望石鲁。那时石鲁才58岁,却十分虚弱,只有那不屈的头发还支棱着,但满口的牙几乎没了,但眼光依然那样犀利。老朋友相见,满腔的苦水和十年的悲愤岂能三言两语能说完?他们在诉说,我就在旁边找机会。那是下午4点多,屋里较暗,我用的是海鸥4A120相机,当时的《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潘德润给了我两个120的伊尔福400度黑白片,用F4的光圈,1/30秒的速度曝光。我在墙角站了足足有40分钟,有适当的神态和手势我就拍,一直把两卷都拍完。
我有些预感,这幅照片一定是重要的时刻。回来我就自己冲放,效果很好。几天后我拿去给石鲁先生看,老人当时就很高兴,非常欣赏,拿过来就在照片的背后写下了两句:“天怒像疯狂,其实老头儿没牙了”!这幅照片我现在还存着,后来他还给我画了一张画儿,题名是:红竹万杆风。画面上几棵红色的竹笋在向上蹿,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
1979年,“四月影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三次影展,我的这幅作品拿去展览,有人还为此配了一首诗:“总算活过来了,‘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一口白牙。”反应极好。至今我也不知是谁给配的。1980年2月,《大众摄影》拿去发表,他们还专门找了石鲁的老朋友、画家华君武给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这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石鲁的形象记录,李江树为石鲁拍的肖像是一张好作品。
我拍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注意,他太专注了,屋里挺冷,他还穿着大衣,身体很差。我那时只是个业余的,还在北京无线电二厂工作。海鸥的镜头很好,加上伊尔福的胶卷,绝对是“把意识记录下来的技术保证”。
李江树的这幅作品一出现,不仅让各界震动,还引发了许多人去关注石鲁。有人半开玩笑地对陕西的摄影家们说:你们的石鲁怎么让李江树拍去了呢?结果很多人去拍,到底也没有超过这幅的,甚至连李江树自己都没法再超过自己了。
李江树说:
拍人物不像拍别的,可以重复,可以近似,时机由自己来掌握。拍人物必须得所有的元素都集中在一起才能成功。比如特定的时代“文革”浩劫之后,劫后余生的人才有的痛苦经历;特定的地点医院,人物的神情一定是悲伤的;适合表现的环境渐暗的光线,严冬后仍然很冷的屋子;激动的情绪,专注的谈话,瘦骨嶙峋的身体,白了的头发,黑了的嘴巴,广大受迫害的艺术家的代表……所有这些,都是一张照片不可缺一的因素,只要换掉其中一项,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照片了。就像一切事物一样,它也有个“高潮”,只要过了这个高潮,就再也不会重复了,历史就这样过去了!这也是我自己都无法重复的原因。
《画家石鲁》就这样成了摄影名作,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成了一个时代的形象,成了一种概念的符号。看到了这张照片,就想起了石鲁,就想起了李江树,就想起了“文革”。我们也不必说这张照片得了多少奖,也不说它发表了多少次,单是李江树后来的作为,就足以让人们相信,他拍出这张作品不是偶然的。
1954年李江树生于北京,1976年他就开始学习摄影,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他纪实摄影的开端。1978年他进入《中国妇女》(英文版)当摄影记者至今。由于酷爱读书,使他很早就意识到文化功底对摄影的影响。因此他除了拍照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1985年,他的报告文学《林莽,浩瀚的林莽》获“国际青年”征文金奖;1995年,专题摄影《儿童孤独症的拯救者》获全国纪实报道摄影一等奖;1996年,《人民的音乐家王洛宾》获全国新闻人物肖像大赛铜牌2003年,中篇散文《向北方》获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好百年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出版的散文集有《湿地》、《手感》、《向北方》;中短篇小说集《沿着额木尔河的划行》;摄影美学专着《象征摄影》、摄影评论集《有狼的风景》等。一个摄影家能有这么多文字作品,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不仅文字数量多,文笔也具大家的风范。
“摄影界的文化人”,能够在名字前面加上这一前缀的,中国摄影界屈指可数,李江树之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