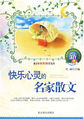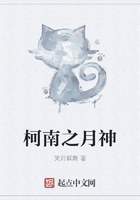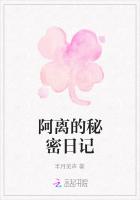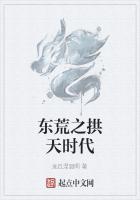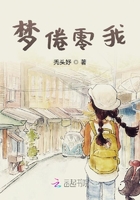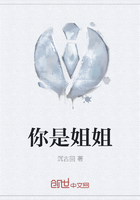“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就不用说了,然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四五运动”还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摄影家,甚至可称为中国摄影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形式、新的风格都诞生于此。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非常地投入,因而也就对摄影的发展贡献很大。“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因为那时他是“邓小平的人”,而邓小平在1976年时正受排挤,邓力群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过理想,并憧憬着它的实现;但是真的长大成人了,你才会发现,你所从事的事业常常是自己不曾想到过的,我便是这样跨入摄影之门的。
1973年,我结束了5年的插队生活(那是使我一生受益的5年),赋闲在家一年。正好家里有一台相机,周围的朋友、亲戚有喜欢照相的,受他们的影响,我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1976年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掀起的汹涌波涛,第一次使我省悟到了摄影的真正价值,从那时起,我就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6年1月8日的下午,我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一种不祥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心里。我小心地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妈妈告诉我,周总理去世了!话还没说完,眼泪便夺眶而出。尽管在这之前,就听说总理病重住院,但噩耗传来,我们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晚饭全家人几乎都没有吃,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出哭泣声。
第二天清晨,我拿上相机,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的国旗已经降了半旗,天气阴沉沉的,跟我们的心情一样,感觉很压抑。1月11日当人们听说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消息,首都上百万群众不约而同地冒着寒风,聚集在长安街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给总理送行。而后,人们又涌向了天安门广场,为了能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和花圈,有时要等候一个多小时。纪念碑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小白花,悼念的人群中经常有人哭得晕了过去,医务人员自发地在纪念碑前为悲痛欲绝的人们设置了临时急救台。而“四人帮”一伙儿对全国人民的悼念活动进行了压制,人民心头的怒火越压越重,终于在清明节前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1976年3月25日,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出现在纪念碑前。而后的10余天中,首都人民到天安门为周总理献上了数以万计的花圈和诗词。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每天早晨6点15时下班,20多分钟便到家了。吃完早饭,大约8点左右,揣上相机,骑上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当时我家住在朝阳门内,穿胡同沿着南小街南行,再穿过史家胡同至东单,沿着长安街西行,在长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队队人群抬着花圈往天安门走。我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10点又去上夜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年轻,不觉得累,就是略感疲倦,但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疲倦全无。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群,有老人,有孩子,有工人,有学生,有机关干部,有念诗的,有抄诗的,还有写血书的,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感动着。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周总理,用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莱卡相机,只有一支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上的制约,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实际上在广场上呆一天,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拍照,更多的时间是在广场上和大家一起看花圈上写的挽联和诗词。有时候看到精彩的,也拿笔抄录下来。因为广场上每送来一个新的花圈,总会有一些新的诗词贴出来。在3月底时,更多的诗词是以悼念为主:
花圈层层黑纱新,
清明时节倍思亲。
伟岸身影时时现,
断肠哀乐尚余音。
忠骨撒遍河山上,
丹心播进万人心。
总理有知应笑慰,
擎旗自有后来人。
时逢清明倍思亲,
不见报刊怀念君。
无限哀情压不住,
纪念碑前人如云。
一束鲜花表心意,
纵横热泪湿满襟。
为何今载春来迟?
几多悲来几多愤。
给天安门广场送花圈不光只有北京的老百姓,还有许多外地来京出差、探亲的同志。他们不仅抄录诗词,也贴自己写的诗词,还有专程从外地送花圈到广场的。4月1日上午,一个外地人就在纪念碑前贴出他自己写的诗词:
雄碑忆先辈,
俯首悼君哀。
花环如雪泪沾襟,
扫墓千里来。
忠贞为国酬,
生死置度外。
江河九曲归大海,
玉碎光华在。
天安门广场花圈和诗词越送越多。面对人民的悼念,“四人帮”们气急败坏地在4月2日发出紧急通知,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不要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等等。这个通知非但没有阻止人流,反而越聚越多,诗词也越来越激烈。现抄录几段,便可知道当时人们心头的怒火有多高:
不见报刊怀念您,
天安门前献诗歌。
千秋功罪人民定,
毁者稀微誉者多。
有的诗词直指“四人帮”:
总理遭诽谤,
怒火满胸膛。
天安门前摆战场,
花圈做刀枪。
叫声好同志,
请你莫悲伤。
莫忘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素纸黑纱含恸剪,
青松翠柏和泪扎。
谁言献花旧习惯,
明朝她死定无花。
这个“她”现在看来就是指江青。
4月3日下起了小雨,送花圈的人们冒雨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总理为人民,人民爱总理”这十个大字在广场上矗立着,道出了人民的心声。4月4日是丙辰清明节,适逢周末,广场上人头攒动,据后来估计,那天广场上有近百万人。
在广场拍了几天以后,发现没有制高点,人又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这样有合适的画面我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点,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接着他又发表了演说,他在讲演中说:“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咱们爱总理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上按下了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底片,其中这张《力挽狂澜》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事隔几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他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从监狱被放了出来。看到很多报刊刊登了《力挽狂澜》这张照片,他就四处打听作者是谁,几经周折,才和我联系上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名叫李铁华。见面之后回想起那段经历,大家都十分感慨。我送了一张精放的照片给他留做纪念。
4月4日下午5时,北京重型电机厂特制了两个高达7米、重约4吨的钢铁花圈进入了广场,广场上所有群众为他们鼓掌。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干部抬着几十个花圈献到纪念碑前,并在广场上召开了悼念周总理的大会,此时广场上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1976年4月5日清晨,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血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那么一天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时的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尽管后来在编辑画册时,有很多专业记者也拿出了照片,但获得好评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是这些业余摄影爱好者拍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而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笔名)编印了两本收录“天安门事件”诗词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与此同时,七机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几位同志也编印了一本《革命诗抄》。当时这几本诗抄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人们争相购买。在北京可以说每家都购有一两套书,至今我家中还保留了几套。
由此,我和一些“四五运动”的摄影者结识了。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二外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没想到王安时、王樵裕他们也就真的下了决心,积极筹备起这事。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在任世民家中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吴鹏是北京铁路局工人、王志平是农业出版社美术编辑、李晓斌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人、任世民是青海齿轮厂工人、我是北京新兴袜厂工人,只有高强在北京情报所从事摄影工作。虽然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很快我们将手续办好,到高强所在的北京情报所照相室暗房上班了。后来安政也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我们几人当时都有自己的摄影圈子,通过这些朋友将编画册的消息传出去,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后来在《人民的悼念》画册中作者这一栏是这样署名的:“摄影及图片提供者”,共有120人之多。这里面有很多人不是照片的作者,有提供作者住处的,有来义务帮忙的。总之,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两三万张。当时大家干活没黑没白,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画册编好。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月至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天安门事件”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事后,我们这些人被称为“四五英雄”,大家都相继走上专业摄影岗位。20多年来,我从来也没有以“英雄”自居过,我想我们当时和广场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不过做了一件很本分的事情,今后再有这种事我们还会去做。“四五”的摄影者们当时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感去记录那时发生的一切,以避免那段历史影像的空白,因为专业摄影记者都被禁止去天安门广场拍照,这种精神及社会责任感将伴随我们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