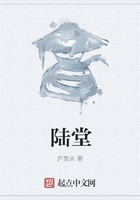听到这如同死亡般的乐音,看到飘起的雪花的时候,静静坐于太师椅上的顾倾城便知道,薛怀夜死了。他的终极绝招斩空极,虽然重创了沈萱,可是谁能抵挡得了袖白雪的致命的一击?
袖白雪一出,天地皆化雪。
便是斩空极下的地狱,也要被袖白雪所化解。
顾倾城抚着眉头,微微笑了起来。“到底是人世间至绝的高手呵,那一场生死,谁也放过不了谁,——纵是薛怀夜已死在袖白雪的致命一击下,沈萱亦难逃斩空极的重创,即便不死,也只有奄奄一息了。”他不由在心底感叹。
一个是与自己难分轩轾平分秋色的弟弟,一个是肝胆相照共历生死的好友,若是这两个人消失在世上,从此以后,他顾倾城岂非寂寞得很?
顾倾城忽然将头抬了起来。
黑暗之中,密室之内,忽然响起了一道森寒之极的语声:“满月如镜,万镜幽明,我将自镜中来,我已来了,凡人们,你们看得见我吗?”
跟着满室光华大盛,八卦图八角之上的莲花灯,重重莲花花瓣打开,赫然露出了藏在其中的夜明珠!
每颗夜明珠,都有碗口般大,照得密室之中,比深海鱼油和雪莲花根制成的长明灯,更明,更亮。
一颗这样的夜明珠已是难得,八颗同样巨大的夜明珠,简直是稀世珍宝!
珠光为密室增添了华光宝气,珠光也照亮了地上的两个人。薛怀夜仰面躺倒在地上,嘴角,胸口,手上和腿上,都沁出了鲜血,他的双眼紧闭,脸上全无血色,看上去已经死了。竹刀跌落在他身边,仿佛因了主人的死,刀也失去了光泽,变得黯然无光,如同一柄失去了刀魂的普通竹刀。
沈萱趴在地上,嘴里不停的吐着血沫,鲜血在他身下,积成了一汪。仿佛再过不了多久,他身体里的鲜血,都要被他吐尽。他的脸色,亦是无比的苍白虚弱。他的人看起来,仿佛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的双眼却睁着,看着太师椅上的人。
那个人身着一袭大红袍,红得如同地狱妖异的火莲,他的面上,戴着冷冰冰的纯银面具,毫无表情,只在夜明珠光芒的映照下,面具下偶尔闪过一线冷光。
顾倾城却不见了。
那个人缓缓的自太师椅上起身,缓缓的举步,一步步走到沈萱的面前,如同无上的神灵般,自上而下俯视着他。
沈萱用力的撑起身子,看着他。
他看得见藏镜人的眼睛。他面具下的一双眼睛,不再象以往那样是藏在暗黑之中,而是灵动的,转动着一双深如星空的眼睛,在看着沈萱。
“你吃惊吗,沈萱?”藏镜人忽然开口,如同一个多年的老朋友般:“金箭射出的红帖之上,我早就说过,我会自镜中来。”他仰起头,看着密室的顶,仿佛透过室顶,看到了今晚高悬在承风阁上空的月光:“满月如镜,我就是从月中来。”
“呵……呵呵呵,”沈萱忽然笑了起来,笑声牵动伤口,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我早该想到,你就是藏镜人,藏镜人就是你,”他盯着面具下那双眼睛,慢慢的,一字字道:“顾、倾、城。”
“怎么可能?”面具下的人大笑了起来,仿佛听到了世上最不可思议的笑话:“藏镜人要杀顾倾城,藏镜人就是我,我就是顾倾城,——难道我要杀死我?”
沈萱摇了摇头:“你就是藏镜人,你就是顾倾城,但你要杀的,不是我,而是,”他的目光慢慢转向身侧,薛怀夜就躺在血泊中,仿佛已经死去很久了,沈萱慢慢的道:“你要杀的人,就是他,薛怀夜,你的亲弟弟!”
他笑一笑,又摇一摇头:“我真傻,是不是?其实,我早该想到,引我上清凉泉,预先在泉边假扮成磨镜人伏击我的,应该是你,对不对?薛怀夜给你的‘妙怀春’,确实是有心救你一命的良药,他既然肯赠药相救,又怎么会要去杀你,对不对?在山洞中伏击我的藏镜人,根本无意要我的性命,所以他才会一击不中,便即遁走,目的只是要让我相信,那个处心积虑时时想要杀我的藏镜人,就是薛怀夜,对不对?”他苦笑了一下,接着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所以当你假装喝了我带回的清凉泉水而中毒的时候,我也完全相信了你,那时你心里,一定嘲笑我很傻,是不是?”
他直直的盯着藏镜人面具下的双眼,两个人四目相对,彼此都再无顾忌,直直的对视着,仿佛要看到对方的心里去:“你让人假扮藏镜人,让我看到他的金箭红帖,让我相信,他最后一定要来杀你,而我,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去替你杀掉藏镜人,解救你的危难。所以,当我在密室中看到薛怀夜出现的时候,我必定会毫无疑问的认为,他就是来杀你的藏镜人,从而对他出手,我们两虎相争,你却正可以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对不对?”
面具下的双眼,一动不动的看着他,良久,藏镜人忽然伸出一只手,将纯银面具,缓缓自脸上移开。面具下的那张脸,容颜绝世,倾国倾城,却不是顾倾城是谁?
沈萱深深吸了一口气,却又笑了。
“顾倾城,看在我们好友一场的份上,看在我们八年前大漠屠狼,再相见时西湖上共醉捞月的份上,看在……看在我就要死了的份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鲜血从他的嘴里,不绝如缕的流了下来。连白发如雪,面色如冰,心冷如铁的顾倾城,也不免动容。
怎么能忘记大漠冷月下的篝火暖语,面对狼群时的生死相惜?
怎么能放下西湖画船上的举杯醉语,湖心捞月时的畅快淋漓?
又怎么能……在亲手设局将好友送上黄泉不归路时,还能无动于衷?
“沈萱……”顾倾城喃喃念着好友的名字,双目中有一丝的迷离,仿佛起雾的湖水:“今夜之后,再没人能陪我月下共语,再没人能与我出生入死,再没人值得我顾倾城惺惺相惜,倾心以待,若是没有你,我顾倾城剩下的余生,真是寂寞得很!”他喟叹着,手指抚上额间,那里,一缕白发下,那道狼爪伤疤依然在,沈萱裸露的手背上,也有一道长长的狼爪疤痕,如同一条丑陋的蜈蚣,从手背一直盘踞到他的手臂上。他们两个人,都是绝世的美男子,却各有一道丑陋的疤痕,如同白玉染暇,可是在他们心里,那两道疤痕,却是彼此最珍贵的印记。
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冥冥中仿佛有种奇特的关连,宿命的交缠在了一起。
“我一直视你如亲兄弟,”顾倾城道:“就连怀夜死了,我都没有如此的心痛。”他凝视着沈萱:“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心里,一直将你看得比我的亲弟弟怀夜还要重要,好象我们之间,一直有某种神秘的关连。但我却不得不牺牲你,”顾倾城咬了咬牙,目光如雪,一瞬间冰冷:“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杀死我的亲弟弟,薛怀夜!”他顿了顿,面上露出决绝之色:“身为领袖天下的临风阁主,我不能自己动这个手,负上杀弟之名,而且,我也未必能有把握杀死我这个聪明过人的弟弟,所以,我必须假手于人,”他瞪着已经奄奄一息的沈萱:“而你,就是最合适的那个人!”
“我明白了!……”沈萱将双手撑在地上,苦笑:“你一直担心,最能与你争夺阁主之位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弟弟,薛怀夜,所以,当得知他即将回来的时候,你便早早开始设这个局,从西湖画船之上,藏镜人射向谢羽依的黄金之箭,你的杀局就已经启动了!”他喘了口气,慢慢的道:“这个杀薛怀夜的局,我们姑且就称它为‘杀夜’之局。薛怀夜骗了你,他说他要回来的时候,其实他的人,已至杭州城中。而你,也将计就计,装作不知道,演了一场戏给他看。”
“杀夜之局的第一步,就是你命人假扮成藏镜人,在西湖上箭射谢羽依,但却要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藏镜人要杀的不是谢姑娘,而是你顾倾城!”
“而谢羽依,恰好又正是为报被你杀死的亡夫陆骏之仇而来,正好被你利用,进入了你的局中,成为杀夜之局的第二步。”沈萱顿了顿,接着道:“你利用谢姑娘和冥泓,在洗心池上再次制造了藏镜人的第二次出现,要杀你的假象。因为你知道你的二弟薛怀夜心计多端,若不是制造两次这么逼直的戏,一定很难让他相信,世上竟有这么厉害的藏镜人,敢来刺杀他的大哥顾倾城!”
“第三步……”沈萱苦笑了起来:“就是你自己亲自出马,再次以藏镜人的身份出现,在清凉泉边的山洞里袭击我,目的就是要我相信,薛怀夜极有可能便是藏镜人!”他没有停歇,一口气道:“最后一步,你再次命人假扮藏镜人,射箭留贴,声明要在满月之夜杀了你,而你,将薛怀夜也在此时骗入了密室,这个时候,我必然会出手杀薛怀夜,也就达到了你借我之手除去令弟薛怀夜的目的。”
沈萱笑了一笑,看着顾倾城:“即使我杀不了薛怀夜,但以我们的武功,我们两个人必然会拼得你死我活,两败俱伤,所以无论我与薛怀夜的决战结果如何,你都是最后胜出的那个人,不是吗?”他笑起来的时候,牵动伤口,却咳得更加厉害起来,他的人蜷缩起来,样子看起来异常的痛苦。
顾倾城缓缓的,从身侧一寸一寸拔出他那名震天下的干星剑,剑身毫光闪耀,直到剑身全出,光芒大涨!顾倾城面上的表情,凝固如冰,他手上的剑,剑尖缓缓下垂,锋利如雪的剑尖,指在了沈萱的颈畔。
“你太聪明了,沈萱!”顾倾城道:“若不是为了借你之手杀掉薛怀夜,我真不忍心看你去死。”他剑尖的寒气,透入沈萱颈侧的肌肤,寒意浸人:“你知道了所有这一切,便不能再留在这世上。作为你的好友,我也实在不忍看你死前这么痛苦,就让我的剑,替你结束你的痛苦吧!”
剑身一提,干星剑闪着冷冷的寒光,朝沈萱刺了下来!
在那一刻,沈萱的脑海中,莫名的想起了大漠风沙中,那个面对凶猛狼群厮杀,一边意气飞扬,大声吟咏着宝剑诗的白衣少年,他脚下踏着剑步,手中挥着干星,朗朗而吟:“我有昆吾剑,求趋夫子庭。白虹时切玉,紫气夜干星。锷上芙蓉动,匣中霜雪明。倚天持报国,画地取雄名!”
那样意气风发的语声,响在大漠的冷月下,响彻了他们的流年,响起在他和他的记忆里,沈萱的眼中,忽然有一行泪流了下来,——永别了!大漠的少年,再也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