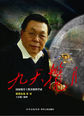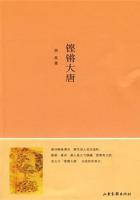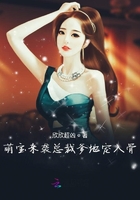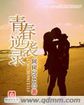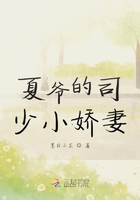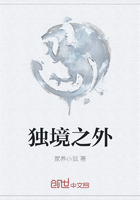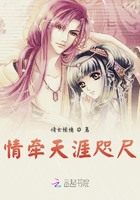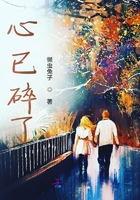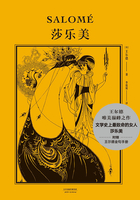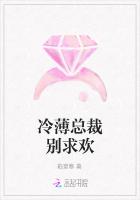大家见孙传庭说得诚恳,又被他的忠君之心所感动,便不再勉强他。步入禅堂后,几位幕僚很快就各写了一首诗。除咏重阳、咏禅寺外,都没有忘记庆贺出关以来赢得的“剿贼”大捷,更没有忘记赞颂督师大人的功绩。孙传庭含笑接过他们递上的诗稿,慢慢地吟诵一遍。当读到“宵旰九重思柱石,疮痍万姓望旌旗”这样的句子时,他连声说:“过誉了,过誉了。流贼尚未消灭,学生愿与诸君共勉!”
从风穴山登高回来,已是申末酉初时候。进了行辕,孙传庭刚刚下马,守候在院中的中军副将便匆匆迎上来:
“禀报大人,原先革里眼手下的一名将领带了五百个火铳手也来投诚了!”
孙传庭心中又一喜,故作寻常地问道:
“人呢?”
“我让火铳手们先在城外休息。那将领带到这儿来了,等待大人接见。”
“你让他再等一下。”
孙传庭不慌不忙地向后院走去。经过前院厅堂时,他知道那降将正在里面向外探视,但他一眼不瞟地走了过去。回到书斋,他先把一位幕僚请来,口授了上疏的内容,让对方先去起草,随后在亲兵侍候下洗了脸,又稍息片刻,才慢慢地回到前院,步入厅堂。
坐在左侧一把椅子上的将领一见孙传庭,赶紧站起来。孙传庭略一颔首,便在中间的太师椅上坐下。那将领立即跪下参拜,口里说:
“末将贺腾云叩见督师大人!”
“你是革里眼的部下?”孙传庭没有马上叫他起来。
“末将原是革里眼贺一龙的部下。革叔被闯贼杀害后,末将被分到争世王刘希尧军中去了。”
“你怎么想到要来投诚?”
“末将不单是贺一龙的部下,还是他的亲信、他的堂侄。革叔被害,末将早就想报仇,只是没有机会。现在大人挥师南下,末将不趁此时反正,更待何时?”
孙传庭见此人说话不像李养纯那么粗俗,心中倒有点好感,便叫他起来坐下,又问道:
“你是怎么过来的?大军追杀流贼时,你在哪里?”
“我们这五百个弟兄,都恨透了闯贼,也不服刘希尧,说什么‘争世王’,根本就是闯贼的跟屁虫!所以当刘希尧率队出阵时,我们的火铳都朝天放,没敢对着官军。后来刘希尧败退,我们就在附近荒村中停下来,没有跟着他逃跑。知道大人到了汝州,我们就赶紧前来投诚了。”
孙传庭点点头,又问道:“你认识杨承祖么?”
“当然认识。原来革左五营中,要数革叔与曹操关系最好,所以下面的人也都有来往。不过杨承祖带的是骑兵,我带的是火铳手,所以接触不算太多。末将与曹营玩火器的弟兄们更熟一些。”
“杨承祖、黄龙向宝州那边追击残寇去了。明后天你们就能见面。”孙传庭很随意地说着,一面注意着对方的反应,“他们两位投诚过来后,非常忠勇,我已为他们请功。朝廷很快会予以嘉奖、升迁。你过来后,只要一心报效朝廷,将来也必定会前途无量。”
“末将一定牢记大人教诲。”
孙传庭看不出此人身上有何疑点,便想着要将五百个火铳手拨到火车营去归白广恩指挥,但又觉得应当先让杨承祖来认一认再作决定,于是说道:
“你先下去休息吧。下一步战事我会另行部署。”
晚饭后,那位起草奏疏的幕僚拿着草稿来请孙传庭过目。孙传庭在烛光下仔细地读了一遍。看着奏疏中列举的赫赫战果,又想到先后前来投诚的一批“贼将”,不由得心情激动,拿起笔来在草疏上加了一段话—— 挺进西安(21)
有自贼中来归者,言贼闻臣名皆惊溃。臣誓扫清楚、豫,荡尽鲸鲵,必不敢遗一贼以贻国家之患,以廑君父之忧。
过了一天,孙传庭正在等候有关“贼情”的新探报,忽然接到牛成虎从宝州派人送回的消息,说前队进攻宝州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又说鼓动百姓守城的乃是在襄阳叛投“贼军”的举人陈可新。孙传庭思索了一会儿,认为陈可新以弹丸孤城敢与官军顽抗,必定是有“流贼”主力作后盾,于是他下令全军继续南下,向宝州挺进!
13
九月十二日这一天,李自成是在十分矛盾的心情中度过的。
一连两天,他不断接到陈可新的告急文书,先是说官军前锋正向宝州急速行进,接着说官军已抵达城下并开始攻城,城内兵丁和居民正在陈亲自督率下拼死守卫,请求他赶快发兵救援,迟则城将不保。又说自己一死不足惜,可怜的是阖城百姓正在重庆更生,转眼之间又将横遭兵火荼毒。李自成从接到第一封文书起,就答应马上派大军驰救,让陈可新坚守待援。以后每接一次告急信,他都答复人马即将出发。但实际上大军就驻在距宝州不远的襄城郊外,却始终没有出动。今天上午,又有一个守城兵丁冒着生命危险从城上缒下,又在附近村庄借到一匹骡子,疾驰到行辕报信,说是孙传庭已率官军主力亲临城下,救兵倘再不至,宝州就完了。几乎同时,宋献策派出的哨探也带回了同样的消息。
宝州紧邻郏县和襄城。孙传庭来到宝州,就等于进入了李自成预设的口袋中。眼看胜利在望,李自成非常兴奋,然而就在兴奋的期待中,又有一种内疚、一种不安时时袭上心头。他对陈可新撒了谎。虽然他与陈只见过几次面,但从李侔的介绍,从陈在这次守城中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关爱百姓而对新顺事业忠心耿耿的地方官,在现有的文臣中实在不可多得。而由于陈的施政,宝州士民也对新顺、对自己这个新顺王充满拥戴之情。现在为了诱敌深入,他把整个宝州连同陈可新都当成了诱饵。这样做对么?值得么?他在一闪念间曾准备发兵驰救宝州,但终于抑制了良心的冲动,没有下达救援令。他想起来宋献策说的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何况他并非“一将”,而是“一帝”,是未来大顺朝的开国皇帝!为了改朝换代的千秋伟业,只好牺牲陈可新和宝州百姓了!
未时刚过,破城的消息传来。陈可新被杀!众多守城百姓被杀!官军屠城!整个宝州一片火光血海!李自成心中又一次震动。他想起李侔说的:“宝州的父老兄弟,连同陈可新这样的好官,就这么丢给敌人去残害么?”他还想起李岩说的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不由得心中自问:难道我做错了么?难道我是一个“不仁”的君主么?
正当他陷于又振奋又内疚的思绪中时,双喜进来向他禀报:
“邱之陶到了。”
李自成顿时抛开宝州,精神转到另一件要事上来。几天前,袁宗第派人押来一个商贩模样的人。原来,邱之陶的管家离开洛阳后,仍打算经陕州从原路驰回襄阳。经过邓州西边时,恰被袁宗第的逻卒发现,因他策马奔跑甚疾而引起怀疑,结果被拦截下来,从身上搜出了蜡丸书。袁宗第亲自审问后将他押到襄城。李自成获悉详情后,既吃惊,又愤怒,在与牛、宋和刘宗敏商量后,决定不打草惊蛇,而是以商讨军事的名义把邱之陶召到襄城来。
“让他进来。”李自成说。
邱之陶进房后,看见只有李自成一人坐在案后,牛、宋和刘宗敏等均不在场,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向李自成行礼落座后,先开口问道;“捷轩将军和牛先生、军师他们还没有到么?”
李自成冷冷一笑,说:“今天要谈的事很机密,就孤和你两个谈谈。”
“不知殿下要谈何事?”
李自成又一笑:“督师大人有封密信让孤转交给你。”
“哪位督师大人?”邱之陶觉得背脊发凉。
“孙传庭孙大人。你不是给他写了信么?这是他给你的回信。”李自成把信团了一团隔着桌案掷过去。信落在地上,邱之陶捡起来读了一遍。他知道计谋已败露,但不了解经过,勉强说道:
“殿下,这事好像有些误会,可不要中了孙传庭的离间之计!”
“哼哼,”李自成鼻子里笑了两声,“孤也怕中了离间之计,所以把贵管家也请来了。你想同他见见么?”
邱之陶听说管家被捉获,明白大事已去,想着自己半年多来屈节事“贼”,为的就是要替祖父报仇,为朝廷“剿贼”大局尽力,现在功亏一篑,绝好的计谋付诸东流,忍不住一阵伤心,流下泪来。
李自成见邱之陶流泪,以为他怕死,故意叹一口气,说道:“你投降新顺后,孤待你不薄。你还那么年青,孤就委以要职。倘若你能忠心事主,本来前程似锦。明年孤进北京灭了明朝,你就是开国功臣。可惜如今你自己走上了绝路,后悔也来不及了。”
邱之陶还在流泪,却忽然变了态度,厉声说道:“李自成,你以为我怕死么?自从你在宜城杀害先祖,你我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从那时起,我天天就想着要取你的贼头祭奠先祖以尽孝尽忠。你以为我会看中那些伪职?真是可笑!什么从事、侍郎,连同你这个狗王在我眼里都屁钱不值!我怎么会为我的行事后悔?我做的事都是为了杀贼报国,不管成与不成,都可同昭日月。我知道今天必死无疑,我将一身清白去见先祖。至于汝辈蟊贼,只等督师大军一到……”
因为邱之陶的声音很大,站在门外的双喜听不下去,突然大步进来,不等邱的话说完,就一耳光打过去,顿时邱的鼻子、嘴角都流出血来。
“看你还敢在殿下面前撒野!”双喜说着,转向李自成,“父王,我把这小杂种带出去收拾了吧?”
李自成没有立即回答双喜,而是望着邱之陶说:“凭你今天说的话,就可处以车裂之刑。但孤只将你问斩,这是因为你虽然居心险恶,但你先前说的一些话对我们还有用处,譬如火车营用的是什么战车之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孙传庭用的大都是偏厢车。几天之内,他就会土崩瓦解,而这些连成一片的偏厢车不但帮不了他,还会给他带来大麻烦。”说到这里,不等邱之陶再说话,李自成对双喜做个手势,双喜便将邱押了出去。
李自成本来可派人去襄阳处决邱之陶。其所以决定将邱弄到襄城来处斩,表面上是为了慎重,内心则还怀有一种当面揭露邱的阴谋的欲望。实际上他很希望看到邱为自己辩护、求饶,从而获得一种猫玩老鼠般的快感。没有料到过程这么简短,邱几乎一下子就承认了罪行,而态度又如此恶劣,言辞又如此不恭,使他不由得想起在汝宁被俘杀的杨文岳,又想起在襄阳服毒自尽的陈慕平。他没有产生预期的快感,反而隐隐地感到了一种失落……刘宗敏、李过、牛金星、宋献策陆续来到行辕,都问起邱之陶的事。“已经斩了。”李自成只简单地答了一句,便开始与他们商议围歼孙传庭的大计。
14
仅仅四五天内,孙传庭已经有过两次颅内失血的感觉。
九月十二日攻入宝州之后,孙传庭来到州衙大堂听取战情汇报。一进门看见杨承祖坐在牛成虎身边,他便问他是否认识贺腾云?杨说贺确是革里眼手下施放火铳的头目,革里眼被杀后,贺与一干火铳手被分到刘希尧军中;又说刘在革左五营中是跟李自成跟得最紧的人,所以自己与贺虽不熟,却能想见贺在刘手下不会很舒服。听罢杨承祖的介绍,孙传庭释了疑虑,当即决定将贺腾云等五百人分到火车营,统归白广恩节制。
接着众将一一汇报攻城战果与伤亡情况。孙传庭一听就明白,“贼军”主力并不在宝州。他们为什么不援救宝州?他们要退到哪里去?他们想干什么?孙传庭正在思索,一个负责随军粮饷的副将走进来,向孙传庭施礼后,说道:
“启禀大人,大军的粮道被截了!”
“什么?粮道被截?是从汝州到宝州来的路上被截的么?”
鉴于去年冢头之战的教训,孙传庭这次出潼关,一路都非常注意粮道的安全。无论从陕州到洛阳,还是从洛阳到汝州,他都密切关注义军的动向,特别是对溃逃的义军盯得更紧,严防他们在奔跑中绕到官军后方去。从汝州来宝州的路上,他也不忘叮嘱部下注意周遭动静。据一路获得的探报,都知道义军在东南,在官军的前方,那么,截断粮道的“贼军”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启禀大人,贼军是在白沙镇附近出现的,有万把人,抢劫了我们从洛阳运出的粮食,阻断了从洛阳到汝州的通路。”
片刻间,孙传庭觉得眼前一阵发黑,脑中的血好像一时都往下流失,有一种眩晕和欲呕的感觉。他不由得两手紧握太师椅的扶手,竭力保持镇定。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凭着多年的战争阅历,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中了“流贼”的狡计,可能已经陷入对方预设的包围圈中。
“贼军是从哪里前往白沙镇的?”
白沙镇在洛阳和汝州中间,距两边的路程差不多。如果不从汝州往白沙,那就只有从北边也就是登封一带斜插过来了。登封是李际遇盘踞的地方。难道是李际遇派人来劫粮?不可能!他没有那个力量,也没有那份胆量。何况这次出征前已派人去见过李际遇;李际遇态度极好,甚至表示了接受招安的意愿。再说若真是李际遇劫粮,他应该劫了就跑,而不会阻断粮道。那么,只能是李自成的人马了,他们是从哪条道绕往白沙去的呢?
孙传庭思考的问题,在负责粮饷的副将脑中也想了很久,这时说道:
“照末将看,这支贼军可能是从密县那边,擦过登封县境,从山间小路来到白沙的。”
“不会吧,”坐在下面的一个总兵说,“这得绕多大一个湾子?再说,万把人行动,怎么连个声响也没有?”
别的将领一听,也跟着议论起来。有的说,如果全是步兵,走山间小路尚不困难,如果是骑兵,还要携带火器和粮草辎重,那怎么能走山路?也有的说,从登封经过,李际遇岂能不知?但李际遇并未向官军通报,难道这土霸王与李自成“贼军”已串通一气?
不管众人如何议论纷纷,孙传庭心中已认可副将的判断,同时对“流贼”行动的诡秘深感吃惊。他轻咳一声,众将都屏息下来。
“我们的粮食还够吃几天?”孙传庭缓缓问道。
“大概还可维持三四天。”副将说。
这次出征,因为后面有专门的运粮队伍,所以前面的作战人马通常只携带几天的用粮。这个情形孙传庭是完全了解的。他思考的是,下一步究竟是还军就粮,还是继续前进。听了副将的回答,他点点头,没有马上说话。一个幕僚也意识到目前的险境,对孙传庭说:
“大人,我们大军是否先回汝州,然后派一支人马去剿灭劫粮之贼?”
孙传庭微微摇头,又想了一会儿,说:“我们这次出征,一路连胜。气可鼓而不可泄。如今必须继续前进,剿灭流贼主力。今天大军在宝州休息一晚,明天一早去攻郏县,就地取粮!”
十三日官军抵达郏县,却发现那里四门洞开,根本没有城守,稍为富裕的人家都已出逃,留在城内的只是穷百姓。官军满城搜罗,只弄来二百余头骡、羊,一天就可吃光。这时孙传庭获知义军主力就布防在郏县东面到襄城一带,于是十四日就指挥大军向东进发,果然前进不到百里,就远远看见义军的各种旗帜在西风中招展。牛成虎率领的前队人马继续前进,忽然一道宽而深的堑壕横在前方。对面半里开外,密密麻麻布满义军。牛成虎不敢轻易进入壕中,派人火急向孙传庭禀报。孙传庭立刻带着亲兵亲将策马来到前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