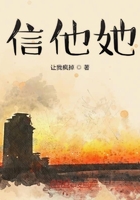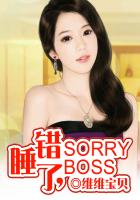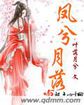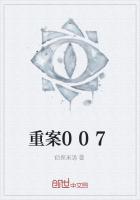1897年的中国形势可以用这样两句话形容:中国二千年封建文明体系按照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势所必然地土崩瓦解着;中国的工业文明以国外资本殖民方式和本民族工业的觉醒发展而势所必然地循序渐进着。
那一年,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强租胶州湾、并铺设胶州湾至济南铁路、取得沿线矿产开采权;法国逼迫清政府总理衙门作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声明、并取得了广西铺设铁路与在云南、广东、广西的开矿权;而英国则取得了河南、山西的开矿权。同年,美商鸿源纱厂、英商老公茂纱厂、怡和纱厂和德商瑞记纱厂纷纷在华开工。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工业如通益公纱厂、苏经源盛缫丝厂、业勤纱厂,亦分别在杭州、苏州、吴县、无锡、和南通等东南沿海城市开风气之先的所在创办。上海商务印书馆也在那一年成立。
那一年,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而章炳麟、陈虬和宋恕等主编的《经世报》则在四百里路之外的杭州出版。与此同时,有工部主事康有为的上书,请及时革旧图新,又有户部尚书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发出自强之上谕,有意变法。
那一年,西历4月14,农历三月十三,浙江上虞当时的县城丰惠西大街吴家,出生了第二个儿子,乳名早已取下,就叫作吴龙山。
无法考证吴家父母何以取儿子的名为龙山。在中国,一般认为龙高贵吉祥,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吴家父母倒也未必有这样的龙的传人的意识,倒是在县城百官镇旁,的确有一座龙山,在当地人看来,风水是极好的。
从父系的血脉上看,吴龙山本来是应该被叫作郑龙山的,因为孩子的父亲姓郑。但原籍安徽的上虞县郑家堡人郑忠孝(公元1853--1916年),虽说祖辈就迁到了上虞这山清水透之地,但生活却未曾有什么好转,到他这一辈,家境实在是到了赤贫的地步,成年后只得到浙东的四明山中梁弄镇作雇工,一直过了而立之年尚无钱娶亲,这个彻底的无产者只好把自己入赘了出去,这才到了丰惠镇西大街吴家,与吴家的独生女儿吴阿凤成了亲,租了六、七亩田,从此才算是有了一块立锥之地。
入赘的中国男人,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精神上自然是低人一等的,他们的孩子,往往就姓了母家之姓。好在吴阿凤育有二男三女,算是给吴家续足了香火,故而,长女秀梅,长子燕山和次女秀姑皆从父姓而为郑,那幼女文桂和幼子龙山,便就从了母姓。
也和一般的规律一样,那入赘的男人往往是极其老实厚道寡言勤劳的,而那女子则往往是聪明伶俐八面生风四面呼应的。郑忠孝勤恳寡言,吴阿凤开朗热闹,西大街上,人称凤三娘。她为人慷慨大方,极好交往,朋友便也不少,她那外向活泼的性格明显地在她小儿子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证实西大街吴家和茶有特殊的渊源。但吴觉农晚年的回忆中却有他时常看到家乡父老春季采茶的情景:“我幼时经常到茶山看采茶。(见吴觉农《我的经历和主要社会关系》)”这回忆确凿无疑是可以成立的。在吴觉农的童年时期,因为父亲的务农,他也势必承担起诸如往田间送饭等一类的轻便农事,而在这桑间陌上,放眼看到茶事,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家中有着六、七亩田地的江南的自耕农,在田头地角种着一些茶蓬,也是农民常有的习惯。因此,吴觉农对茶叶的认识,肯定伴随着他的童年就已经开始了。
上虞,有许多历史上著名的人文景观:比如因为那远古的明君舜王的足迹而命名的舜江、百官镇;因为出了中国古代第一大孝女的曹娥而建立的曹娥庙;比如因为晋人谢安隐居后出名的东山--那“东山再起”的典故就是从吴觉农的家乡而来;还有世界青瓷的发祥地小仙坛,上虞山间那些古窑址们,再清楚不过地记录了这块离河姆渡文明咫尺之遥的神奇的土地;再比如因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而闻名的中国的罗蜜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越剧的《梁祝》开幕便唱: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
然而,或许正是这一切太有名了,那茶的謦香才常被人忽略。人们只是一般地把上虞作为浙东茶区,却不知上虞的茶有着其不可取代的声名和历史。一位杰出的茶人出生在茶乡土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位处浙东的上虞距省城杭州70公里,北濒杭州湾,与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隔江相望。虞山舜江,碧波荡漾,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云雾缭绕,人民在此耕种稻麦,植桑养蚕,更有那藏之以深山丘陵的茗茶飘香。
上虞主要产茶分布在四明山和会稽山脉的两山之间,间隔着一条自南而北源远流长的曹娥江,境内山高林茂,翠绿欲滴,经冬不凋的茶园美丽如画。四明山海拔1012米,会稽山(主峰东白山)海拔1194米,有时云雾缭绕,有时又风和日丽。气侯温和,雨量充沛,土壤适宜,因了茶圣陆羽所言的“阳崖阴林”之说,因此一向被人们称为茶叶金三角,是中国传统名茶平水珠茶的出口产品的中心地带。
中国茶文化中有一段后人乐道的佳话,就出于此处。
东晋谢安当年隐居在此处的东山,友人往来频繁,谢安提倡以茶会友。在征途中,吴兴太守陆纳招待这位将军,也仅仅是清茶果品而已。可是陆纳的侄子陆俶突然摆上了酒肉佳肴,事后陆纳处罚了侄子,严厉责问说:你既不能够为叔父争光,为什么还要来沾污我以茶代酒的清名呢。
可以看出,在晋代,中国茶文化的积叠,在吴觉农的故乡已经是很深了。
记载上虞茶事的文字还可以间接地从唐代陆羽的《茶经》中明确查到,陆羽在公元八世纪下半叶时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曾经搭舟沿舜江(也就是现在曹娥江)经东山、上剡溪考察后,于《茶经·八之出》中用了最简洁的字记录道:浙东,以越州(今天的绍兴地区)上。而上虞,正是古时越州的重镇。吴觉农先生晚年力著《茶经述评》中点评到浙东茶区时首先就提到了越州,并不无骄傲地开言便说:越州所属各县无不产茶。从州产名茶来说,据明万历《绍兴府志》(1586年)的记载,则有:府城内卧龙山瑞龙茶;山阴天衣山丁堄茶,兰亭花坞茶;会稽日铸岭日铸茶,陶宴岭高坞茶,秦望山小朵茶,东土乡雁路茶,会稽山茶山茶,诸暨石笕茶,余姚化安瀑布茶,童家岙茶;上虞后山茶,嵊剡溪茶。
关于上虞后山茶,明代天顺举人韩铣在1504年返故园探亲时,在丰惠品茶时专门作过一首《后山茶诗》,诗曰:谁说后山别有春,金芽带露摘来新。鵶山入谱香难久,鸟咀虚名味莫论。数片漫煎消酒渴,一瓯轻泛沁诗神。我来受罢山僧供,两腋清风欲奋身。此诗大有卢仝“七碗茶”诗的飘然欲仙的神韵。
韩铣曾任广东韶州知府,农田水利政绩显著,他对故乡茶叶的评判是很内行的。
上虞和被民间称为“下虞”的余姚山水相依,关于余姚茶的记载里同样可以看到上虞茶的影子。《神异记》中记载:余姚人虞洪上山采茶,遇见一位道士,牵着三头青牛。这个道士带着虞洪到了瀑布山,对他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很会煮茶,常想请你送给我品尝。这山里有大茶,可以给你采摘,以后你有多余的茶,请给我一些。虞洪就经常叫家人进山,果然采到了大茶。他后来就常用茶来祭祀这位高人。
无独有偶,除唐代茶圣陆羽当年撰写《茶经》时泛舟沿着舜江考察来往之外,唐代日本国天台宗初祖最澄大师西渡中国,也是在上虞峰山道场受法后,携带着茶种回国广为种植,日本茶叶文明之源也是自此开始的。最澄和尚(公元767-822年)初冬时来到中国天台,次年初春,入越州龙兴寺,从泰岳灵岩寺师承顺晓大师所在地丰山道场受密法,这个丰山道场就位于今天一虞的百官镇境内,离曹娥江只有两公里左右。据说,最澄学成之后,于公元805年带着佛教信徒们抄写的陆羽《茶经》和丰山道场附近的茶种回了日本,并在滋贺群版皖村及琵琶湖畔繁殖茶园,也算是开日本茶业种殖的先河。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宗教界人士还来上虞考察,寻觅了最澄当年的踪迹,最后确认了最澄于公元805年在上虞从顺晓大师学习取经的地方。在丰山道场顶峰的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座坐西朝东石雕半身顺晓大师的遗像。有人推测,说是最澄为感顺晓大师之恩而雕刻的。这种传说,传递了把中国茶叶传入日本的最早的使者最澄在吴觉农故乡的活动踪迹和确实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