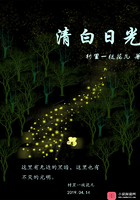这种将铁与血,将真实的打工遭遇与农民工在工业社会的处境结合在一起的写法的确独树一帜,在尖锐坚硬的铁面前,柔弱的肉体和灵魂都显得极为脆弱,但别具只眼的是,郑小琼写出了铁在科技面前,在那些机器的塑造下的柔软和脆弱,并将这种塑形与打工生活对人的打造并置在一起,打工生活不止像一场酸雨,更是一个重新回炉打造的过程,它不仅改变人的肉体、灵魂、思想,还可能将整个人都摧毁掉。语言呈现出一种狞厉坚硬之美。她当然在写苦难,但这种苦难是如此普遍,如此底层,如此容易被忽略,因为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整个农民工,整个生活在工业社会的工人们的悲哀处境。他们就像铁一样被安放在机器里面,只能被动等待被切割重塑的命运,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只能任由疼痛穿越整个人生。
《塑料厂》“一年一年,一件一件。我们也是这样,把自己的青春熔化、分解,流进每个制品之中,让人打包,运走。”与《铁》比起来,《塑料厂》的控诉更直接,直接指向黑心老板,他们会给慈善机构捐款若干以换来慈悲的名声,却将自己受工伤的员工赶出厂外,“他们得不到赔偿,被保安赶出厂门。他们的眼神无助,委琐的身子在厂门外抖瑟。”“塑料厂老板不需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感受与疼痛,他需要我们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像那些塑料制品一样能够给他带来利润和钞票。”“人类不断地砍伐着真正的绿色植物,却要制造出这样虚假的绿色树木,红色花朵,来安慰日益贫乏的心灵。我们应该怜惜的事物正在被我们糟蹋,它们在我们的暴力下消逝了,生活挖去了我们内心最为柔弱的部分。”
与郑小琼同时崛起的女作家塞壬也擅长描写打工生活,她的《下落不明的生活》描述流浪的打工生活,来历不明又未知去向的生活,艰难的、疼痛的、伤痕斑驳的生活。这生活疲惫之极,气息奄奄,充满敌意、怨毒、风险,以及难以言说的焦虑,孤独与忧伤。与郑小琼的散文一样,都是以亲历者来回眸艰辛的打工生活,所坦露的真实和艰辛拓展了普通意义上关于底层的认识。那绝不是一个寒夜中卖红薯的老人或被城管欺压的痛苦,而是关于生存、梦想、现实的钳制的描述。文章包括三个短篇《一次次地离开》、《夜晚的病》、《南方的睡眠》,近乎呓语般写出“我”这个流浪在外的打工者的心灵和精神状态。
《一次次离开》是漂泊的状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行李,是一个伤感的名词。它意味着伤感和离开,意味着一个事件的终结,而另一种未知的开始。”收拾行李,去旧货店卖掉家具告别一段生活,奔赴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里作者写出了人生的无奈,不得已,它意味着一次次丢弃,丢掉曾经相伴的东西,而变迁的生活也意味着总是收不到信,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地址的人”,也很难联系上,因为我的手机号总在变换。“如果不对命运妥协,我就得一次次地离开,我的下落不明的生活将永远继续。”
《南方的睡眠》中“我”陷入昏睡,不分白天黑夜,除了看碟吃东西就是长长的死去一样的昏睡。“蒙头蜷在单床上,像是潜在更深的地底,所有的记忆、喜怒,身后的那些可知或不可知的事,它们都陷落,陷落,一直把睡眠推往更深的地方。”“睡眠,成了无法逃避的选择,无休无止,昏天暗地。除了我,四壁、床、桌子、电脑以及空间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一样,它们昏睡、疲软,仿佛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尘埃见证一切。”
而被誉为西部小说新领军人物的张学东也是以描写底层生存见长,他的的《艳阳》小说所写得是西部最基层的教育现状,教育经费极其短缺,师资力量十分薄弱,生源常因家庭困境而面临流失,教师们除了担任极其繁重的日常教学任务,还要东奔西走不辞辛苦地家访,把那些旷课逃学的学生找回来。然而他们的努力常常是徒劳。
小说以“我”为叙事者,在我的感受中描述出一幅乡村教育窘困图,他是以“我”的心理流动,从细节入手来描述的,燥烫难耐的天气,校长递过来的老旧肮脏的茶杯,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中学,有路子的老师都办了调动,甘心留下的都是一心等着光荣退休的老教师,办学设施都是80年代初期的老古董,孩子们连操场也没有,跑早操得去车来车往的马路上,这是小说后文中悲剧产生的伏笔。家长大多是小商小贩外来民工,“整天只顾挣钱糊口,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哪还顾得上这些孩子”。对孩子不管不问,老师家访找上门了,也一味推给学校,“责问老师都是干啥吃的。”
往往一个老师都要代两门以上的课,比如小白老师代数学和物理两门课,还是一个班的班主任。学生厌学,素质差,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像警察和小偷。顽劣的学生动不动旷课,上网吧打游戏,打架斗殴,说粗话,收其他同学保护费。但即使顽劣如刘七一,他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为了治好父亲的肾病,他每天起早贪黑去抓青蛙,希望用民间偏方为父亲治病。他还偷偷喜欢阮灵,而小说中那个爱整洁的阮灵,因为憎恶母亲抛弃父亲、私生活不检点,竟然一把火烧掉了自家的家具厂。她也因此入狱。而小白老师,那个钟情于教师职业,不辞辛劳地奔波在家访和日常教学工作中的年轻善良的女教师,在一次清晨带孩子跑早操时被一辆运煤车撞死。
张学东《坚硬的夏麦》陆小北父子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呢?对于乡村中的这对父子来说,贫穷似乎是罪恶之源。小说不断穿插叙事者我正在阅读的小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把那个老人与大海的搏斗同陆氏父子与贫困的挣扎并置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老人与海》的结局老人拖回一副空骨架,而陆父被麦子压断了腰,陆小北溺水身亡。
“我”出现在小说中时是一个几次高考未考上的失意青年,临时担任陆小北的班主任,由此呈现出乡村教育的窘困。“学校里有点路子的老师先后调走了,有头脑和资本的也跑出去做买卖倒生意去了,剩下的老师多半都面临退休,而他们中有的教了大半辈子书,临了还是个民办的。”“我”这个考了两年未考上大学的高中生一来就负责初三的物理和化学,校长讲语文和政治,另一位女老师讲数学和英语。这样的师资设置和五十几个贫苦农家子弟的人生梦想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滑稽的笑话。正如小北犀利点破的那样,念书念了也是白念。
陆小北无钱交学费,我劝服校长免了他的杂费,这样小北读书已是没有问题。但陆小北精明小气的哥嫂又与他们起了冲突,陆父想借几个鸡蛋给小北补充营养,结果被奚落,陆小北一气之下毒死了哥嫂的鸡。在被陆父追打后,小北离家出走,结果陆父因一个人卖麦压断了腰,小北在回家途中落水身亡,一个悲凉的结局。
陆父就像《老人与海》中那个执着的老人,一心想让儿子读书,有所作为,他的梦想和努力却被现实击得粉碎。这里潜伏的问题是:贫家子弟如何成功?这里也包括“我”。陆父在小说中的形象是让人记忆深刻的,“黑瘦憔悴,脸、脖子、胸膛和脊背黝黑并且皱褶叠复,泛黑的褐斑毫无规律地爬上额头、脸颊、鼻梁和太阳穴,那是照射在黄土地上的阳光最引以骄傲的丰功伟绩。如果说有区别,他和别人惟一的区别是他的背看上去更驼,更弯,像这片土地上最古老最常见的那种枯柳,总是卑微地佝偻着,像是永远也直不起来或从来都不曾直起来过。”
卖麦子时被挑剔没有晒干,现场晾晒后还要本人背到麦子山上,老陆就是这样压断了腰,更令人气愤的是,即便这样,也拿不到现款,只给了一张白条。这里道出的是一个农民的艰难。而陆小北嫂子因两个鸡蛋和陆氏父子发生一场口舌大战,导致一死一伤的结局,这种辛酸的生存又怎么只讽刺了陆小北嫂子一人呢?
小说结尾处有一句非常优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话:“很长时间,眼前总有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在汹涌翻滚,仿佛《老人与海》中鲨鱼最后疯狂追击小船时的波诡浪谲。”将纠葛在文中的明线-----陆氏父子的遭遇,与潜隐在小说中的暗线----《老人与海》的情节缝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陆氏父子的人生困境,无望挣扎和悲凉结局与老人在大海中的一切是如此相似,这样将小说题旨拓展得极为开阔,他们既是现存乡村大背景下农民的最真实写照,又是困窘人生中的挣扎。
罗伟章的《奸细》是一部批评现行教育体制的精细之作,小说围绕新洲二中和五中的尖子生争夺战展开,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各类人的面貌性格,活现了中国基层教育的状态。
“在洋槐树丛中,耸立着灰色的教学大楼,底层大厅里,迎面立着块巨大的倒计时牌,上面写着距高考还有多少天,字迹如血。这块牌子,每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就竖起来,它不说话,却是最有威慑力的指挥棒,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着它转,全校师生匍匐在这块倒计时牌底下,忘记了梅雨,也忘记了春光……”这正是对高考指挥棒魔力的描述。
尖子生=升学率=活广告=大量择校生=财源滚滚,这个畸形公式滋生出的怪现状。火箭班里坐得密密麻麻,尖子生张泽君成了两校争夺的对象,也成了父母手中一颗赚钱的棋子,二中以重金将其挖过来,还许诺若考上名校予以十万不等的奖励。张泽君一来,学校巴结逢迎,迅速给其母解决工作,而为学校拼了十多年命的人,其班主任徐瑞星的妻子一直未能解决工作问题。因为如果张泽君真的考上了省市状元,“其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秋季开学的时候,蜂拥而来的择校生,会让学校的花草都浑身流油的。”二中的火箭班班主任徐瑞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在这场掐尖大战中充当了奸细,因此饱受自己道德良知的谴责。
而那些被掐了尖的学校和老师则坠入痛苦之中,比如张泽君所在的五中,张在那里六年,多少人为她付出心血,而在瓜熟蒂落之时被人摘走,“摘走了就摘走了,白摘!正因为这样,种瓜者心里的那份疼痛,该是多么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
由此道出小说的主题:以追求升学率为唯一指标的现行教育体制如何深刻地伤害了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如何摧毁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道德、人格与健康。以小说中被掐尖的康小双为例,为了工作,她不仅放弃一切娱乐活动,全副身心扑在工作上,拼命挤压学生休息时间,“随便去哪里,哪怕是去保温桶里接开水,康小双都迈着小跑,她的眼神永远绷得直直的,目光里有一种烧焦的糊味。”“她是把每一分力气都抠出来交给学生的,为此,她没当好妻子,也没当好母亲,可到头来却收获了这样的结果。”学生的辛劳就更不用说了。
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猎人》中的下岗工人杜老枪酷爱打猎,三天不摸枪就难受,一次打猎归来被人举报,遭到拘押并巨额罚款,杜老枪一家一贫如洗,老婆瘫痪在床。杜老枪在看守所不断被殴打,为了救出父亲,年轻貌美的女儿袖袖当了妓女,杜老枪出来后,偶尔得知女儿卖身得钱,激愤之下,开枪打死了那个上门要睡觉的嫖客。看似极普通的民间故事,却蕴含着深痛,作家对底层生存的关注。
《最后一个猎人》中“最后”二字隐喻着一种时代的变迁,自然生态被极度破坏,社会生态也在逐步恶化,猎人这一古老职业已无生存空间,他们手中的猎枪也称为被缴获的对象。而正是猎枪引发了一场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一个枪法极好的猎人成为杀人凶手,一个纯洁的小家碧玉沦落为妓女。故事在杜老枪杀人处戛然而止,后面的情节读者自会猜出,杜老枪自然会得到法律的惩处,杜家也将走向崩溃边缘,瘫痪在床的杜母,巨额外债,袖袖又怎么能拥有美好未来?这样的猜测自会重创读者的心。最后一个猎人杜老枪是被谁毁灭的?他的故事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小说笔调舒缓,带有沈从文的余绪,蕴含着极深的悲悯。喜欢小鸟的木鱼,石码头,爱吃野鸡野鸭的船老大,花街的红灯笼,不是带有沈从文《柏子》等篇章的影子么?不同在于,沈从文对那些船员和他们的爱情带着欣赏的同情,人性的温暖。而徐则臣笔下的船老大无疑是鄙俗的代名词,他们有了几个钱后就花天酒地,只图个身体舒爽。
杨沫《共度》写得平实而又诚恳,父亲患了肺癌,一家人被这场灾难拖入痛苦的深渊,普通人家原本过得极为艰窘,一旦有重大疾病就好比深海遇险。父亲住进了医院,为了照顾父亲,我妻子辞了职,女儿不能上幼儿园,母亲也病倒,一家人几十年的积蓄全都搭了进去,即便这样也未能挽救父亲的生命。尤其暴露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如脆弱的医疗保险制度等。
但可贵的是,在这场灾难面前,原本矛盾重重的家人团结在了一起,亲情重新凝结,十年未回家的葛淙回了家,坏脾气的父亲也向大家露出温暖友爱的一面,这样一家人在苦难中学习了爱。这成为小说中最可宝贵的部分,它告诉我们如何爱自己的亲人,并因出自自我疼痛体验而入骨入心。
荆永鸣《老家》是一篇读来格外沉重的小说,写作笔法类似于《在丰镇的大街上号啕大哭》。“我”在京城从事餐馆生意,而老家时刻牵扯着他的金钱和神经,这份乡愁和眷恋已经演变为疼痛,欲望的火焰已焚毁了古老的乡情,龌龊的交易活跃在街头巷尾,乡村一级政府从根子上烂了。竞选,本是极为神圣的事情,可在小说中成为金钱的交易,金钱的比拼,而当上官则意味着钱财滚滚。
叔丈人和二姐夫两家的遭遇贯穿始终,尤其着重刻画了叔丈人这个倔强、执着的上访老人的形象,他先为助儿子遇年竞选村长而借了十万块钱,但竞选失败后他也看开了。但儿子遇年为急着还借款而下了小煤窑,被熏死后又被扔进沟里冻了一夜,宣称冻死的,这使叔丈人一口气叹不下去,坚持上访,却不但告不成功,反而一次次被扭送回来,终于一次被送回后,他患上了喉癌,撒手人寰。
农村的衰败,农民的困顿,二姐夫是那种不停地折腾的农民的代表,种地、种烟、种药材、养鸡、猪、奶牛,做过各种努力想要改变家庭的境况,都是越挣扎越衰败,越努力越失败。养蚂蚁被“大力神”公司把一万多块钱骗走,既使人被抓住了,钱却挥霍完了;政府号召养奶牛,却牛饲料越来越贵,牛奶越来越不值钱,又蚀了本儿。他们想投资、想赚钱却没有任何门路,越折腾越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