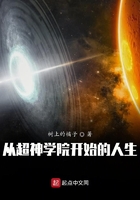林萍突然病了。
我得知这个消息是她住院的第三天了。老岳母打电话告诉我,说林萍病了。我问是怎么回事,老人家在电话里说她也不太清楚,只说是什么长了什么瘤。大概挺严重的。放下电话我就往医院赶。我要去看她。
这个消息太意外了。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她还像还挺好的。
那个晚上,她到我住处去取楠楠忘记在我那的作业本。我们坐在屋里说了会话,都是关于楠楠的。当然,她也问了我最近的一些情况。我很奇怪我们这样的关系。我们像是朋友,又像是陌生人,就是不像一对已经离了婚的夫妻。她当时的那种泰然,让我感到一种冲动,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想破坏我们既有的这种关系。我似乎想要证实什么,又似乎是想毁坏什么,反正就是不想让她这么泰然地面对我。
我想:要是我侵犯了她,她会怎么样呢?
我想知道她的反应。
就在她转身已经要走的时候,我突然一把抱住了她。我知道我那样做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已经是离了婚的夫妻了。可是,那个晚上,我有点不顾一切。我想要让她在我面前完全地放弃自我,惨败而回。她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的柔美。“W,你想干什么?放手啊你放手你不放手我要叫了。”她气坏了,并且竭力地挣扎着。可任她怎么挣扎,我就是不放手。
“你叫吧,你愿意叫就叫吧。我才不管你。”我说。
“你这个流氓,你松手!”她拼死抵抗。
可是我就是不松。
最后,她满脸通红,终于把那力气一点点都用完了,被我推到床上。
……我大口喘着气,仰面朝天。她不说话,在一边蜷着身子。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对她,但是我忍不住。我轻轻地在她后背上抚摸着,“生气了?”我问。她不说话。刚才的那种感觉好极了,特别的刺激。在我们过去的婚姻生活中也很少有。我非常的疯狂。她后来默默地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她的体形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好,皮肤白皙,双腿修长。“别走,”我说,“再躺一会。”可是她明显地加快了穿衣的速度。短裤、长裤,然后才是胸罩。她的乳房一点也没下垂,丰满、挺拔。过去她穿衣服总是先穿胸罩。她可能气糊涂了。
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是门“咣”的一声。我开始感到羞愧起来。是我强迫了她。她内心里是反抗的,可是身体最后又屈服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没有男人。我相信是这样。当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反应非常强烈。她为自己的那种强烈感到了羞愧。我想消除她那种羞耻感,就在她耳边说一些亲热的话。那些亲热的语言正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而我的这种亲热语言更加强了对她的刺激,她越发感到羞愧。在精神上,她坚挺着,可是在肉体的欲望上,她却败得一塌糊涂。
她生气了。
很长时间,她电话也不给我打了。她真的生气了。而她这一次生病,却给我提供了一个赎罪的机会。在她走后那个晚上,我在心里一直问自己:这次关系,仅仅是我的性欲在作怪吗?好像不完全是。如果是这样,我不应该会这么的内疚。我是不是还有些爱她?那倒还有点可能。我们还有一些情意在。比如,她那次请我吃饭,提醒我注意一些事情,还是很关心我的。但是我们要复婚,也是不太现实的。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目前的这种自由状态。虽然,我也很想再有一个家,感受家庭里的那种温馨,可是,要以自由来换取,是不是代价大了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犹豫。
我匆匆赶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家正在走廊上,看到我,眼睛就红了。
“她说她半夜就感到不舒服,后来楠楠去上学了,她也没能从床上爬起来。我把她送到医院来,医生给她做了检查。现在医生说是子宫可能有问题,要切除掉。”她说。
我问:“有危险吗?”
老岳母摇了摇头。
林萍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得出,她非常的虚弱。“你怎么来了?”声音里透着一种非常的不高兴。
“我刚听说,”我说,“就赶来了。”
她半晌不吭声。
我说:“我是好心来看你么。不要紧的……”
她还是不说话。
我就在边上默默地看着她。我知道,她还在生气。
“我病了,照应一下楠楠。”许久,她这么说。
我坐到了床边,拉住她的手,说:“你放心吧。”她把脸别到一边去,不想再看我,抽回手,轻声说:“你不会烧饭做菜,要不,你让她到我妈妈家里去吃。我妈会照顾她。你每天接送她上学就行。”我说:“你就不要操这样的心了。你现在还要人伺候呢。你爸和你妈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他们还要人照顾呢。”
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见了我,问:“你是她丈夫?”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他看我的眼睛顿时放大了一下。我知道我让他刹那间迷惑了。“……呃,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说。医生就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一位护士拿了一份合同过来,要家属签字。岳母有点不知所措。她怕得厉害。她不知道签了字以后,她的女儿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倒好像是如果她签字了,女儿的性命也就会从此断送掉一样。而那份医疗合同也的确赫然写有:“……有一定危险,经家属同意……实施手术……医院概不负责……”等字样。
我对岳母说:“这是一个必须的程序。您签吧。”老人家颤抖着,哭起来,说:“我……拿……拿不住笔,你、你签吧……”我有些犹豫。我不是怕承担责任,而的确是考虑到由我来签不合适。因为,我已经不是她的“家属”了。医生过来,对我讲了一大堆医学上的问题,大意是林萍的问题不是十分严重,需要做手术,把子宫切除掉。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必须要做。如果不签这份合同,手术就会被延误。
看到岳母那信任的眼光。我终于在家属那一栏签上了“同意”字样。
林萍单位的同事这时也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不少。她们都在走廊上叽叽喳喳,看到我,有些异样。我也感觉有点不自然。现在,客观上我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我是一个离了婚的丈夫,――前夫。前夫,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她们拉住林萍的母亲,一直安慰着她。而林萍的妈妈却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我感觉她的手特别的冰。
“不会要紧的,不会要紧的,”我一直对着她这么说,因为我知道她的身体并不好,经不起紧张,“会好起来的。这种手术好起来很快。”
从医院出来,在去学校接楠楠的路上,我心想:在林萍那些同事的眼里,其实她也是一个挺让人同情的女人,离婚了,带着女儿过,现在突然又得了这样的重病。虽然她可能不再需要生育了,但是,一个女人切掉了子宫,从性别学意义上讲,她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
与有些离婚夫妻不同的是,我们离婚后,关系在一点点的恢复。我们并没有反目成仇。除了女儿的因素之外,还因为我们都算是有点文化,我们不想把关系搞得特别紧张。
楠楠被我接出来后,我告诉她,妈妈病了。她居然没有什么反应。现在的孩子,真是被宠坏了。“妈妈得了什么病?”半天,她才这么问我。我说:“可能是子宫里发生了病变,需要切除。”“很重吗?”她问。我安慰她说:“没什么。当然,可是也不是一件小事。你妈妈会很痛苦。”她现在还小,不知道失去子宫,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林萍一直是个内心比较骄傲的女人,除了离婚这件事给她一些影响外,她觉得自己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连离婚的错误也不在她,而在我。真的,她就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不是违心这么认为的。现在,要切除子宫,她肯定很难过。
“以后,让爸爸接送你。有空了,我带你去看妈妈。”我说。
楠楠点了点头。
马青打电话告诉我:过去来找过我的那个布清正在接受上一级纪委的审查,他在过去的信贷业务中,有多次违规行为。恐怕,这次他要倒霉了。
当然,这跟我的小说没有关系,一个有问题的人,早晚要出事,我想。但是,我的小说有没有客观上给他造成一些影响呢?马青说:“你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他们银行的人都在争着看,对号入座,和他挂上了钩。”
“这跟我没关系。”我说,“他这种人早晚都要倒霉的。”
“你别看他才是一个信贷部主任,这种人手里的权力却是大得很。你要贷款,就得求他。国家银根紧缩后,一些企业不敢贷了。另一些企业却拼命要贷。这要贷的里面学问就多了。”马青说。
“一部小说能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倒也是个功绩。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应该给我一个奖励。”我笑着开了一个玩笑。
马青说:“这个布清真的就认为是你的这部小说害了他。你在小说里写的那个包簿清和他真的是有些相像。一个单位里面,本来无风还三尺浪呢。你的小说出来,有人与他不睦,就是趁机搞他呗。”
那也还是不能怪我。自己本身有问题,能怪谁?
“你别说,你这部小说影响还真大。大家都在谈,说你这部小说里面的谁谁谁是谁,谁谁谁又是谁。主要是老百姓对现在对一些事情看法太大,你这部小说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议论的借口。”马青说。
我说:“你把我小说的作用说得太夸张了。”说真的,我现在已经怕人们再议论我这部小说了。我希望人们议论我小说的是艺术,而不是有关影射。我无意于影射任何人。如果大家都这样看,好像我的影射就是铁定的事了。在人们的印象中,我不就成了鬼蜮了?鬼蜮,最早载于宋代《四方记》,传说能在水里暗中伤人。非常可憎的一种小动物。在开始校对这部小说之前,我以为人们一定会对我的叙事艺术更感兴趣呢。
这样的局面让我有些沮丧。
“你要当心,布清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们扬言要找你算账。”马青对我说。
我说:“他怎么还有黑道上的朋友?”
马青说:“也不一定是朋友。他花钱买呗。那种人,只要你给他钱,他给谁卖命都一样。据说有个叫裴三的,是布清的好哥们。裴三在马台街那边开了一家饭店和一个网吧。你不要惹他。”
我说:“我怎么可能惹他?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谈过这次话的后两天,在去医院看望林萍的路上,我一直感觉仿佛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一会感觉里是一个和我一样骑自行车的人,一会感觉他是徒步而行,一会感觉那人开了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在跟。当我回过头去,阳光灿烂,大街上的车来车往,人们忙忙碌碌。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完全是受了马青的暗示。
做过了手术的林萍脸色稍稍好转了些,不像前些天那么难看了。她让我坐下。我带了些营养品给她。在她的床下,已经堆满了朋友们送她的东西。过去在单位里,她一直就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等我完全坐定后,才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男人。开始,我以为那个男人是17号床病的家属,但很快我就明白他和林萍的关系有些不正常。那个男人年纪和我相仿,也许比我还要大几岁。那样子,一看就是机关里的。
“这是楠楠的爸爸。”当我的目光长时间和林萍对视后,她好像才不得已对那个男人介绍说。
那个男人笑了笑,过来,和我握了一下手,稍稍有些尴尬地说:“我叫Q。”
我问了问林萍的感觉,她说一切都还不错。她问楠楠的情况,我说楠楠还行。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男人就站起了身,向林萍作别,也顺便向我作了一下别。
“他是什么人?Q什么?”他前脚刚跨出病房的门,我就这样问林萍。
“你好像没有必要知道啊,”她说,“我的一个朋友,省机械厅的。”
我心里泛起了一股醋意,“男朋友吧?对你挺关心的。”
“别人介绍的。”她说。
“对你挺不错的,”我说,“这是一个机会啊。”
林萍说:“这跟你没关系!”
我心底忽然就生起了一股怒气,跟我没有关系?你曾经是我的女人。我的!虽然离了婚,可我现在心里没有打算完全放弃。也许,我还会要你。如果我还打算要,你就不能跟别的男人谈婚论嫁。你这样绝情,可我还有情,难道我不是一听说你生病的消息,就马上赶来了吗?我生了气,可是我没有发作。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一个病人。
一定是我的脸色非常难看。她也一定为自己说出这样过份的话感到内疚。她的手这时主动抓住了我的手。
“等你病好了,我们……”我说,但后面“复婚吧”三个字到了嘴边却又缩了回去。因为,我想让她主动说这三个字,而不是我。
“什么?”她看着我。
我说:“没什么。”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说我没想说什么,可能我想要说一件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忘了。我说我现在记性很不好。“你还生我的气吗?”我问。
她叹了一口气,眼里好像有泪水。
我说:“是我那天错了,不行吗?向你道歉!”
“不用,”她看了我一眼,嘴角还笑了一下,“你真是太过份了。我完全可以去控告你。婚内还可以定强奸罪呢。你现在可是婚外强奸。”
她一笑,气氛就轻松多了。我就也笑起来,说:“强奸就是强奸,没有婚外强奸这一说法。你想告就告呗。”
“不要脸!”她轻轻地骂了一句。
林萍的母亲来了,给她送来了鱼汤。老人家没对我说什么,她只是用眼神向我表示了她的感谢。按理说,这时的我真的可以置之度外了。但是我想我不能那么做。我们毕竟还好么。想到刚才那个男人,不知道我的前岳母知道不知道。也许她知道,并且也同意支持,所以,她才会对我用感谢的眼神。这么一想,我心里又开始不快起来。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罗萌萌会来。
当时我正在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和几个朋友打球。手机突然响起来。大家停下活动,纷纷去看躺在操场边草地上的衣服口袋里的手机。一个个放下衣服一脸的失望又回到球场上。而手机还在响。我走过去,捡起自己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喂――”
电话的那边传来罗萌萌的声音,“干嘛呢?”
我说:“在玩球。”
“我今晚到你那边去。我现在在火车上呢,快到了。”她说。
我叫起来,“你开玩笑!”
她说:“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相信我?你是不是不欢迎我去啊?”
我连忙说:“不是啊。”
她说:“如果你不欢迎我,我就找别人去了。”
我说:“真的不是,我怎么能不欢迎呢。我是想你在捉弄我。”
“一个半小时以后就到你那里了,现在车子已经到了涂县。”她非常认真地说。
我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她说:“今天早晨六点的火车。”
我算了一下时间,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她不可能开这样的玩笑。我说:“那么,我到车站去接你吧。”
她高兴地笑起来,说:“好啊好啊。”
朋友们看着我。我抱歉地说:“不能打了,我要到火车站接一个人。”朋友们说:“女朋友吧?”我笑了一下,说:“差不多吧。”大家就宽容地笑笑,散场。正是星期天,那就早点散吧,回家洗洗,休息好,明天还要接着上班呢。他们跟我还有些不一样。我是一个不用坐班的人。
火车站里乱哄哄的,到处都是人。在出站口,站满了等客的人,更有一些旅店的服务员,左顾右盼,寻找目标,拉人住店。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了。罗萌萌乘坐的47次还没有到。一趟一趟的人流往外涌。我有些焦急起来。我掏出手机,拨通了她的号码,“喂――”我说,“你现在在哪?”她说:“我正在车上呢,马上就到,已经进站了。”
又是一大批的人朝外面涌过来。那里面好像就是一只魔瓶,源源不绝地向出口处吐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又一批人出来了,是47次的人。我努力地张望着,没有看到罗萌萌的身影。突然,一个俏丽的笑容出现在灰色的人流里,是她。我有些兴奋地冲她扬了扬手。她也看到了我,也朝我这里摇了摇手。
“来啦,”我一把接过她的包(她背了两只包,一大一小),拥着她向停车场走去。
“你没有想到我会来吧?一个突然袭击。”她开心地笑着,很得意。
“我不是一直叫你来吗?你来了我很高兴啊。”我半搂着她的肩膀,在她耳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