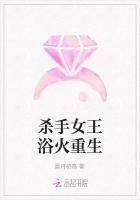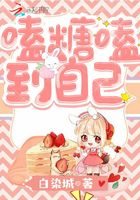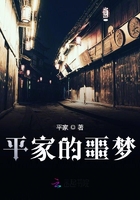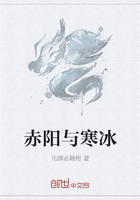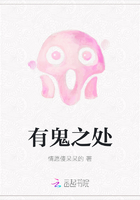群山环绕白云飘,小城西河涌波涛;山水相连岸边站,新街新貌新学校。
日落西山,夜幕低垂。黄昏夹着习习的凉风飘然而至。
这时候,李静和她的家人有拉车的、有推车的、还在匆匆忙忙地往前走。
“还有多远?”李静问父亲。
“二十多里。”李新刚拉着车子弯着腰低声说着。
“黑灯瞎火走夜路,二十多里地要走到啥时间?”李静发着牢骚。
李静的母亲王秀兰说:“夏天,白天长夜晚短,现在太阳刚落山,咱们趁着天亮走快点,我看摸黑走不了多远。”
“爸,你让我拉一会车,你歇歇。”李静说。
李新刚好像没听见一样,只是弯着腰、拉着车子走的更快了。
王秀兰看了看李静说:“你自己走好就行了,你根本拉不动这一车货。”
李静是心疼父亲才说要拉车的,一路走来几十里路父亲一人拉着一车货太累了,她真想让父亲休息一会,自己拉车。听到母亲这么一说,她紧跑几步上去使劲的推车,给父亲减轻负担。心里想: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帮父亲拉车。
屋漏偏遇连阴雨,越急越有烦心事。
“前边有一段公路坑坑洼洼、极其不平。”李静的母亲说。
李静放眼望去,只见前边公路上,小坑连着大坑,大坑套着小坑,路的表面好象大海波涛,起伏不定,连绵不断,更象大海涨潮时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
李静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乡间公路、而是一条通往外地的省级公路。“这一段路为啥没人修呢?”李静在自言自语。
“姐,你看这条路,小坑可以卧头猪,大坑可以卧头牛。”李静的弟弟李林叫着。
“走这条颠簸、崎岖的公路,真是太费力了。”王秀兰插话。
李新刚接着说:“这是一条能走到新县城的唯一公路。”
李静在后边推着,车子在公路上左右摆动,家俱在车上晃来晃去。
“前边有一个大坑,往左拐一点。”王秀兰对丈夫说。
李新刚车把一扭,往左边急拐,由于用力不均匀,车子晃了一下歪倒在地上了。
李新刚先把车上的家俱,卸下来了一部分,然后,几个人才用劲把车子扶了起来了,物件却掉了一地。
李静和弟弟捡起地下的东西递给父亲,李新刚把东西重新摆好,用绳子绑了又绑说:“这下没事了。”
“咱们快点走,走过这一里多路,前边就是石子路了。”王秀兰在催大家快走。
费了好大的劲,李静和家人,终于走过了那一段崎岖不平的公路。
走着,走着,天黑了,王秀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电。借着手电的亮光,他(她)们快步如飞地往前走。
前边有好大一片灯光,母亲说那就是新县城,这里新建了一个发电厂,家家户户都能用电灯照明。
李静在老城十几年,都是用煤油灯照明,每天清晨上学时,手里还要拿一个,自己制作的小煤油灯去学校。这里跟省会城市一样,能用电灯照明,心想这里真好。
李静虽说从小在山里长大,步行走过很多次山路,但是这一次,一整天走了九十里路还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累的她上气不接下气,腿痛腰酸,早就不想往前走了。
到了,到了,终于在晚上十一点钟走到了新县城。
左拐右拐,李静们到了他(她)们的新家,新家只有一间房,房子从中间用竹笆隔开,后半部分放了两张床,中间放了一个三斗桌。前半部分是厨房,一个烧柴的大地锅占了很大地方,擀面条的面板只有放在门后。从老家拉来的东西把这间房子塞得满满的。两张床中间有一个空间,放了一把椅子。从房间里出来,必须穿过锅台边上一条小路才能走到外边。
李静和弟弟每人一张小床,一个抽斗。母亲王秀兰住在单位里的另一间房子里。
第二天清晨,李静和弟弟就急着出去,看这个新县城的新面貌。
李静走出家门,看了看自己家住的这个院子,北边是一排平房,西边也是一排平房,东边和南边是一条没有水的大深沟,院子有一个大门朝西,从大门走出去是一条五六米宽的大路。
她站在大路上抬头一看,前面是一座大山,转身又看还是大山,转了一圈看来看去全是大山。
在老城时,大人们都说这里是老北山,今天一看,果真不假。
四周全是大山,中间一块平地上建有很多房子。
顺着大路往前一拐,是一条宽有七八米的大街,街道不长,一眼就望到了尽头;大街两边有小商店和饭店,还有一些单位的大门夹在其中。
李静很快就发现,这条街不只是单单的一条街,而是东西南北四条街。大概走有两百多米,她就走到了十字街的中心。十字街的西北角上:是一个大商场;东北角上:是一个新华书店;西南角上:是一个县招待所;东南角上:是一个大剧院。
她顺着街道往左拐,走到了另一条街上,这条街上有很多山民在那里卖山里果和柿子。
“山里果多少钱一串?”李静在问。
“一毛钱两串。”卖家看了看李静又说:“你若是要的多,一毛钱三串。”
李静掏出一毛钱,买了两串。她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的往前走,走到这条街的尽头,看到前面是一所小学挡住了去路。
走到学校前面,峰回路转,她又看到了一条路往右拐,路边上是一个早市,早市上卖菜的、卖山货的、卖小商品的应有尽有。看过早市后,继续往前走,有一个大桥,大桥两边有很多人在那里卖柴和买柴。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山区里没有煤烧,家家户户都是买木柴、烧地锅做饭。
穿过卖柴的,往前走是一条老街,街道很窄。再往前已经没啥看的,李静就转身回家。
“这个新县城比起老县城,街道太少,真是差远了。”李静回家后对母亲说。
王秀兰正在烧火做饭,看到女儿出去半个多小时就回来了。她对女儿说:“新县城刚建不久,老县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里还正在建设,过几年一定会建的更好。你和你弟弟这些天先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再有一个月你们就开学了。”
母亲上班了,父亲回老城了。李静和弟弟闲逛了将近一个月,走遍了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
开学了,李静和弟弟跟母亲一块到新学校报了到。由于李静的名字要改成王静,李林要改成王林。母亲还费了几天功夫。
那个时侯,因为备战的需要,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一个年级是一个连,一个班级是一个排。
王静被分到了初中一年级一连三排,上课的第一天,就是排队分座位,男生排成一队,女生排成一队,然后按顺序一排女生一排男生。
王静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左右看看,又扭头往后看。“是你,你也分在这个排里。”王静很惊讶地说。
后边坐的那个男同学,竟然是她搬家避雨时,遇到的那个小伙子。
“真巧,咱们分到一个排了。”“我叫张立国。”
“我叫王静。”“你家住在哪一条街?”
张立国说:“我家住在老街。”
“我姑奶家也住在老街。”王静想起了她母亲的姑姑。
开始上课了,王静因为基础太差,老师讲的数学课一点都不会,物理化学更是听不懂。
张立国比王静大两岁,小学六年的课程全部学过了,基础扎的牢,学习比较踏实。
上数学、物理、化学课时,王静要是听不懂,下课后,王静常常扭头请教张立国。
久而久之,王静的学习有了很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