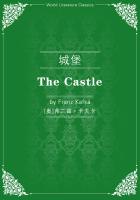一个,--心里扎上一刀两个,--心里扎上一刀三个,--心里扎上一刀四个,--心里扎上一刀五个,--心里扎上一刀一具一具冷冰冰的尸体被抛进大海,于虎的一颗心已经扎个-长篇小说稀烂,鲜血淋漓。当他就要数到第十三个人,这是个不吉利的字眼,有些街道没有第十三号门牌,有些饭店没有第十三号房间,因为在《圣经》里这是耶稣受难的日子。这一点,于虎不知道,全底舱里的人都不知道。可是,现在这个十三,像箭一样刺到了于虎心上。当于虎好起来时,江天柱却病倒了。一天天刚亮,于虎还两眼朦胧似醒未醒,有一个人从那边人群里挤到于虎身边,气喘吁吁地说:“江天柱叫你去,他--泊不行了!”于虎一听整个脑袋轰地一响,他三脚两步、急急慌慌向那里走去,蹲到江天柱跟前一看,江天柱脸上已经失去生命的活力,一但江天柱很安宁,很平静,他在张嘴说话,可是于虎听不见,于虎连忙饥下身将耳朵贴到江天柱唇边:“我……不……行了!来个……海葬倒也干净……只是这难兄难弟舍不下……给你……你要担起这个担子,领出一条路……”他抖颤颤地取下别在腰上的一只葫芦,递给于虎:“……你们去淘金……难……免……逢……上……跌……打……损伤……逢上瘟疫……这药用得上……我……我只有一个心愿……把我从船尾扔下去……让……我的魂回向东方……”他说着人头一歪,再也没动。他那样祥和,那样平静。于虎喊叫:“老大哥!老大哥!你不能呀!”可是他摸着江天柱的手,手已经像一块大理石一样冰凉了,凉得那样透骨,那样阴森。他死了,但死得坦然,死得高尚,--个多世纪过去了,现今的人还知道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灾难深重的时候,在太平洋上飘洋过海的这群苦难的灵魂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是圣者,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但他是圣者,--于虎两手紧紧抱住葫芦,好像抱住江天柱的整个生命,于虎哭了!但他咽着喉咙不让出声,一片眼泪洒湿他的衣襟,他心中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像江天柱一样,死死得尊严,活活得郑重,不能让整个底舱的人死心绝望,要带着他们走呀!”他哭了一阵,猛醒过来,用力在脸上抹了一把,猛地站了起来,他想:
“上天有灵,他的尸骨归不了家,也让他的灵魂归得了家!”
他迈上甲板,约翰想拦他,却给他吓住了。约翰看见于虎两眼闪着锐利的眼光,约翰刚伸手,就被他一掌搪开了,--他就踏着甲板向船长室走去。
贝吉特一见他这情景也愣住了。
贝吉特想笑,但倏然间又把笑收回。
于虎很礼貌地说:
“船长!我于虎有一事请你相帮!”
“你说,你说……”
“我们整个舱底人的老哥哥死了……”
贝吉特像躲闪利剑一样,吞吞吐吐说:“这……这不干我的事!”
“贝吉特先生,我不是跟你来算账的,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事请你相帮!老哥哥临终只有一个愿望,就是由我亲手把他送到船尾,面向东方,抛进大海,让他的魂能回到他的家乡。”
贝吉特是一个凶悍的海盗,但又是一个慈悲的有神论者,他在神的面前常常低下头来。现在正是如此,他认为他为这个中国人的灵魂做一点事,是神的旨意,但迟疑了一下,提出条件,他所以提出条件,实在是出于胆怯,他的蓝眼珠盯住于虎,他心里盘算不知这个对手有什么想法,他小声说:“不能全部出来送葬,这颠簸的老船,可受不了那么折腾……”“不,贝吉特先生,我们不会让你为难一我们只出六个人就能抬起死人的尸体了!”“好!”贝吉特一下轻松下来。
于虎回到底舱,商量一下,推出六人,把江天柱的尸体抬起来。于虎一手抬着殉难者的左肩,一手捧着殉难者的头,他忽然觉得这个失去生命的身子却很轻很轻。这个时候底舱里所有的人都跪下了。在这苦难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江天柱这个忠诚朴实、大公无私的人,为大家不知做了多少好事,可是在船离美国这个新大陆愈来愈近的时候,他的灵魂升天了!他的灵魂升天了!于虎明白江天柱常说的一句话:“同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可是现在不是为了过佳节,而是为了送葬,但是于虎跟江天柱谈了许多话,江天柱却没有把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告诉给于虎。于虎想到他活着普救众生,他死去孤魂苦鬼,他心里一阵凄然,但在这时他激励了一下自己,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把他的后事办好……中国人不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们远走他乡,但还是按着中国人的方式生活。现在,就在这海洋上浮动的地狱里,人们还是跪膝拜着他们可尊敬的人,而且认为他们的信心会送他的灵魂平安地回归故土。这时底舱里响起一阵不高的嗡嗡声音,于虎仔细分辨,听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将近两百年前,尽管人们生活在愚昧昏暗之中,但是人们的心是纯洁的,善良的,一为了淘到那黄灿灿的黄金,他们飘洋过海,风雨同舟,形同骨肉,生死相依。
于虎上了甲板。
他发现贝吉特本来恐惧一下又转为亲善的神态。尽管一方是奴隶主,一方是奴隶,但贝吉特很佩服中国人守信的精神,觉得中国人真是肃然可敬。海浪把甲板摇得一下向左,一下向右,不断来回来去地倾斜,于虎他们为了保护好江天柱的遗体,尽管飘摇动荡、蹒蹒跚跚,但他们像对待一个憇眠的人,不愿打断他的好梦,稳稳地抬着他向前走。这时,在这庄严、肃穆的气氛下,贝吉特走在前面,变成一个向导。年轻的约翰突然跑了上来,他不知从哪儿找到一件华丽的但已破旧了的睡袍,轻轻盖在遗体的身上,然后,他又很快地好像从红胡子胁下钻过去,悲哀地溜走了。但是,这并没惹起红胡子的恼怒,是的,贝吉特被这些中国人的举动所震慑、所感动了。
这是一个隆重的海葬的仪式。
于虎他们没有像美国人抛死尸那样,一头拎着腿脚,一头拎着膀臂,用力地悠了几下,然后抛向高空,砰然落进汹涌的海涛。不,于虎他们来到船尾,不论船在汪洋大海中翘得多么高,摇得多么猛。当雪白的海涛一下卷上来时,他们灵活而乖巧地将江天柱推入这海涛,他们的心里想到这海浪如有神意,是来拯接这圣洁的灵魂的。于虎带头在甲板上跪了下来,一他们向海涛进行祷告,苍天垂泪,大海呜咽。当于虎站起来时,突然给一个可怕的场景所震动了,他看见海水中鲨鱼成群,它们锐利的脊翅一下露出海面,一会没入海底,它们凶狠地嗔到血的气息,追逐着船只……在那并不太古老的年代里,太平洋呀!一你承受着多少罪孽,多少悲痛,由于抛下去不计其数的活人、死人,鲨渔追逐着,吞噬着,一艘一艘贩运奴隶的船尾上都漂浮着战栗着鲜红的长长的血的飘带,你给德沃沙克的美妙的旋律鸣奏过的新大陆呀!你繁荣,你豪富,你成为金元帝国,而你的每一个金元上都染着这鲜红的血。太平洋呀!你应该放声痛哭,太平洋呀!你何曾有过太平!于虎经过那一阵恐惧之后,他不能再看,他不能再想,--他仰望青天上一无所有,可是他觉得江天柱的灵魂正从那儿冉冉而去……他为了不破坏这庄严而神圣的葬礼,他忍着汪在眼眶里的泪水,没有让它流出来。不过,他在这以后,常常一人孤坐默默无言,好像有一个声音在问他: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他也无法知道自己怎么会落得这样。但是,他没有忘记江天柱临终的遗言,不过只是麻不仁地跟难兄难弟说话、做事,他甚至用言语鼓励大家,可是自己却渐渐失去耐心,他从上船那天起就机械地用指甲在身边船舱木板上每过一天刻画上一个记号,记号密密麻麻的,他看也看不清,数也数不过来了。可是这一只古老的机帆船还在大海波涛上不急不慌、浮游飘荡。
有一天,于虎在船帮上划下九个月零七天的记号,忽然听到约翰趴在船口上喊他:
“于!于!”
在这么漫长的航行中,有心计的于虎想到了美国语言不通,办事难,于是跟约翰学着英国话,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彼此讲话。
他看看约翰,他从来没有发现约翰这样快乐,一快乐得娇嫩赤红的面孔,晶莹碧绿的眼睛都在纯真的欢喜中颤动着。
不等于虎回答,他就喊道:
“看见了!看见了!”
“看见什么?”于虎原来嘲弄地看着约翰不知约翰为何疯疯癞癫,到了这种程度?忽然灵机一动,一种希望从心底升了上来,是不是他所盼望的那一刻时间终于实现了。
“美利坚,美利坚!”
“我不信……”
约翰被于虎装作冷淡的态度所捉弄,为了证明自己的明确无误,就向舱口下伸出一只手:
“不信,你上来看看。”
于虎抓住约翰的手,从舱口一跃而上。
从昏暗的底舱来到露天之下,明亮的阳光剌得于虎两眼一时昏花起来,他紧紧闭了几次再睁开来,他终于看到眼前一片蔚蓝色海洋波平浪静,大群大群雪白的海鸥在“噢噢”叫着,你追我赶,在头顶上飞翔。果然,在所到之处,出现了一条宽阔的黄色地带,这黄色地带很长很长,说明不是岛屿,而是大陆,一直忍着眼泪的于虎,这时,在悲哀中夹着欢乐,在欢乐中夹着悲哀,眼泪刷地流个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