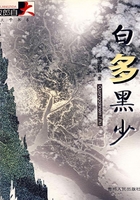飞机在太平洋浓墨一般的上空飞行着。
夜,是那样安稳、宁静,整个宇宙都在酣睡。
于飞醒过儿次一乘客不都把电灯扭小,机舱里一片低暗朦胧。
可是,他每一次都在望着那个老人。
老人一直都在抱着那小小婴儿缓缓地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
这是人类间多么伟大的爱呀!但,他每次都怀着这种感动,又甜蜜地睡着了。
天亮了。于飞有军人早起的习惯,机舱里还没什么人行动,他放轻脚步到卫生间去洗了脸,漱了口,又取出菲利浦电动刮胡刀。他把圆形的刀头按在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他觉得十分爽快,十分惬意,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把窗帘推上去,他的眉毛耸了耸,眼睛一下睁得大大的,他整个面孔笼罩着一脸的庄严(人在看到意外的美时,一而且美得激动人心,有人会欢笑,有人会庄严他要去的目的地波特兰,在美国西北角上,下面一望无际全是雪山。雪山,雪山,他心里赞叹着:“美国的大自然真雄伟”!这里跟喀喇昆仑山不同,那里像有无数高耸云天的黑色间杂着白色的巨柱,这里望下去,一座雪山连着一座雪山,千万座雪山,就像波涛形成一个洁白的大海。飞机一直飞了很久很久,下面一浪一浪都是雪海,他心里赞叹着:“美国的大自然真雄伟!”一他一下恍然大悟,这雪海是不会有边际的,也许从这儿就一直到阿拉斯加,白令海峡,北冰洋吧!
于飞在西雅图转机到了波特兰,在波特兰,当于飞下飞机时,穿上黑蓝色厚呢绒大衣,提了小提箱,随着人群向打开的机舱门走去。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啊!在这里,他又看见那位慈祥的老人,他们好像不急于挤在人群里,老人抱着那小小的婴儿在缓缓地走来走去,他走到那老人跟前,看到他怀中的婴儿,赤红的小脸皱成一团,小嘴翕动着,多么像一只小猫呀!再看那老人,满发白霜,脸上露出一种怜爱。一于飞突然觉得在哪儿看到过这个形像。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基罗雕塑的圣母像一虽然那一个抱着死亡,这一个抱着新生,但那慈爱的面容多么相像啊!于飞心里又浮起夜间想过的,多么伟大的爱啊!不,不是伟大,而是崇高,如果这个世界充满这种崇高的爱多好呀!当他走到那老人跟前时,他从老人眼光里看到一种亲昵,俩人目光相对,于飞对老人微微一笑,显示出他对老人的尊敬。
他下飞机,走出廍道,就听见一个沉重而洪亮的声音:
“哈啰!于--飞!”
于飞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后是白皮肤里渗透出嫩红色的面孔,一双会笑的眼睛。两个人的心都在抨怦跳,一下拥抱在一起,“老朋友!到我们波特兰来了。”然后,挽着于飞的手臂,走向取行李的大厅。两位朋友一面在缓缓拖转运货轨道旁边站着,一面交谈。于飞:“这雪山真美极了。”“是的,这是波特兰人的骄傲。于飞:“噢!是我的了……”一只蓝布布套包裹着的大箱子从运送带上转了过来,他刚要弯身去取,汤姆森已经伸出长长手臂一把把箱子拉出来。于飞:“几十年了……你还是有一个外科医生的手劲。”汤姆森洋洋得意:“我还在动手术。”他们争执了一下,还是于飞把沉重的大箱子提到手上,走出站台。“于!等一等……”他把于飞拉到一幅墙壁画面前:“这是这个大地真正的主人!”于飞看到墙上画的是印地安人图画,等汤姆森开着汽车驰行时,于飞一种屠戮的血腥冲击到他心上。这和飞机上那慈爱的老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怀着困惑心情沉默不语,他在想:“美国人不掩饰历史,这是他们坦白的一面,可是为什么在机场上画那样大的壁画,难道是为了引起前来旅游者的好奇心,来寻觅印地安人踪迹吗?也许是,不过汤姆森指给他看显然是掀开美国历史的一页。”于飞想着他渊博的知识与智慧,他记起他曾读过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记得看到一段有关印地安人的话:“在1615年以前,光有72,000亚尔冈山人《印地安人的一个部落》,居住在南缅因到赫德逊河之间。到1690年他们不是被歼灭,就是被奴役。不论怎样替英国人对那部落文化所持的偏见进行开脱,不论怎样强调他们想把印第安人转变为基督教徒,那种半心半意的虔诚,不论怎样诉之于土地是从印第安领导人手上合法买来的虚构故事一没有任何东西能掩盖这一野蛮残暴的真相。教徒领导人对这一有步骤的、残酷的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和疯狂的种族灭绝的杀戮是负有责任的。”于飞忽然发现自己沉湎往事、缄口不言,几乎连沿途经过什么地方都没看见,对主人是不大礼貌的。他脑子灵活地一转,他认为称赞波特兰的美丽主人总是愿意听这种恭维的。于是他说:“你们这里的雪山真好看极了!”“你来的季节不合适,你知道波特兰是出名的玫瑰花城。夏天,那满地的鲜花和空中雪山相映成辉,才是最美的。”
这样一来,他们之间忽然就谈起来。
“我给你夫人打了电话,告诉你今天到,她说白天要到实验室,要夜晚才能来电话。”汤姆森俏皮地陕一陕眼睛,“你得忍耐。”
“老朋友,我到你家里,就是到了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