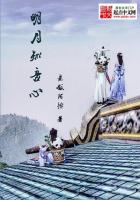客厅里剩下我伯母和我。
我目测了一下,她的这套房子大约有一百二十平方米。她单独一人居住在这里,她的父母兄弟都各自有房子。如果我伯父搬到这里住,无疑更舒适一些。但是,我伯母说这个建议曾经提出过,却被许喜鹊一口回绝掉了,差点都翻脸了。“你伯父认为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呵呵呵,有那么严重吗?真是大男子主义!”
我不免偷笑了一下。我伯父如果还能跟大男子主义挂得上勾的话,那“大男子主义”一词就得重新定义了。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我伯母问。
我摇摇头。说真的她的名字叫什么我有必要知道吗?偶尔之中,我撞上了这个婚礼,然后来参加了,仅此而已吧。我伯父和我一家甚至同我奶奶都已经隔绝了二十年,以后也不能指望有什么改观。
“我叫艾菲儿。”她说。
我明显感觉到她说出自己名字时的得意劲,看来她很喜欢自己的名字。艾菲儿,我的天,读着像个六七岁小女生的名字。
伯母说我今年三十三岁。伯母说我一次婚姻都没有过。伯母她又说我是医生,生殖泌尿科的副主任医生。我伯母不停地说,边说边夹着娇羞的笑。一个开朗与娇羞结合得非常完美的女人。我都不明白了,我伯父这一把老骨头,怎么能把这么活色生香的女人弄到手?我想起了我母亲,这样不好,可是一看到伯母,我还是不可扼制地想起我母亲。公正地说,她比我母亲出色,年龄姑且不论,其他方面,比如大城市女子独具魅力的自信自得,单这一点我母亲就没有。
我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如果沙佳邦是我伯母的女儿或者妹妹表妹,我伯母说着说着,嘴里突然蹦出沙佳邦长沙佳邦短,那该有多好啊。沙佳邦也是北京人,虽然北京有一千多万人,但电视电影中常有这样的巧合,甲见到乙,发现乙是丙的亲戚,所谓无巧不成书嘛。可是,我也就是想想而已,我伯母她已经说过,她是未婚的,至于妹妹或者表妹,那根本与沙佳邦挨不上边。我对自己说,就死了这份心吧。
在动身去饭店之前,我刚认识的伯母十分快乐地跟我聊个不停。幸亏我来了,我伯父他独自坐进书房,还把门关紧,他一点都不像个做新郎的人,看上去我倒更像。我风韵犹存的伯母穿一身玫瑰红的套装,化着稍微有些夸张的妆,神采飞扬,顾盼生辉。客厅的白色大沙发把她那一身行头衬托得更加夺目。我由衷地赞美到:“你真漂亮啊!我伯父他可有福了。”
我伯母对此倒不谦虚,她深有同感地点点头,抿抿嘴,做掉这两个动作后还灿烂地一笑,对我的知音般的赞美致以衷心感谢。“幸亏我长得还不难看啊,”她这么说,表情一下子认真了起来,“我要是长得太难看,要是太老了,你伯父会要我?做梦!”说到这里她语气猛地昂扬,脸也跟着放松了,笑意像波浪一样一层层堆上去。
我有点明白了,我伯父娶她,是因为她的年轻美貌。可是,这二十年来,围绕在他身边的青春美人何止这一个?二十年都心如死灰,怎么突然又色欲纵生?
我伯母咯咯咯地一阵大笑,然后说:“是我勾引他的!”
她好像被自己逗得越发兴奋了,我看到她两眼都散发出礼花般的绚丽色彩了。她说:“我二十五岁就开始追他,我追了他整整八年!八年抗战。”
她说:“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男人啊!”
她说:“得到他我多么幸福啊!”
我坐在那里浑身都不自在了,主要是觉得有些为难。好比是看到一只羽毛优美的小鸟,天真无邪甜甜蜜蜜地往前走,以为走进的将是一块洁白无暇的圣地哩,事实上却是烂泥潭臭水沟。在一旁观看的我,真不知该不该友善地提醒她一下。
我说:“我伯父身体不太好。”这样的说法应是合适的。
我伯母怔了一时,情绪显而易见地低落了一些。“就是这一点有些遗憾了,如果他没有病就好了啊。”
我以为她指的是脑子上的病,我伯父进过精神病院,那可不是一般的医院,脑子上的病有着最顽固的遗传性,做医生的人不会不在意。我说:“就怕孩子以后也得这种病。”
我伯母突然笑起,好像我的话让她很开心。她开心什么?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堂弟或者堂妹,或者可能是许盼望的弟弟或者妹妹,如果脑子也出毛病,对许家来说,都是可悲的事,有什么好开心的?
“凯歌啊,你怎么也像你伯父一样傻!”我伯母探过身子在我脸上轻轻拍了拍,这个动作完全是长辈式的。我发现她的手很细,很软,有着绸缎般的感觉。我喜欢她的手。她的手在拍过我之后,又交叉着,搁到玫瑰红的套裙上,顿时被衬得晶莹剔透,宛若一枚放在天鹅绒上的珠宝。
“凯歌啊,”她又叫一声。我希望她手再往我脸上拍,可是这一次她的手没有动,但身子动了,她站起来凑到我耳边,小声说:“我们不会有孩子的,你伯父精索静脉曲张,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男性不孕症。”
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她没有抹香水。女人有没有抹香水,抹的是什么品质的香水,我在五米之外就知道了。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我伯母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应该与沐浴露、洗手液有关,那些东西为了挣钱,现在总是越来越多地加进香料。我虽然不喜欢这种通俗的气味,不过要看在什么人身上,现在它们从我伯母那儿向我涌来,至少我没有反感。
接着我感到耳朵痒痒的,她因为压低了声音,便使话语有了一股音乐般的舒缓,流进我耳朵,又通往四肢,让我很想愉快地手舞足蹈。
刚开始我注意力的确都集中在鼻子与耳朵上了,感官上的享受吞没了我。
“你也要多加小心啊,”她重新回到座位上,显得有些语重心长。“要多吃西瓜、葡萄、番茄以及那些贝壳类的动物,这些东西富含番茄红素,能促进精子的产生。另外,也不要去洗桑拿,桑拿室温度太高,造成死精太多,也会导致不育。”
我仰起头她看,我相信就是聆听领导关于加薪的指示我都不会有这么专注的表情。
“精索静脉曲张?”我没听懂她的话。
我伯母笑了,她的笑容一看就是医生式的,从容不迫中又渗杂着没法跟你说清的骄傲感。“精索!精神的精,索道的索。”
“精索静脉曲张。”我非常吃力地把这个医学名词重复了一遍,在此之前我的确从未听说过这个词,最多知道后四个字。静脉曲张,好像会使血管弯曲变形,我曾看到娥眉的一些老人,对了,比如我奶奶,她的小腿上青色的血管像蚯蚓一样蜷成一团,弯来弯去,并且惊乍地往外鼓。而“精索”这两个字,它所指的,一定跟男人生殖器有关了。
我的伯父有毛病,他没有生育能力?
“治也是能治的,不过,你伯父他不想彻底治愈,他都威胁我了,说如果想生孩子让我快去找别人结婚。凯歌,你能不能劝劝他?”
我根本顾不得回答她,我得赶快把下面的问题端出来,这是至关重要的啊。我说:“这病是什么时候得上的?”
我伯母摊摊手,“他精索静脉瓣膜先天性缺陷,他说二十多岁时阴囊就时常胀痛,却不敢说出来。你看看憨不憨?后来还是痛,实在受不了时才到医院开点中药,一不疼,就搁一边了,这么断断续续的,什么病能治得好?我都给他开过七八年的药了,当初如果听我的话,动个手术,也许早好了。可是,他就是不肯。你劝劝他吧。我可是想有个孩子,他那么聪明,我这么漂亮,这孩子绝对好品种。”
我听到胸腔深处传来咚咚咚响声,像是谁在里头,正用上吃奶的劲把一面大鼓拼命擂动,震得我四肢发软,整个人都坐不住了。我伯母问:“怎么了凯歌?脸色这么苍白。”
我看了她一眼。真的得谢谢这个女人,她至少帮我们把一个隐藏了二十年的往事撩开了最费解的一幕。我的妹妹许盼望,她不是许喜鹊的女儿,她是我父亲许鹦鹉的女儿。我的天!连古人都知道百折不挠地拦轿子递黄状以求伸冤,两个当事人,一个钢一样硬着,一个面条般软着,不约而同都一退千里甘心承受。我能说什么呢?我叹了一口气。
我伯母充满关怀地过来,她把手伸向我的裤门。她说:“你不会也跟你伯父一样有这病吧?我来查查。”
我垂下眼睑看着她那只珠宝般剔透的手抵达我的裤子,揪住了拉链,吱地往下抽去。米黄色的卡宾牌便装裤像只熟透的石榴,刹时绽开了,露出枣红色的三角短裤。那里鼓鼓囊囊的,富有质感。我伯母的手很镇静地转动一下,就要伸过去――我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差点把整个茶几撞翻。这太荒唐了,我已经导致五个以上的女孩去医院痛苦地做过人流了啊。我侧身望向书房的门,谢天谢地,那门还安稳地关着,我伯父正继续着自己的读书享受。我把裤门关好,脸热乎乎的,估计都红了,这倒是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我弄得跟处男似的,纯洁得虚假。反应过度了吗?不会,我心里很清楚,这样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我都庆幸自己能够在那个关键时刻清醒过来。
我用生硬的口气说:“我没病!”
我伯母愣一下,终于想起这不是在医院,她现在的身份也不是医生。她也笑了,双掌重重地一拍,说:“唉,我给人看病都看上瘾了。”能这样解围,说明她还不失机灵。我连忙也跟着笑,我想我也踊跃加入进去,双方都努力,这场尴尬也就加速过去了。
这时我伯母看看表,走到书房前,拉开门,她说:“老许,我看该走了。你说好不好?”
不知道我伯父在书房究竟有没听到我和伯母刚才的对话,他脸有些僵硬,从书房里出来,简直比从墓地回来还郁郁寡欢。我都弄不清此时该对他添几分同情还是加几多恼怒。看不起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伯母已经迎上去,喜滋滋地帮他整整领带捋捋头发,好像他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薄胎瓷器。我突然间冒出一个与衣服有关的联想:设计再蹩脚的服装,最终都有人买去,穿在身上,满心喜欢,甚至不无炫耀。
去国际饭店还是打的走。我伯母一点意见都没有,三个人中还是她最兴奋,眉宇间有无数彩绸蹁跹起舞。车到国际饭店,也是我伯母先下车。她的家人已经先来了,一群人站在大门口,围着一圈,高亢地交谈着。我伯母就像鸟儿一样向他们奔去,脸上艳若桃花。
我跨出车,返身一看我伯父还坐在车内不动。他已经付过车费了,但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反复上下在这个口袋按按那个口袋搜搜。
我问他:“找什么?”
他马上就停了手,望向我伯母那一群人,还是坐着不动。出租车司机津津有味地回头盯着他,还在进行一番饶有意味的揣测。我于是伸出手,抓住我伯父的胳膊,把他拉出来。他需要这一拉的,所谓找东西,其实只是内心慌乱的点滴泄露。这么大的一个生活转折点,这个笨蛋自己根本无力走出来。
站在大门口那一群人像遭遇磁石的铁沙子一样,全都向这边涌过来,把我伯父团团包围,簇拥着他往里头走去。我想好吧,没我什么事了,我可以走了。但走几步,又回头进去了。差点忘了,我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没解决哩。我伯父他还真忙,这个敬酒那个打招呼,被我伯母拖得团团转。我看他脸都失色了。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局面,我相信他打死都不愿有这个婚礼。找了一个相对清闲的空隙,我悄声问道:“你听说我爸在北京开百货商场吗?”
他像被烫了一下,猛地往旁一跳。没有没有!他说。
我说:“你见过他吗?”
没有没有。
“他找过你吗?”
没有没有。
我每问一句他的身子都跟着紧一下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