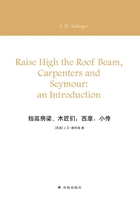村长高兴极了,又是恭维:“还是你老哥有办法!”又是敬酒、敬烟,爷爷一律不受,辞了众人,带着苏璞回家了。可那支古老的歌曲一直在苏璞的耳朵边回响:一辈走了一辈青,这才是轮回……
十一
回到家,爷爷也不做声,他是怪自己,怪自己生的儿子不多,人家敢欺负他的孙女儿。他气呼呼地要打电话给爸爸,让爸爸找人回来修理伯村长,妈妈拦住了,说:“那个病秧子能打架啊?您是不是要他去送命啊?他那条瘦命,人家还不想要呢!”
爷爷一口气憋在心里,极不舒服,就埋头不做声,不说话。
红薯收了,田野静下来了,霜降了,就染红了整座整座的山头,红的、黄的、橙的……那颜色五彩斑斓,一蓬一蓬,一丛一丛,热烈绚烂,那深山峡谷,更是美得醉人。那是大地积聚了所有的力量,所有的色彩,要在这个季节喷薄而出。
可爷爷不愿意休息,先是犁地、耕田,把收过庄稼的田地犁一遍,让土壤翻过来晒着,又给每一块田地挑足土肥,把肥料晒干,撒在地里,又细细地耙一遍。霜降过后,就要种油菜和麦子,他要把底肥施得足足的。
爷爷在山下劳作时,遇到了回家过双休的晓荷,他喊她上来陪苏璞。
“听你爷爷讲了你的遭遇,你可够倒霉的!”寒暄一阵后,晓荷问,“你就没想调个地方?这地方根本就不是年轻人待的……不过,镇上也不行,同样的工作,镇上比县城一个月少好几百块的工资呢!”
苏璞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山下一串急躁地喊声:“快来人啊!快来人啊!苏老爹吐血了!”
苏璞跑下山去,爷爷趴在地上,不知还有没有气,围观的人都不敢动。苏璞跑过去把爷爷扶起来,爷爷血流满脸,乌红的鲜血已经在脸上结了痂,可伤口暴着,还在丝丝往外渗着血。这么冷的天,爷爷栽倒在地上,他的身体已经发凉了,苏璞握着他的手指,冰冷得像一块生铁,连弯曲都不能。
可爷爷还没死,他睁开了眼睛,微弱地动了一下嘴唇,嘴里很干,两片嘴唇像被粘住了一样,无力地张开,又缓缓地闭上——没死也去了半条命。
“快拿水来!快拿水来!”晓荷急得大叫。
水来了,苏璞送到爷爷嘴边,可他不知道张嘴。他浑浊的老眼里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只是茫然地张着。苏璞从来没见过硬朗的爷爷这副无助的样子。
爷爷在半山坡耙地,准备把地耙最后一遍,然后撒菜籽。可耕牛不听话,爷爷气不过,拿鞭子抽了它几下,那牛也不服,暴跳起来,拖着耙就往前奔。爷爷气喘吁吁地追上去,又用拐杖抽了它几下,气接不上来,人一用力,喷了一口血,就栽倒在地上了。
爷爷老了!尽管爷爷不同意、不愿意,可他还是老了!苏璞心酸地想。
“快去卫生院吧!”三佬爹来了,他把爷爷常坐的躺椅扛下来了。他想把爷爷扶上躺椅,好抬,可爷爷已经不知道迈步子了,两条腿无力地在地上拖。苏璞心里生出巨大的恐惧来,从来没有过的绝望般的恐惧完全占据了她的心。
爷爷被抬上了躺椅,高大的他窝在躺椅里,只那么一点点,像一个瘦小的孩子,他的一双脚,穿着弟弟的旧球鞋,掉在下面甩啊甩。
走了十五里山路,爷爷被抬到镇上的卫生院。嘴唇上磕破的伤口很小,已经没有流血了。医生吊了两瓶盐水,他缓过劲来。他醒了,就要抽烟,要回家了。医生不让,说吐血的原因还没查出来。
拍了两个片子,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果然,爷爷的肺也有问题:肺癌晚期。
爸爸回来了,亲戚朋友都来了,弟弟也来了。弟弟在医院里大发雷霆,埋怨妈妈没把爷爷看好,为什么那么冷的天不在家休息,还非要不停地做事!如果不是不停地做事,爷爷怎么会累?如果不是太累,硬朗的爷爷怎么会突然得上肺癌的?如果不是怄气,怎么会吐血,倒在地上没人知道,过了好久才被人发现?
爷爷不管他,要回家,他说:“伢呢,人活一百岁也是要走那条路的啊!”
苏璞不让,她哭起来,她说:“是我没照顾好爷爷!怪我!怪我!都怪我!”
苏璞筹了钱,把爷爷在医院里安顿下来。临近考试了,她也得回学校上课。白天上课,放学后就踩自行车走十几里路来镇上照顾爷爷,医院没陪床,她和妈妈就轮流住在晓荷的寝室里。
在爷爷的病床边,苏璞收到了叔采茵的来信,她竟然没有通过县教育局的面试,这一切,只让她觉得荒谬和可笑。不过也好,她正好可以回到男友身边。随后的几天,她又收到了采茵寄来的汇款单,整整一千二百元,苏璞想了想,收下了。
岑晓荷借了五百块给她,她也接了。“我们这边,工资还是要高一点的。”晓荷说。
“三鼻子”和施校长都来医院看爷爷,临走时施印还给了苏璞三百元,苏璞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爷爷看病要钱,没什么尊严比人的生命还重要。
苏璞和爸爸开着三轮车,把爷爷种的土豆和红薯拖到县城里去卖。苏璞抚摸着滚圆的土豆,多好的土豆啊,可这么好的土豆也不过卖了一千多块钱。
苏璞的眼前浮现出爷爷愁苦的双眼……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得这么穷苦?为什么?为什么?她问自己,没有人回答。
妈妈接替苏璞的时候,她到弟弟的学校转了转,发现弟弟正沉着一张脸在挨老师的批评。一向聪明好学的弟弟怎么会挨老师的批评?
爷爷还是回家了,弟弟也不补课了,整个寒假都在家陪着爷爷。
这个春节,她和弟弟整天陪着爷爷。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陪着爷爷在田地里转悠,爷爷还坚持自己扛着锄头。油菜和小麦都种下去了,妈妈抽空种的,弟弟拿着弹弓打偷吃的鸟儿。爷爷看见麦苗从松软而温暖的土地里钻出来,阳光穿过山梁、穿过田埂、穿过田埂上的白桦树,照在青秀的麦苗上,照在爷爷花白的胡茬上,他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天气阴冷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烤火,看着太平岭对面的山野和林子,看着白桦林脱去金灿灿的衣裳,卸下最后一片金黄的妆扮,亭亭玉立地挺立在山冈上。多美的白桦林啊。苏璞想。
最后,雪落下来了,落在房子上、树木上、山林上、田野上,一切都白了。喜鹊喳喳叫着,在门前的雪地上蹦跳着觅食。
弟弟一大早起来,给爷爷念小学时学过的课文:下了一场雪,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弟弟故意把“也”字念得很重。
弟弟又念: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爷爷高兴地笑了,他看着苏璞和弟弟在门口打了一场雪仗,最后,爷爷把爸爸妈妈和奶奶托付给她和弟弟。弟弟伏在爷爷腿上哭了。
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爷爷走了。肺属木,爷爷的肺没能像春天的山野那样苏醒过来。送走爷爷没花多少钱,因为爷爷说了“一切从简”,爷爷的挽联是苏璞写的,俊逸的毛笔字在山野里飘啊飘啊……
第二年五月的时候,各种粉的、紫的野花开遍了整个山野,山上、水塘边、田埂上,到处都是,开得蓬蓬勃勃,绚丽烂漫。农忙又开始了,苏璞和弟弟在田里插秧,可是已经没有爷爷挑秧打秧了。苏璞看见爷爷砍过的那丛野蔷薇,又发了芽,还开了花,可因为爷爷砍得太深,伤了根,它长得太孱弱了,枝叶瘦瘦的,花也惨白惨白的,不知它还能不能熬得过今年的酷暑严冬。
苏璞去找施印了,在一个施印没回家的周末。晓荷跟她讲过“三鼻子”侄女的调动,那个女孩只跟施印见过几次面,知道他能帮上忙,就托“三鼻子”联系上他,求他帮忙。施印也热心,就天天晚上带着她往城里跑,跑了一个暑假,竟然就办成了。
有那么容易?就那么容易?苏璞半信半疑。
“你可以试试嘛!”晓荷说,“反正我是准备去试试的!”
苏璞还有些犹豫,晓荷又说:“唉,我反正是看透了,人生啊,爱情啊,就那么回事,只有钱才是真的,钱才能抓在手上。——花时间花精力谈恋爱,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也许还是一场空,还不如……”
苏璞还有些犹豫,她又说:“一个女人的漂亮,是把双刃剑。如果你不想把它变成前进路上的武器,那么它就会成为你的包袱。”
这句话意味深长,苏璞记住了。
那天施印还没有起床,他听见是苏璞的声音,就说,等一下。然后他换了件衣服出来了,苏璞看见他穿着一件淡绿色的T恤和一条黑色的沙滩裤。
苏璞愣了一下,有点儿眼熟,脑袋晃了晃,想起来了,是那个……偷看她洗澡的人。
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