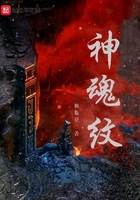上校失约了,他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整支考古队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凉亭下,等了他大概有一个小时了。哈拉夫坐在长木桌旁,八盏黄色吊灯的其中一盏正照在他的头顶上。年轻厨师在鱼旁边配了蔬菜饭以及从幼发拉底河边采来的莴笋做成的沙拉。但他还是在等待客人的到来才开始做鱼。
“我们最好还是开动吧。”埃斯拉打破了僵局,“看来上校是不会来了。他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
“不来也该打个电话啊!”凯末尔愤怒地抱怨道,“这么多人在等他……”
“我想上校今天应该忙坏了。”蒂莫西替他辩解道,“我们今天碰到他的时候他好像是准备去什么地方。”
蒂莫西的话还是没能让凯末尔冷静下来。
“好吧,但他还是可以打个电话啊。”接着,当他看到艾丽芙出现在视野里之后,他加重了语气,像是故意要说给她听,“看起来这段时间我们都习惯让别人等待了!”
餐桌上的气氛顿时尴尬了起来。艾丽芙一行回来之后,凯末尔就一直埋怨她,并对她大声呵责,但年轻女人迅速做出了反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没资格对我的生活说三道四。”现在,凯末尔似乎又想吵架了。艾丽芙意识到之后,便假装没听见她男朋友的话,径直往厨房走去,希望能帮哈拉夫的忙。
埃斯拉是穆拉特的教授,她第一次建议他加入考古队的时候,穆拉特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余下的一整天仿佛都如置天堂。但他越想就越觉得自己可能并不够格。他想象着考古队里的其他人应该都比他聪明、比他有经验,更别提他们之中还有两名外国人了。所以基本上他自认为这件事是告吹了。但过去的两周使这个聪明的男孩子意识到人无完人。他看到他所敬重的包括埃斯拉在内的所有人都会犯错,有时候犯的错甚至在他看来是无比愚蠢的。当在考古队工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两点:首先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其次就是努力使自己适应与团队一起生活、工作。他在考古队中发现后者才是最为困难的部分。每个人都想尽力做好,但一旦开始生活在一起,完全不同的个性就产生碰撞了,即使是在很琐碎的小事上都会爆发激烈的冲突,比如晚餐吃什么又或是谁先去洗澡。既然争吵是无法避免的,大家就要记住别让这些争吵伤害任何人的感情。除了以上这些,穆拉特还发现考古队的生活比他想象中的精彩多了。实际上,他何止兴奋,他已经完全离不开考古队了。毕竟在这里触摸、感受的土壤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味道,那些苍白但永恒的色彩,以及那追溯至几千年前波动起伏的历史线不可避免地指引着你的心灵,你整个身体充斥着无法追溯的好奇心。即使你很想摆脱这些感受,你也完全做不到;所以最终,你会用尽一生的时间从一个遗址到另一个遗址苦苦找寻那些细小而残缺的线索,这些线索将会带你到埋葬真相的诸世纪下的某地。
蒂莫西深沉的声音打破了餐桌边这令人讨厌的沉默:“我们喝点酒好吗?”
“我想今晚我们还是别喝酒了吧。”埃斯拉脸上的表情是在期盼其他人能够理解她的提议,“明天是工作日,我可不希望看到谁带着酒意工作。”
“喝一小杯不碍事的。”看来泰奥曼对蒂莫西的提议没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所谓的‘一小杯’。”埃斯拉继续说道,“我真的觉得我们今晚不能喝酒。”
在其他时候泰奥曼可能都会好说歹说向这位考古队大神求求情以获得准许,但看到她今晚心情如此低落,他也不想再在此刻与埃斯拉理论什么了。
“好吧,我们下次再喝。”他就像一个虽屈服于命运却仍旧不屈不挠的男人,“把面包递给我切一片。”
艾丽芙手拿一杯柠檬汁从厨房走了出来,往桌边走来,厨房里飘来阵阵煎鱼的香味。泰奥曼正切着面包片,继续发着牢骚:“鱼还没好吗?”
“耐心点吧。”年轻女人对他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才刚下锅呢。”
凯末尔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年轻女人。艾丽芙却并没有注意到,只是随意把杯子放在桌上。
“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件事。”埃斯拉有些生气,“凯末尔这个傻瓜现在很沮丧。我希望他猜错了,艾丽芙对蒂莫西并不感兴趣。”
这些想法在她脑海里浮现的时候,她听到有一辆车在逐渐开近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往路上望去,但只有一道车前灯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那会是上校的吉普车吗?”蒂莫西猜想道。
吉普车在离凉亭右边约2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上校首先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一位警官和两名卫兵。
“哦,天啊!”泰奥曼有些夸张了,“他们是四个人!都要来吃晚餐。”
埃斯拉没好气地望了一眼泰奥曼,站起身来往吉普车走去。她脸上的表情很严肃,眼里闪过些许痛苦的神情。
“对不起,我迟到了。”上校说道。他嘴上道歉,动作却像一个刚刚获得胜利的聪明孩子那般兴奋。“但我不想空手而来。”他继续打趣道,“吉普车上有带给你的东西。”
埃斯拉一脸错愕。她完全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快过来。”他甩了甩手,“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些对你们很重要的镌刻师所做的泥板,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是说帕塔萨那?”埃斯拉仍旧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是的,他的泥板。更确切地说,在我看来是他的泥板。我们还找到了一只纯金酒杯、一个银鹿雕像、一座铜女人像和一根项链。”
这激起了埃斯拉的好奇心,她跟着上校一起往吉普车走去。“你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她问道。
“在瘸子梅米利的葡萄庄园里。”上校解释道。此时他们刚巧走到吉普车敞开的中门边。“看,在这里。”他指了指吉普车底板上放着的东西。
首先抓住埃斯拉眼球的是那座女人雕像,然后才是鹿、酒杯和项链。这些东西旁边放着两块泥板,其中一块已经碎了。她先拿起其中一块完好无损的泥板,借着车里的微光仔细检查了起来。确实像是帕塔萨那的泥板--18厘米×27厘米大小的土制泥板,正反面各有六行文字,正面写的是泥板内容,而背面则是泥板的摘要。当她望向泥板底部看到印章的时候她知道上校没弄错--这些就是帕塔萨那的泥板。
“我没明白!他们是什么时候偷了这些泥板的?”
“昨晚。”上校对自己给了埃斯拉一个惊喜尤为自豪,“等我一点一点地告诉你。我只是带来让你看看,但现在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运回警局去,它们现在都是证据了。”
“但我们要翻译碑上的内容。”埃斯拉紧张地喃喃道,“其他东西我们照相就可以了,但是泥板必须要先拓下来。”
“要弄多久?”
“最多一天。”
“好吧,但要确保不能超过一天,因为检察官需要这些证据。”
“好的。”埃斯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天之内我会亲自把东西给你送回去。”
蒂莫西、穆拉特和泰奥曼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三个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埃斯拉手上的泥板。
“帕塔萨那的泥板。”埃斯拉很气愤,“另外四件重大发现也是昨晚从我们眼皮底下被偷走的。”
“把东西给你们放到哪里?”上校问道。考古学家们正慌乱地看着这些东西。
“噢,不用了,我们自己来吧。”埃斯拉说道。上校不知道她这么说是怕麻烦卫兵们还是害怕卫兵们会把这些考古发现都弄坏了,但他并没有坚持。穆拉特和泰奥曼已经把泥板接了过来。穆拉特的眼睛注意到车里的一个麻袋。
“这个袋子也要拿走吗?”
“那不是你们需要的。”上校说道,“那是一袋大麻。”
“大麻?”埃斯拉惊奇地问道。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瘸子的庄园里发现的。”
十分钟后,上校坐上餐桌,开始和大家讲述发生的事情。泰奥曼的担心完全是徒劳,那位警官和两名卫兵并没有留下来吃晚餐。餐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担心晚餐不能及时进行的哈拉夫和已经饿得饥肠辘辘的泰奥曼--都在仔细聆听上校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刚开始审问舍穆兹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是在逃跑,只是和往常一样开车到处溜溜而已。抓住他的伊赫桑警官证实了他的说法,从他的装备以及行为上完全看不出他是在逃亡。我向他问起哈吉·赛塔尔,当我一说到名字的时候,他长满麻子的脸就毫无血色了。”
“我没杀他。”他说道。
“你杀了他。”我说道,“我有目击证人。”
“那他们是在说谎!”我说道,“别想抵赖了,我们知道就是你杀了哈吉·赛塔尔。”
“噢,上校,求求你了,别这样。”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我跟前跪了下来。其中一名卫兵还以为他要袭击我,便用来复枪托往舍穆兹头部砸过去。舍穆兹倒在地上,还有一点儿抽搐,但仍在努力跪起来。“随你们想干什么,但别冤枉我!”他不顾前额流下来的鲜血向我们乞求着。但他已经不敢再向我靠近了。
“好吧,你昨晚在哪里?”
“在家。”他一脸无辜。
“我明白了。”我说道,“显然你还不准备和我们说实话。”
“我发誓我说的都是事实,长官。我对神灵起誓我说的都是真话。”
“别发誓了!”我厉声吼道,“你当着我的面撒谎。我们已经和你哥哥谈过了,是他告诉我们一直到早上去祈祷的时候你都不知所终。”
他的脸色阴沉了一会儿,但随后便又振作起来继续解释。
“长官,我去钓鱼了。”他声音颤抖,“前任的上校禁止这里的人钓鱼,所以我没告诉你。”
“这种话你用来骗谁啊?”我径直向他走去。
舍穆兹不禁想往后跪几步,但站在他旁边的卫兵已经把来复枪架在他左侧了。
“别动,朋友!”
“他瘸了的左腿明显很痛。我弯下身平静地说道:‘我最后一次警告你。我们知道你没有去钓鱼。没人能在去钓鱼之后在日出前就回来。今天早上你在去祈祷完之后就跑回家了,那时候天都还没亮。你也没有带什么鱼回来啊。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的,你可不能等着幼发拉底河里的鱼自己游到你的网子里;你在等着哈吉·赛塔尔好把他从尖塔上推下来。”
“舍穆兹微微抬起头,先是绝望地望了一眼站在身旁的两名卫兵,接着看着我。
“好吧,长官。”他说道,”我说实话,但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昨晚都没到过清真寺附近。我出城去了。’
“看吧,又来了,继续编。”我很生气,“把子弹带递给我。”
“求你了长官,别。”他跪在那里瑟瑟发抖,“我发誓我这次说的真的是实话。我们昨晚去了黑墓。”
“这次换我惊讶了。”
“你们去了黑墓?”
“是的,我们去了黑墓。我们去寻宝,你应该猜得到。”
“又在说谎了……”
“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我以我全家人的性命起誓。”
“还有谁和你一起吗?”
“舍穆兹沉默了。”
“看吧。’我用手指着他的脸,‘如果你不能证明当时你在黑墓,我就会以谋杀哈吉·赛塔尔的罪名逮捕你。”
“他眼里满是恐惧,就像一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胡狼。最终,他坦白道:‘瘸子梅米利的儿子贝克尔和我在一起。”
“你们在遗址发现了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在梅米利的葡萄庄园发现的。”他的声音听来很疲倦。
“我们会去证实的。那你们挖宝的时候遗址看守人老赛罗哪里去了?”
“老赛罗的儿媳妇给他生了一个孙子,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想去看看。所以梅米利告诉他:‘进村去吧,赛罗,我会叫我儿子贝克尔帮你看守遗址的,朋友不应该就是这样吗?’赛罗是个纯真的人,他信任梅米利,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真的进村去了。他和这件事没任何关系。”
“舍穆兹供认之后,我们在车库把梅米利的儿子贝克尔抓了起来。我们仔细地搜查了葡萄庄园,把他供认的赃物和一麻袋大麻充公了。起初贝克尔拒不认罪,但后来我们没费多大劲就使他承认舍穆兹所讲是事实了。”
整支考古队都在专心听着上校的故事,以至于现在上校讲完了他们还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哈拉夫首先打开了话匣子。
“我有种直觉,赛罗叔叔应该有问题。他早上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发现挖掘有什么问题了,但当时我们都已经开始了。之后他之所以不说肯定是因为害怕。”
“我们应该开除他。”凯末尔说道,“我们是雇他来守护遗址的,他却把遗址交给了盗贼。”
“更为重要的是,今晚遗址可能都不安全了。”埃斯拉紧张地说道,“可能赛罗叔叔因害怕而逃走了也说不定。”
“他没离开。”上校肯定地说道,“我们把赛罗带回去审问了。之后便派了两名值班人员去守卫遗址。”
埃斯拉感激地看了看上校。
“谢谢。我们明天再来讨论看守人的问题。”她说道。但她心里还是在想着审讯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舍穆兹没有杀害哈吉·赛塔尔,是吗?”
“看起来是的。”上校答道。上校到来以后所带的那种愉快的表情似乎转瞬消失了。
“我想你弄错了。”凯末尔反驳道,“你所说的事情并不能证明舍穆兹没有杀害哈吉·赛塔尔。他可以在把盗窃来的东西藏到庄园以后再去杀害哈吉·赛塔尔。”
“不大可能。”上校冷静地说道,“明天一支技术小组会从加齐安泰普过来,他们会来采集指纹。只有那个时候一些东西才能确定。”
“既然这样,我们就抓紧时间继续吃饭了。”泰奥曼都快饿昏了,“毕竟,饿着肚子可帮不上什么忙。”
泥板七
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祖父弥谈努瓦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派出去寻找他的信使们全都空手而归。我们放弃寻找他的希望之后,父亲阿拉拉斯就开始把精力放在我身上了。我也不能说他对祖父的失踪感到很高兴,但他的确想从祖父失踪这件事情中获利。他开始花大量时间与我待在宫殿外。他不赞成我写诗,而是迫使我学写官方碑文。我按父亲说的做了,但我还是在私底下偷偷写诗。这样很怪,但我也从未对父亲发过脾气;相反,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能理解他了。
弥谈努瓦以前称父亲是国王的狗腿。但在我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政府。
那一年,我们的国王在丰收季病了。开始只是腿部肌肉剧烈疼痛,但仅仅过了一周之后国王就去世了。大家在太阳神特舒卜、他的妻子太阳女神希帕特、儿子沙努马以及女神库帕芭面前摆满了贡品,虔心祈祷。河中央最好的算命者来向我们传授应该怎样祛除国王头上的不祥的阴云。
算命者看着从一只被屠宰的羊身上取出的肝脏,研究着肝最厚的部位是在顶部还是在尾端,最终还是无望地摇摇头。
算命者在幼发拉底河下流的一个平原上空放飞了一公一母两只雄鹰。但两只鹰并没有飞往同一个方向,而是各自向相反的方向飞去。
算命者又在池塘里放生了两只鳗鱼,但鳗鱼也同样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游走,这也告诉我们国王将不久于人世了。
算命者的预言是对的,阿斯塔鲁斯国王在七天后就离世了,去到了天国。接下来举行了一场长达十四天的礼,和前国王卡玛纳斯一样。他的尸体被火化,火苗随风飞舞,通往空中。他的骨灰被安置在一个陶罐里。
阿斯塔鲁斯国王的王位被我们的新主人、神灵的新宠--皮斯里斯所取代了。皮斯里斯登基时,和阿斯塔鲁斯刚登基时一样年轻。然而,他和阿斯塔鲁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阿斯塔鲁斯是个缺乏自信的国王,这也是他不能脱离议会掌控的原因之一。皮斯里斯就完全相反了,他野心勃勃、冷血残酷,也极其自信。在他掌权后的第三个月就完全脱离了议会。他开始不理议会的决议,也拒绝实施他们所颁发的法令。我的父亲试图反对他的统治,但国王公然威胁他,说道:“要不然你站在我这一边支持我,要不然我就终止镌刻师的世袭制度,你们家已经占着这个职位很多代了。”我父亲深知国王这种做法的错误,但他却没有勇气当面向他提出来。也不能说他是一个懦夫,只能说他原本就无法反抗皮斯里斯的统治。为了保护国王的权益,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提出对付外国统治者甚至是议会尊长的复杂阴谋计划,但他不能对皮斯里斯这么做。
皮斯里斯脑子里有着更为危险的想法,更别说还计划着自己独裁统治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做大帝国时期的希泰国王。他偷偷地进行着自己对亚述帝国的侵略计划,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这小小的国度怎么能和那样的大帝国抗衡。我父亲也曾婉转地警告过国王,时常恳求他放弃这样危险的计划。但皮斯里斯太年轻、愚昧并且过分野心勃勃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完全没有把我父亲的警告听进去。最终父亲向国王低了头,开始与他和谐共处,这也就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毕竟,皮斯里斯是国王,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表。公然反对他会导致神灵的震怒,带来更多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