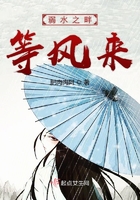溪月跑了几步,有些吃力,怕伤到肚里的孩子,只得放慢了脚步,心中仍在砰砰乱跳。这府里的人都怎么了,平日里都是道貌岸然,却藏了这么多秘密。远远看到齐王宇文松和看守剑庐的家人老陶往聆雨轩的方向来,溪月心中更是心惊。
他俩是要去剑庐还是要到聆雨轩?怎么办?通知不通知耳房里那两人?溪月心中矛盾不已。按理说,这事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可那两人的私情若是被撞破,府中必有一翻风波。男子也就算了,女子必然逃不了凄惨的下场。朝中的风气虽然开放,偷情却仍是为人所不耻的败德之行。
溪月焦急万分,正在踌躇,宇文松和老陶走得越来越近。溪月心生一计,故意迎着宇文松走过去。“儿媳拜见父王。”她主动和公公打招呼。宇文松点点头,打量了她一眼:“你行动不便,要多注意,不要在园子里乱走。”溪月嗯了一声,见宇文松和老陶正要转身往聆雨轩去,忙假装体力不支要昏倒。
“少夫人——王爷,少夫人要昏倒了。”老陶无意中看了溪月一眼,见她摇摇欲坠,忙告诉宇文松。宇文松回头一看,溪月扶着腰,一脸痛苦的神色,忙走过去扶着她。“你这孩子,我说什么来着,叫你不要乱跑,果然应验了。老陶,快去通知金管家和二公子,让他们请大夫。”老陶依言而去。
溪月被送回竹雨斋时,宇文长风已经回府。大夫替溪月诊脉之后,说她腹中的孩子并无大碍,开了安胎的方子给她,让她好生休养。宇文长风这才松了口气,派人去回报给宇文松,让他不必担心。
溪月躺在床上,宇文长风有些心疼,又不得不责备她:“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让你不要乱走吗?”溪月一肚子委屈,又不好和他明说,只得撅着嘴不语。宇文长风以为自己语气重了,惹她不高兴,叹了口气。溪月坐起来,拍了下他的肩,没好气道:“你都不知道今天是出了什么事,就这样数落我。好了,我也懒得告诉你。你们家的人啊,一个赛一个的古怪。”“我们家的人难道不是你的家人?”宇文长风回了一句。
溪月见他皱眉,忍不住道:“你大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大哥?他……是个好人。怎么了,你想说什么?”宇文长风狐疑的看着妻子古怪的神情。溪月想了想,始终觉得这事难以启齿,侧着脑袋低语道:“不告诉你。”“不告诉我也行。不告诉我的结果就是,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出门,只能在竹雨斋里呆着,直到孩子平安降生。”宇文长风故意激她。
溪月没办法,只得搂着他的脖子,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宇文长风先是一脸惊讶,渐渐的有些笑意:“这么说,要不是你急中生智,替他们掩护过去,今天非东窗事发不可。”“我看就算不东窗事发,也是危险了。你说,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啊?要是给大嫂知道,她不活活气死才怪。”溪月愤愤不平的说。
看着她歪着脑袋不满的神情,宇文长风淡淡笑道:“大嫂没嫁进来之前,茜雪就已经是大哥房里的丫头,若不是碍于大嫂,早就给她侍妾的名分了,而不是现在这样。这事你装不知道吧,大哥有他的难处。”“啊?”溪月揪着他的耳朵,气道:“原来你早就知道了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房里的丫头……哼,我嫁进来之前,你和瑞雪小蝶是不是也……你最好别给我知道,不然我……”
宇文长风揉揉耳朵,故意道:“你怎样?”“我……我打你的孩子,我天天打他。”溪月笑道,轻抚着腹部。“我跟小蝶、瑞雪可没什么,你别瞎猜。”宇文长风笑着把手按在溪月的手上。
“惠芝的叔叔谢安想纳妾,怕他夫人不同意,找了惠芝的几个哥哥当说客。惠芝的三哥说,女子当如《诗经》里所说,以不妒为美德。结果谢安夫人说,《诗经》是周公所编,男人当然向着男人,要是周婆所编,一定不会这么包庇男人。这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溪月笑着和宇文长风开玩笑。
宇文长风笑道:“这件事一听就是谢氏子弟拿谢安来取笑,《诗经》何曾是周公所编?谢安的刘氏夫人是名士刘惔之妹,饱读诗书,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溪月冷哼一声:“我觉得刘夫人说的很对。今天大哥这件事,就算我不说出去,你瞧着吧,大嫂迟早也会知道。”“别人我不管,你可不要说。”宇文长风嘱咐了一句。溪月知道他的顾虑,点了点头,轻轻靠在他肩上。
长公主回府后,听说溪月差点在花园里昏倒的事之后,心里非常担心,派了两名仆妇来问话,确认溪月和胎儿都没事之后才放心。
次日午膳时,溪月再见到宇文啸风夫妇,忽然觉得有点别扭。表面上,他俩是那样恩爱,可私底下呢?男人趁着妻子不在府里,和婢女偷情。虽说他俩的关系时日已久,可真要让青鸾知道了,只怕以她的个性,未必能接受。溪月看了青鸾一眼,不知道该是同情她,还是担心茜雪的命运。
她又看了宇文啸风一眼,见他正替妻子布菜,俨然一副好丈夫的样子,心中不禁失笑。她对宇文啸风的印象不坏,一直觉得他是个憨厚的老实人。可自从闻知他在朝堂上斩杀河间王司马虢,又撞见昨日那不该撞见的一幕,对他的印象渐渐模糊起来。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叫人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