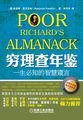一路上我们三人换着班儿开车,起先的兴奋劲儿被貌似没有尽头的高速公路,消耗殆尽。我手里握着方向盘,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什么,只是企盼着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唯一令我期待的是,琳达和杰森到底长什么模样,我想他们对我的模样也应该是有相同的期盼吧。
终于,在车灯的照耀下机场高速指示牌映入了眼帘,再有个两、三公里就进入迎宾大道了,也就是说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汉州机场了。
一行三人,从停车场里走出来,来到国际到港航站楼等待杰森和琳达的飞机降落。听秋玥说,杰森与琳达是在曼谷汇合的,在那儿游玩了几天散散心,然后一同来的这里。
汪有义社团那边的情况,在路上的时候,邸晓波已经对我和秋玥讲过了。他们社团的名义上是个茶园,就在东湖边上的茶村里。现在汪有义已被医院宣布为植物人,社团里的人当然明白,汪有义是永远不会醒来了,正在和他的家属商议何时停止对汪有义的维持。
当然,这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社团希望能早点让他入土为安,对他来说也是有个交代。在次界,带汪有义去参加考核的介绍人叫吴亚军,自从回来后一直在医院看护着汪有义,身体情况和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不管别人怎么劝,也不肯离开。社团索性也就由着他了,不过加派了人手,轮流照看他。
机场广播里传出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提示从曼谷到达汉州的航班即将到达。秋玥从包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他们名字的接机牌,我和邸晓波站在她的身后,在旅客出口开始等待了。
我伸着脖子努力在人群中寻找,虽然我不知他们俩的模样,但是对于他们的频场我还是相当地熟悉。
人群中的两个人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一高一矮。高的是一个头发偏褐色的小伙子,一脸淡淡的络腮胡,一双兴奋的目光在深陷的眼窝中,正向这边看过来。他马上用手拉了拉身边正在同样四处环顾的女孩,那女孩也朝我们这边望过来。
女孩是一头长长的金发披散在肩头,白皙的面庞上镶嵌着两个蓝宝石般的大眼睛,看到我们后,也兴奋地向这边招着手。一定是他们了——杰森和琳达。
秋玥和我,也向他们那边挥着手,身边的邸晓波高高挥舞着双臂示意他们赶快过来。等他们从出口出来,我们就马上迎了上去。
杰森张开双臂,直冲我就抱了过来,这家伙比我高了差不多两头,孔武有力的双臂紧紧箍住了我,连声说道:“Hello,Wan.Nicetoseeyouagain.It’sbeenalongtime.”
一旁的琳达和秋玥抱在了一起,两人也在忙不迭地互相问候着。
我有点儿发懵,我倒是能大概听懂杰森的意思,可是我英文说的是很差的,而且发音也不太准的。我磕磕巴巴地回道:“Hello,Jason.Iamverygladtoseeyouagain.YouhaveagoodtimeinBangkok?”
杰森回答道:“Yes,weplayverywell.”
说罢,他双手抱肩,上下打量着我。一旁已跟秋玥和邸晓波打完招呼的琳达,也同样张开胳膊,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和我亲热地贴着脸,就像好久不见的亲人一样热情。
琳达的个头和我就差不多了,她双手按着我的肩膀摇晃着,说道:“Meetyouatlast.Doyouhaveagoodtime.Wan.”
一旁的秋玥,表情复杂地看着我们。
我又磕磕巴巴地回道:“Hello,Linda.Iliveverygood,alsoverygladtoseeyouagain.”
我都不知道用的语法和单词对不对,也就更不知道他们俩到底能不能听明白了。
不过,看起来还不错,他们俩应该是听懂了。这时,我开始怀念在元界和次界的日子了,最起码我们之间的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呀。不像现在,得连说带猜的,真是麻烦。
好在秋玥和邸晓波的英文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行五人,边走边聊,其实我是边聊、边猜、边比划的,好不辛苦。逗得他们几个哈哈大笑,真是令我难堪,后悔没学好英文。看来我的英文水平也就停留在四级考试的成绩上了,其余就没什么卵用了,唉。
既然英文不行,那我就负责开车吧。大块头的杰森坐在副驾驶,其余的三人坐在后面。好在,这是七座的SUV,放我们五个人的行李,还是绰绰有余的。郁闷的是,他们说话语速太快,等我听到后再琢磨一下,然后组织好语句时,他们早就已经开始下一话题了,我只有在旁边傻笑的份了。
我看着后视镜中几个兴高采烈的人,大声问道:“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哇?已经这么晚了,得找个地方吃口饭,然后再找住的地方了。”
秋玥抄起手机,鼓捣了几下,说道:“看微信吧,位置都发给你了。吃饭和住酒店我都预订完了,你就按照上边的地址导航就行了,别打扰我们聊天,讨厌。”
无语,还是无语。旁边的杰森看出了我的无奈,拍了拍我的肩膀,耸了耸肩,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没办法,女人的样子。”
“哎呀,我的老兄,你不是还会几句中文嘛,那就别用英文和我聊了,用中文吧,行不?”我兴奋地说道。杰森摊开双手,看着我摇摇头,说道:“Youspeaktoofast,Idon’tunderstand.”
“得,那你还是和他们聊吧。”我向后面摆了摆手,又惹得他们哄堂大笑。
就这样,我们一路走着一路笑着,吃过了饭,入住了酒店。邸晓波和吴亚军取得联系后,定下了明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就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五人收拾好行装,就开车直接前往医院了。因为,吴亚军他们现在都在医院,还有汪有义,确切地说是汪有义的身体在医院。
肃穆的走廊、紧闭的病房、悲伤的家属、沉痛的同事正和两个白大褂的医生商议着什么。邸晓波正在与吴亚军交谈着,我们站在他的身后垂手而立,倾听着。
邸晓波轻声地问道:“就是今天吗?”
吴亚军点了点头,说道:“是,我们都已经和家属商量过了,家属也征求了医生的建议。医生也是倾向于结束。家属虽然已经同意了,但是心里的坎儿还是始终过不去。这不,主治医师正在和家属做最后的确认。”
我的心头一阵阵酸楚,心里明白,在次界汪有义被击中的那一刹那,他就已经不在了。现在躺在病床上的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身体而已,再无生气可言。
面对医生的家属们,还是发出了阵阵的悲恸之声,看来事情已经商定了。我们在吴亚军的引领下,对汪有义的家属说,我们与汪有义是业务上的朋友,特意过来看望的。汪有义的老父亲已是满头白发,他的肩膀抖动着拉住邸晓波的手,嘴里说着感谢的话。而我们能做的只是些安慰而已。
然后,我们依次进入了病房,汪有义的妻子一言不发地坐在床边,双手摩挲着汪有义的面庞,早已没有泪水的双眼,直勾勾地望着丈夫,空洞洞地眼神里是她无限的留恋。一个小女孩,大概四、五岁的模样,在不停地拍打爸爸的手,嘴里喃喃地说:“爸爸,起来,陪我玩儿。”
我眼睛瞬间溢满了泪水,我低下头擦了擦眼泪。秋玥和琳达也正极力地不哭出声音来。秋玥默默地拍了拍,这个悲伤女人的肩膀,女人回过一只手,紧紧地握住秋玥的手,脸颊贴在上面,干涸已久的泪水,无声地涌出了双眸。
琳达蹲下身子,抱住小女孩,亲了亲,然后将她的头揽在怀中,用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我看着眼前这个初次见面的男人,熟悉而又陌生。黝黑的面庞,头上梳着利落的板寸,一对浓眉下紧闭着的双眼。呼吸机的面罩已在脸上勒出深深的痕迹。在次界我们并肩战斗过,在这里却是初次见面,而且是最后一面。
古人那句“相逢何必曾相识”登时浮现眼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秦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掀起了心中的滔天巨浪。这是出离了愤怒的巨浪,正在对着乌云中肆虐的闪电咆哮着,希望有一天能够淹没那无边的乌云,拍散撕裂天空的闪电,还我一片碧水蓝天。
追悼会是在第三天举行的,举行完毕后,我们谢绝了家属们安排的白事宴席,与吴亚军互留了联系方式后,我们离开了。
开着车、沿着路、五个人、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