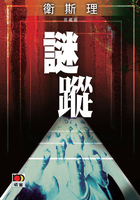据说,凡事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有些东西,只消一次就足以改变它的性质。比如说诗诗,她迈开了这第一步,开了这先例,那她就已经是那种类型的女人,她没有理由可以搪塞,没有理由可以为自己开脱,难道她会因为对孩子的爱选择出卖自己而变得高尚么?不!绝对不会,某些时候,为了别人做出牺牲可能要比为了自己更加自私。
诗诗拐进巷子,这条她走过许多次的巷子被积雪埋得很深,还没有任何东西在上面放肆过,流浪猫狗都不知踪影,或者都已经被冻死了。她倚着墙壁慢慢往里走。
有些东西的到来猝不及防。
突然间,疼痛袭击了她的腿,就像是有两个大钢锥死命地往里凿她的膝盖,那是一种骨头粉碎的疼痛感,碎片和血肉搅和在一起。诗诗之前也有过疼痛,但没有一次有这一次来得这么迅猛,这么强烈,她的大腿几乎没有知觉,整个站不住,膝盖一弯后,整个人倒在雪地里,她靠着墙壁艰难地爬起身子坐下,裤子上沾满了雪,一会儿后,她就感到屁股上刺骨的冷,但她无可奈何--她爬不起来,动弹不得。曾经的这个时候,她的两条腿受过多么严重的摧残,光着躺在寒冬的湖底,接着在风雪中跋涉了几天,她一直生活在郑叔家,虽然是个丫鬟,但是有哪个丫鬟有她过得那么好啊!郑叔从来没有拿她当佣人看待,一直提供着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给她成长,所以,突然有一天,将她置身在冰天雪地中的时候,那两条纤细的腿终于还是坏死了。现在我们再来追究原因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就像是马后炮,风凉话。确实有那么几次,她感到很疼,一晚上都咬着牙,大汗涔涔,她一直忍着,认为一切都不会有事,上帝会眷顾她,但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在她最痛苦和无助的时候,上帝似乎没有一次站在她的身边--他早就离弃她了,她是不知道还是一直在欺骗自己只有她自己清楚。
可怜的女人靠着墙壁喘着粗气,要是有人能拉她一把该多好,但这哪有可能呢?这是一条狭长的小巷,抬头只有一线天空,进口出口只容得下一个半人并排走,原本灰暗的世界,在这狭长的幽深里,完全蜕变成了黑暗,原本的灰暗倒成了诗诗努力想追求的光明,她感到无助。裤子下的积雪让她感到极为难受,但一切都没有办法。她只能坐着,温暖那些积雪,然后吸收冰冷的雪水。
一会儿后,她的腿慢慢有了知觉,可怜的女人苦笑了三声,她的手在膝盖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情势终于有所缓和,疼痛感消失了,这不像是一种妥协,更像是一种短暂的怜悯。她扶着墙,艰难地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掸去屁股上的积雪,融化掉的早就渗透到她的肌肤里去了,这让她极其不适。腿并没有完全好,颤颤巍巍,直打哆嗦,在起身的时候,诗诗听到膝盖里清晰的嘎吱声,就像老旧的自行车没有上油一样粗糙,里面还有无数的小碎骨在争吵着,聒噪着,她的心头就在此刻掠过一阵恐惧,但还没有来得及沉浸在恐惧之中的时候,又一条短信打乱了她现在困顿的处境。
“再不来孩子就没救了。”
诗诗心急火燎地跑到后门口,不错,跑的,她压根已经没有身体上的病痛了,或许说,身体上的痛楚是被怎样一种急切的精神和爱镇压着,胁迫着?
“该死的腿,你给我坚持着!”
她心底里有一种热喷薄而出,完全变成了一个正常人,科学无法解释,可能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腿的问题,她焦急地全身心去做另一件事,忽略了本身自己生活所不能承受的负担。那就是所谓的爱?
呵!瘸子也能奔跑!
诗诗拨通了电话,出来的人是李彩彩,她睡眼惺忪,一看到诗诗就骂骂咧咧:“三更半夜烦不烦哪!”
“我女儿怎么样了?”诗诗焦急地拽着李彩彩的衣服。
李彩彩眼珠一转:“先把钱拿过来。”这是一只夜间无精打采地出来做贼的老鼠。
诗诗递了过去,李彩彩一把抓过去数,然后转身就走,诗诗连忙拽住她,她在用一种极其卑微的语气恳求:“我的女儿呢,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她死死地抓着李彩彩的衣服。
“我女儿呢,我女儿呢?”李彩彩讽刺地学她的语调说话,摇头晃脑。她面前这个女人压根开不得玩笑。李彩彩感到很无趣,切了一声,丢一下一句话就摔门进去了:“活着呢,一切都好。”
“啊,上帝啊,谢谢您,您一直都在眷顾着我,我终生感念您的恩德。”诗诗双手抱拳站在雪里,看着天空,像一个祷告的天使,在向上帝传达众生的甜与苦,乐与忧。我们的傻姑娘,她怎么又在感念上帝呢?难道她不知道上帝早就脱离了她的阵营?若是上帝真得眷顾她,为什么不让她听听那孩儿的哭声,却要让她生活在欺骗和谎言中,而且,甚至还要为这欺骗和谎言献出自己的身子,任由人践踏!
有一种东西一直是科学难以解释的,就像亲生骨肉间那种微妙的念感。起初诗诗感觉到的是不错的,但是她压根就不会往那边想,她相信也只愿意相信李国大夫妻俩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宇儿,不管她自己吃多少苦,一切都值得。她哪知道什么事实呢?她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在虐待中度过的呢?念宇刚刚一直在哭,若是她能够再坚持哭一会儿,李彩彩开门的时候诗诗可能就听到了,可惜,一切太不凑巧了,一个宽大的身影闪进了房间,那个黑影抱起孩子,在怀里摇啊摇,冲了一罐牛奶慢慢喂她,宇儿停止了哭泣,只是大口大口地喝牛奶,她是饿伤了,也哭得没了气力,就在黑影的怀里睡着了。而那黑影来到这里并不单纯地是想要照顾念宇,李彩彩似乎下楼了,千万别让她听到孩子的哭声后心烦意乱再虐待孩子几下,庆幸的是李彩彩径直开了后门出去,似乎在和谁讲话,黑影紧紧地搂着念宇,那小姑娘立即就在她怀里睡了,李彩彩重又摔门进来,在她离开这里的时候,黑影心里欣喜若狂。确定李彩彩已经上楼后,黑影便轻轻地放下念宇,又急忙逃了出去。一切的一切是这么凑巧又像是故意编排。没有人知道这出戏伟大的编剧--命运--下一步要往哪里发展。某些愚鲁的人甚至还以为李国大正在医院温柔地坐在念宇的病床边,关怀备至,想来,这是何等可笑。
最紧的风头刮过去了,诗诗被刮得什么都不剩了,宇儿终于没事,这比一切都要重要,她现在终于有时间来慢慢反省自己今天的行为。她似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起初她并没有想到孩子交给李国大之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她到现在依然没有意识到她只是在被人玩弄。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拿肉体去交换金钱,此时此刻往回看,她甚至被自己的选择吓坏了。
“我也是一个妓了么?”
人生最难的莫过于做出选择,最最最难的毫无疑问就是明明知道接下来是无数深渊的伏笔,但依旧不得不往前大加迈步,这就是“第一次”所富有的特质,有了第一次,接下来的无数次都可以找到正当的理由来开脱。人性的模式调到了崩溃阶段,接下来的一切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你能保证你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么?万一念宇又出事了怎么办?我们姑且先不论以后这么样,就是现在,这第一次的性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一个伟大的母亲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而去卖淫?难道这就高尚了,呸!当然,诗诗自己压根没有觉得自己高尚,一种抵抗不了的低迷牢牢地把控着她的心,对她自己而言,她感觉到的是可悲,她为自己可悲,她为念宇可悲,可悲她做了自己的女儿,她为那个男人可悲,她为一切可悲。当她心中有一个闪念去拨通那个男人的电话时她的灵魂就已经开始遭受侵蚀,再到后来,她赤身裸体地被一个陌生男人欢爱着的时刻,她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头脑一下子短路了,世界开始晕眩。在那一刻,她感觉自己是个妓女,一个彻彻底底的妓女。她是被迫的,但是,情色行业真正的主流不就是这些被迫的女人吗?若是能够生在一个普通却安定的家庭,她们会选择步上这条道路?懒惰?好吧,人人都会有懒惰的一面,那其中的人因为懒惰而选择这类行业的又是寥寥几何?她们都是苦命的人,有些人甚至为了养家,有些人甚至是为了学生的生活。可是她们不都一直遭受自上而下的谩骂和侮辱,攻击和欺凌。没有人认为她们高尚,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她们的故事,他们所会的就是装成俨然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拿SW说事来突显自己的清高。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种群,一面骂她们是毒瘤,一面又天天想跟在姑娘们后面吸尽她们的毒汁,有人在呐喊--来吧,姑娘们,尽情地毒死我吧!这些人体内的荷尔蒙狂潮过后,就会穿着一个小裤衩,坐在床边跟小姐们讲授君子之道,国家大事,责怪她们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要求她们改过自新,当然了,他们依旧是这里的常客。跟这些姑娘们啰哩吧嗦什么呢?她们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学识,她们中好些人的心智甚至只是个孩子,天真、善良、悲天悯人。但外人真得不关心你是否稚气未脱,只要你是妓女,你就是世界上最十恶不赦的魔鬼,他们还怎么认为你高尚,难道要让他们承认,他们嫖的是一群高尚的人?所以,她们终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管一个姑娘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从事这一行业,她将注定生活在灰色地带,游离在司法保护之外,一切的一切外在因素随时都可以威胁她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很少有人出来维护,很少有人!这一片偌大的土地上,每天光她们就得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去传道,或者说,这个世界上都已经没有人了。任何人都可以抛弃她们,甚至践踏和侮辱,但是作家、公知他们却不应该离弃这个广大的群体。可是那些伟大的人在干什么呢?那个什么什么狗屁头衔的某作家成天和某个什么什么头衔的公知人士天天就身高的问题切磋琢磨,后来他们又转移话题来讨论那狗屁文章是不是那人自己写的!他们两人伟大的学术精神和涵养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就是国人的希望!国人的骄傲!
说自己是小人的难免不会有君子,说自己是君子的一定是小人。
世界是灰暗的,就和现在下雪的灰暗世界一样,诗诗步履蹒跚在晨里的雪地中,她心里已经接受了一个观点--她已经是一个妓了。当她第一次做出选择那样做时,她就已然沉沦,当她自己接受自己贴上这样一个代名词的时候,她已沉沦得好深好深……
我的爱人,这并没有什么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