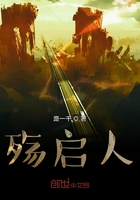城,就来源说不温雅,是为防守;用诛心之法深挖,是内,舍不得自己的所有,外,把不少人看成小人或敌人。事实是确是有小人或敌人,于是经验是,实利经常比理想分量更重,人,有了较多的财富,包括子女玉帛之类,并有了权,就(下令)筑城。财富和权有大小,城也就有大小。最大的是现在还夸为国宝的万里长城。其实又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不过是自己外强中干,怕匈奴南下牧马而已。理论上,对付南下牧马,还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己有大力,新词儿曰威慑力量,使不安分的异族不敢南下牧马。二是自己有大量,视南下牧马为无所谓,这还有个说法,曰“人失之,人得之”。显然,这只是理论,至于事实,大力来于励精图治,大量来于视人如己,有了权,容易把享乐摆在第一位,理论上的两种办法就都行不通了。结果是还得筑城,权大筑大的,权小筑小的;大还包括多,如皇帝老子,凑全了应该是,城之外有郭,即外城,城之内有皇城,皇城之内有宫城(末代的清朝名紫禁城)。皇帝之下有官,官有大小,依例而城也有大小,于是而有省城、府城、州城、县城,又于是而大大小小之城遍天下矣。
人,有理想的一面,是讲理,或希望讲理;但更多的是事实一面,既来之,则安之。对城也是这样,既然有了城,日久天长,就觉得还是以有它为好。这感觉也不无理由,以《清明上河图》所描画为例,上河,无妨出宋门野一阵子,至于华灯已上,登玉楼,倦倚屏山,就还是以入宋门为是。且说宋门以内,还有个不容忽视的优越性,是有了城,多人聚居,会带来繁华和方便。除了巢父、许由、马祖、赵州之流以外,有几个人不欢迎繁华和方便呢?
我是常人,当然也欢迎这样的繁华和方便。并曾设想,由于某种原因,要长途跋涉,劳累,口渴腹空,到日薄西山的时候,眼前终于出现了雉堞,其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呢?是真就宾至如归了。单说想象中,是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在城门外或内,找到个《老残游记》那样的高升店,也许竟如卢生住的邯郸旅舍,主人还蒸黍米饭,供应饭食吧?那就可以“解衣般礴”,喝白干,佐以花生仁,然后饱餐黍米饭,兼听“画角声断谯门”了。
这是与城有关的诗的生活。诗与梦是近邻;梦想太多不好,因为容易随来破灭。那就还是想想实实在在的。我的出生地是农村,在京津之间。没有机会到较近的天津和较远的北京看看,但童年想象力强,希望迫切,常常闭目设想,就在不很远的地方,有豪华,有热闹,这豪华和热闹是在一个高大的城墙里。城墙有多高呢?城门是什么样子呢?很想看看。直到过了十岁,才有机会,第一次看到城,并穿过城门进了城。但那不是天津城,更不是北京城,而是本乡本土的香河县的小城。记得其时我还上初级小学,是秋末冬初,县里开小学生成绩的观摩会,各校都挑选几个学生为代表去参加观摩。
我也许不像现在的甘居下游吧,由老师选中了。十个八个人,由老师带队,早饭后出发,步行向西北,还要涉水过运河的支流青龙湾,约五十里,很累,但到太阳偏西时候,终于远远地望见南面城墙的垛口。其时我是初见世面,觉得城墙很高,有小村庄所没有的威风。接着想到,能走进这样的城,与未被选中的同学相比,真是高高在上了。于是忘了劳累,加快往前走。不久走到南门前,更细端相,门拱形,高大,深远成为洞,都是过去没见过的。入了门,往前瞭望,直直的一条长街,两旁都是商店,像我们这小村庄来的,真不能不自惭形秽了。走到接近北门,住在门内路东一个客店里。夜里,想到有生第一次住在城里,很兴奋,也很得意。早晨,天微明,躺不住了,爬起来,几个人一同登城。记得是半走半跑地往西行,眼忙着看城内的人家,城外的树木。不久就绕回来,馀兴未尽,都同意,又绕一圈。几天过去,原路回学校,向未选中的同学述说所见,着重说的就是那个方正而完整的砖城。
离开家乡以后,几十年,我到过不少地方,也就见过不少城。印象深的当然是住得时间长的。以时间先后为序,先是通县,后是北京。通县,最使我怀念的是新城西门,那是晚饭后或星期日,多数往门外以北的闸桥,少数往城西的八里桥,都要出入这个门。闸桥是通惠河上的一个闸,其时河上已不行船,岑寂,或说荒凉,立其上,看对岸墓田,水中芦苇,我常常想到《诗经·秦风·蒹葭》,并默诵“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是有所思,思什么呢?自己也不清楚。但这是生活,值得深印在心里的。离开通县,到了最大的(也许要除去南京)北京城。我住内城,常到外城,并不断出城,可以说,生活总是与城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最难忘怀的是经由西直门出城,那有时是与三五友人往玉泉山,坐山后,共饮莲花白酒,然后卧林中草地上听蝈蝈叫。更多的是与墅君结伴,游农事试验场,麦泛黄时,坐麦田中听布谷叫,晚秋,坐林中土坡上听蟋蟀鸣。一晃几十年过去,城没了,出入城门,游园,并坐话开天旧事,都成为梦。有的人并默默地先我而去,因而有时过西直门,心中就浮起李义山的两句诗:“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随着拆城的一阵风,我第一次见的香河县小城也没了。远望城垛口,住城门附近小店,听“画角声断谯门”的梦真就断了。对于城,如果仍恋恋不舍,就只好安于李笠翁的退一步法,寻遗迹,看而想象其内外,发思古之幽情。语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许多城高而且厚,斩草除根不易,遗迹也不会少。举其荦荦大者,如北京有元土城,南京有石头城,不久前与莉芙女士往郑州,还看到商朝的一个都城(仲丁迁的敖?)的遗址。可惜的是,与我关系最深的那个香河县小城却连遗迹也找不到。但因为时代近,变化的迹象易寻,城基,东西南北门,中年以上的人还能指出来。我近年有时到那里住个短时期,住所在东门附近,常常经过旧的东门和城东南角,就不由得想到昔年有城时候的种种。不免有黍离之思,秀才人情纸半张,曾诌七绝一首云:“绮梦无端入震门,城池影尽旧名存。长街几许升沉事,付与征途热泪痕。”有征途,证明有聚散;有泪痕,证明我没有忘记这个小城以及其中的一些人。只是可惜,去者日以疏,至少是有时候,我对影感到寂寞,东望云天,确知已经不再有那个小城,连带的也就失去许多可意的,就禁不住为之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