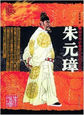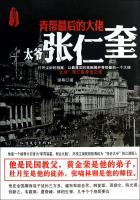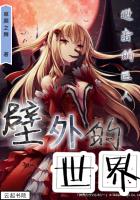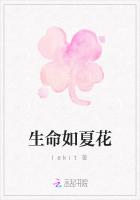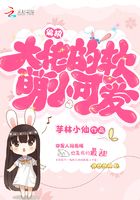弗雷德·霍伊尔听惯了掌声和赞扬声,第一次碰到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向他挑战,心里面觉得很不是滋味。当他听到下面的议论声和笑声时,使他感到有些尴尬,也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怒不可遏。他火冒三丈地指责霍金完全是外行,违背职业道德。霍金也当仁不让,指出霍伊尔不应该把没有经过证实的成果公布于众,这样做才是与职业道德相违背的。本来这是一次很正常的学术讨论,由于霍伊尔比较自负和怕丢面子,他根本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以致后来双方都有些不太冷静,互相说了对方一些过头的话。虽然他俩的对峙和交锋是短暂的,但大名鼎鼎的霍伊尔教授和默默无闻的研究生霍金之间的争论却展开了。当时,作为霍金的同学、朋友的杰恩特·纳利卡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这种被夹在霍金和他导师霍伊尔之间,处境是十分难受的。那些日子,他整天无精打采的.可以想像他的导师霍伊尔是如何严厉地训斥他的。
霍金既然敢于指出霍伊尔理论上的缺点,必定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霍金虽然当时还很年轻,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是十分严谨的。更重要的是,霍金早就对霍伊尔的理论感兴趣,对他的理论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认识了霍伊尔的学生纳利卡以后,霍金对这个理论的许多部分作了数学上的详细论证。霍伊尔虽然智力过人,而且在这个领域经验十分丰富,但由于他急功近利和骄傲自大,理论上的漏洞也是明显的。那次在会议上的争论之后,霍金回去立刻着手写了一篇论文,详细阐述他的观点,论证霍伊尔理论中所提到的那个量是发散的。霍金的观点一经公开,立刻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许多同行认为霍金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有的人认为霍金是物理学领域的一颗新星,其前途不可估量。
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前两年中,霍金的病情恶化得很快,正如当初医生们所说的那样,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确是十分可怕的。他行走愈来愈困难,有时只能靠着拐棍往前挪动几步。他的同学、朋友都十分关心他,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但倔强的霍金往往不愿意过多地麻烦别人,总是尽量地自己照顾自己。他常常扶着墙壁、拄着拐棍在房间或户外缓慢地行走。有不少次,他被重重地摔在地下,身体受到了严重撞伤。他的导师和同学有时看到他的头上缠着绷带,毫无疑问他又因行走不便摔着了。他说话也受到严重影响,说得越来越不清楚,他的亲人、导师、同学和朋友几乎听不懂他说些什么。这时,他比刚患病时要坚强得多,他把心思几乎都用在了研究上。他这个时候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似乎已经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他有时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几乎忘记了自己已经是病魔缠身。他不想向病魔低头,不想让那讨厌的病影响他的研究进程。幸运的是,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没有对霍金的思维产生什么影响,这对研究理论物理学的霍金来说是提供了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极为难得的机遇。虽然他已行走困难,说话也模糊得让人难以听清,但他的大脑却是运转正常的。霍金的这种境况让人感到很吃惊,他以极为清晰、细密的思维进行着数学推导和理论论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这时,珍妮·怀尔德姑娘与斯蒂芬·霍金的关系也有了进展。他们周末的约会越来越频繁,他俩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珍妮当时还在伦敦的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学习,每个周末她都从伦敦到剑桥来,与斯蒂芬一起度周末。他们相互发现对方有许多优点,越来越觉得离不开对方。珍妮是位很了不起的姑娘,在她身上透露着一股纯洁、高雅、清新的气息。她不受世俗偏见的束缚,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她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斯蒂芬的父母及亲属们都非常感激珍妮姑娘在斯蒂芬患病时所做的一切。珍妮姑娘没有嫌弃斯蒂芬而远离他,而是不顾各种困难去帮助他,尽可能地让他感到欣慰。斯蒂芬的导师、同学和朋友也都对珍妮姑娘的这种行为备加赞赏和钦佩。珍妮姑娘明明知道斯蒂芬得的这种病很危险,即使能够治疗也只是控制住病情不再发展,但她还是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走进斯蒂芬的生活中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俩决定订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当然,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珍妮,认为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残疾人拴在一起。况且斯蒂芬的病情还在加重,将来的后果难以预测。当别人对她不理解时,珍妮姑娘说:“我自己决定了要做什么,就这样做了。我和他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得病了,我不知道一个体格健全的斯蒂芬是什么样的。”
斯蒂芬·霍金虽然很倒运,但珍妮姑娘的降临却使他感到了生活的幸福和快乐。与珍妮姑娘订婚给了斯蒂芬生活的勇气,鼓舞着他去完成博士学业,然后找一个适合他的工作。也许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他重新鼓起了生命的航帆,在与病魔斗争的同时,努力地继续从事他的宇宙学的研究。他终于从生命的低谷中走出来,向着取得博士学位目标前进。
这时,斯蒂芬·霍金在选择博士研究课题上也有突破。霍金的导师丹尼斯·夏玛带着他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生到伦敦去拜访一位名叫罗杰·彭罗斯的年轻数学家。罗杰·彭罗斯是一位著名遗传学家的儿子,早年曾在伦敦上大学。20世纪50年代,他大学毕业后来到剑桥大学,成为丹尼斯·夏玛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到了伦敦的伯克贝克学院工作,当时在宇宙学领域是知名的数学大师。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彭罗斯一直在从事奇点研究,提出了独特的奇点理论。奇点是空时中密度为无穷大的点,虽然根据广义相对论可以推出奇点的存在,但是那时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有奇点存在。彭罗斯用新的数学方法证明,宇宙间的恒星坍缩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一个密度为无穷大的奇点。在彭罗斯得出这一结论之前,人们认为只有完全对称的恒星,才会在坍缩时变为奇点;而其他恒星在坍缩时,坍缩物质有可能穿过太空,而不是紧缩在一个奇点上。罗杰·彭罗斯的理论给了霍金很大的启发,霍金敏锐地感觉到,彭罗斯的这一奇点理论可以被应用于宇宙起源的研究上。如果把宇宙膨胀看作是恒星坍缩的逆过程,那末按照彭罗斯的奇点理论,在很久以前的某个时刻,宇宙就是一个密度无穷大的奇点。霍金向导师丹尼斯·夏玛汇报了他的想法,他的导师也认为这是一个创新性的观点,要求他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丹尼斯·夏玛还经常带着他的研究生们到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去听讲座。国王学院有许多知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常常举行报告会和研讨会,还邀请一些来自其他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罗杰·彭罗斯也是国王学院的研讨会和报告会常客。当然,参加会议的学者观点也可能截然对立。宇宙稳恒态论的创始人之一、国王学院应用数学系的教授赫尔曼·邦迪也常在会上演讲,介绍自己的观点。霍金虽然行动十分不便,他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前往伦敦参加这些会议。他觉得参加这些会议对他启发很大,能够激发他的灵感。有一次,丹尼斯·夏玛带着他的四位学生乔治·埃利斯、布兰登·卡特、马丁·里斯和斯蒂芬.霍金到伦敦去参加报告会。当他们快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进站了,他们就拼命地跑着赶火车。他们好不容易进到车厢里来,发现霍金还在站台上非常艰难地挣扎着往前挪动。两个同学看到这种情景,从车窗里跳下去,帮助霍金上了火车。
霍金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找到了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形成了博士论文的框架。他准备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深入地探讨关于宇宙起源于一个密度无穷大的奇点问题。他所选的研究课题受到他的导师夏玛的重视,夏玛认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课题,鼓励他深入地研究下去。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霍金非常努力,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刻苦过。由于奇点问题既是数学上的难题,也是一个物理学上的尖端问题,所以研究起来难度相当大。它涉及数学上的无穷量、物理学上的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问题,要求研究者的数学基础要扎实,在物理学领域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霍金完全具备这些才能,他将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他首先开始数学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着手撰写博士论文。
霍金的博士论文终于写成了。除了珍妮姑娘和他本人外,无人能够感受到这篇博士论文中所蕴涵着的艰辛。它是霍金用整个生命写成的,凝结着他的无数汗水和心血。当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凝结着他朋友、同学、亲人,特别是他老师和珍妮姑娘的辛勤汗水。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鼓励和支持,霍金要完成这篇论文也是不可想像的。
霍金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写得相当精彩,其中包含着宇宙起源的奇点定理。他在论文中指出,是否有过大爆炸奇点的问题对于理解宇宙的起源关系重大。他紧接着论证道:“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任何合理的宇宙模型都必须起始于一个奇点。这就表明,科学能够预言,宇宙必须有一个开端。”他认为,虽然过去有人相信宇宙有一个开端,但无人能够解释宇宙在这个开端上是如何起始的。物理定律在该处真的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不起作用吗?其实不然,物理定律在宇宙的奇点上仍起作用。但仅仅根据广义相对论是推不出这一点的,这就需要一种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的理论。
在霍金博士论文的最终评审中,评委们一致认为,霍金把奇点定理运用于宇宙起始状态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虽然这篇博士论文的前面几章显得有些乱,表明霍金在剑桥大学前两年的学业不够扎实,但其最后一章由于包含了对奇点定理的深刻理解,使得这篇论文的分量大大加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这样,评委们通过了霍金的博士论文,霍金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23岁的他成了斯蒂芬·霍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