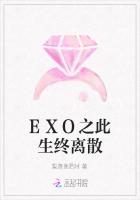在建新木器厂工作两年后,赵伯被调到新成立的乌鲁木齐市二轻局汽车修理厂。尽管每月不到七八十元的工资,加上加班计件补助,也就百多元。全家人最多时大小10口,全靠这点工资生活,孩子们要上学,如果生病,还要支付吃药打针的钱,想来经济十分紧张。可是,赵伯回忆这段日子,却显得很轻松。他说:“安拉的恩典,就那点钱,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好。当时一袋面最贵时80块钱,老家还时不时来亲戚,但我们从来没有借过别人的钱,也没有遇到过揭不开锅的困境。”
1980年,赵伯58岁,并没有到退休年龄。但为了赶当时的“接班”政策,他就把自己的年龄报大了两岁,提前退休,让二儿子顶替。因为二儿子初中毕业后不愿考高中,他担心学坏,所以就早早安排了工作。
退休后,赵伯又同几个老朋友合伙,贩卖了几年黄金。开始还赚了一些钱,后来金价下滑,赚的钱没了,本钱也赔进去不少。吃了这次亏,加之孩子们都基本上成人了,赵伯也就不再东奔西跑,开始靠5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尽管和有钱人比较,破旧平房,没有高档家具,不能大口吃肉,也不能穿高档服装,但赵伯说这种平常日子过得安宁。
五
在西大桥租房住了几年,市政建设搞征迁。因为他们租住的是公家的房产,就把他们安排到了二道湾聋哑学校附近的平房。后来赵伯嫌距市区远,就想办法搬到了文化宫一侧的居民区。在这里,赵伯一家一住20年,6个孩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赵伯夫妻为人诚实,待人热情,住到哪里,左邻右舍都说好。赵伯想的是,自己年轻时糊里糊涂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买卖,后半辈子应该多做点善事,祈求安拉的饶恕。
1971年春天,当时的市革委会在文化宫礼堂组织宗教界人士,集中批斗反动阿訇金如贵。原来,金阿訇是老坊寺的伊玛目。“文革”中造反派占领了老坊寺,改做什么加工厂。金阿訇和几个虔诚的哈宛德22一商量,有天突然到寺里,把已经安装好的机器都搬出了寺外。这一下惹了大祸,成为乌鲁木齐反动阿訇一手策划和组织的重大反革命案件。批斗大会全天进行,中午在文化宫食堂吃饭,稍事休息就继续开会。一些阿訇不愿耽误晌礼,可是没有地方去洗小净,也找不到僻静的地方礼拜,很是着急。赵伯知道了情况,就把自己熟悉的几个阿訇,包括“文革”前在陕西大寺开学的尔目阿訇,在撒拉寺开学的艾里阿訇,在凤翔寺开学的马安泰阿訇等七八个人,领到自己窄小的家里,让老伴烧洗小净的热水,腾开一间房子专门供他们做乃玛孜。批斗会开了整整一个月,这几位阿訇就安心在赵伯家做了一个月的晌礼。快结束的那天,赵伯还想办法买了些肉,请几位阿訇吃了一顿午饭。
恢复宗教政策后,马安泰阿訇当了陕西大寺的伊玛目,担任了自治区政协的常委和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的副会长,地位高了,却始终记着赵伯的这番盛情。多次给人说:“那个年月,人们见了我们阿訇,躲都躲不及,谁敢给一汤瓶水?赵维杨老汉是真正的穆民,一家人冒着危险操心了我们一个月。我们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赵伯对他说:阿訇是穆民的柱子,我担点惊给阿訇一些方便,是在罚赎自己以往的罪过,老人家就不要再把这件事挂在嘴上了。
1988年底,文化宫居民区征迁。赵伯一家来到当时还比较偏僻的宁夏湾地区,买了一个有几间平房的小院,一直住到现在。
当时这儿交通不太方便,坐公交车要走一两公里。环境也不太好,周围不是农民的菜地,就是垃圾场。但是除了小儿子和小女儿,其他的儿女都已经成家,所以对老两口来说,僻静一些反而好,尤其是他们搬来时这里正在准备兴建清真寺,做乃玛孜很方便。“对于上年纪的穆民,住在寺周围,比啥都强。”当已经独立生活的儿女们不大满意时,赵伯总是这样知足地回答。他惋惜的是,劳累了一辈子的老伴没有在这里安然生活多久,1991年初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当然,现在的宁夏湾已经今非昔比。清真寺早已建起来了,尽管不大,但比较精致,聘请的年轻伊玛目有尔林,也有思想,每次听他的卧尔兹很有教益。市区的公交车基本上通到了门前,垃圾场变成了新住宅区。剩下的一点菜地,成了房产开发商的抢手货,但听说由于市政府已经规划要在宁夏湾建一座现代化大公园,严禁新建任何建筑,因此至今没有动。赵伯又一次没有想到,他选择的宁夏湾这个便宜小院,最后竟然是乌鲁木齐的宝地。
赵伯家离寺门不到100米,一天五番乃玛孜他都到寺里去做。别说经常做乃玛孜的五六十个信士,就是聚礼日来做礼拜的穆民中,赵伯也是年龄最大的人。赵伯也从不倚老卖老,他十分尊重伊玛目,对待寺坊大大小小的穆民,以及周围的汉族朋友,也都很谨慎,很热情。他虽然没有上过一天汉文学校,但是到底念过几年经,也自学过一些汉字,因此在老人中间,也算知书达理的人。特别是他诵读《古兰经》,很合“特旨维迪”,家里人和邻居都喜欢听。每天早上,他坚持晨礼后诵读雅辛,每天晚上宵礼前赞念特巴热。2002年(教历1422年)2月,他在儿女们的支持下,前往沙特朝觐。在尊贵的圣地,他不仅完成了主命朝觐功课,而且虔诚举意,祈求安拉饶恕自己一生的罪孽。朝觐归来至今,他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努力使自己言行不偏离教法,一心一意求取安拉的喜悦。
赵伯从祖父那辈就遵行伊赫瓦尼教法主张,但是他从不非议其他教派。他始终认为,大家都拜的一个安拉,跟的一个圣人,念的一本古兰,遵的一个伊玛目,没有必要闹矛盾。只要自己诚信端庄,各干各得,不应该干涉别人的具体做法。由于他行为中正,虔敬高寿,尽管没有担任清真寺里的任何职务,但是走到哪里,都很受大家尊敬。大寺理事会的成员,常常同他商量寺里聘请阿訇、翻建寺院等重要事务。从赵伯搬到宁夏湾开始,这里迎送朝觐阿吉,处理婚丧嫁娶,甚至谁家来了尊贵客人,哈宛德都喜欢请他老人家到场、作陪。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寺开学阿訇是伊赫瓦尼派的,哈宛德中却有不少格底木,大家每天到寺里一同礼拜,彼此尊敬,相互理解,没有出现疙疙瘩瘩的不愉快事情。
六
赵伯的8个儿女,个个相貌堂堂,聪明伶俐,但是按赵伯的话说,到目前为止,不仅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一两个还曾经走过弯路。
大女儿已经53岁了,老实憨厚,能做一手好饭菜。丈夫是老新疆人,汽车驾驶员出身,身体不好,目前在家除了做乃玛孜,就摆个小摊子,和妻子一块做些小买卖。他们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开出租车,家里生活主要靠这份收入。老二在煤矿学院上大学,这是赵伯后代中唯一的一个正在受高等教育的孙子。
随买氏到赵伯身边的儿子,从小至今,没有见过自己生身父亲,自小随赵伯姓,一直在赵伯身边长大。初中毕业后在乌鲁木齐低压锅炉长当工人。赵伯给娶了媳妇,添钱买了房子,生了一个女儿,也是初中毕业生,前一阵子在一家商店卖手机,收入还可以,按道理一家三口日子应该不错。可是1999年低压锅炉厂被广汇集团收购,大儿子下岗后就再也没有找到合适工作,又对教门不上进,一番乃玛孜不做,整天闲着,两口子有时闹些矛盾。幸亏那个大孙女懂道理,不然一家生活很难过下去。
二儿子初中毕业便顶替赵伯,到二轻局汽车修理厂工作,干了11年修理工,手艺不错。媳妇很贤惠,还有一个女儿。四年前修理厂改制,老工人给一点补助都安排回家,也闲在家里了。本来心情不好,没有想到翻过年家里又出了大事。当时正是赵伯出国朝觐期间,一个傍晚,二媳妇领着女儿出去买东西,在喀什东路被一辆大型柴油货车撞倒,母女俩当场都断了气。老二平时对教门上的事情懂得不多,信仰比较淡薄,面对这些灾难,不认为是安拉的考验,认为自己倒霉,从此精神萎靡,生活没有了规律。开始赵伯还很同情,不仅反复安慰,还时不时贴补点生活费。可是他听不进去好话,有钱就乱花,惹得赵伯不愿再答理。
二女儿为人谨慎,教门虔诚,但是结婚后经常有病,只能操持家务,没有在外面干什么。女婿叫由布,是个念经人,老根子是河州莫尼寺沟的。“文革”前在河州寺哈三阿訇那里当满拉,“文革”后在陕西大寺马安泰安訇跟前又学过几年,还到宁工寺当过二阿訇。因为脾气直,个性强,与人合不拢,后来跟人跑生意,当时改革开放不久,确实挣了一些钱。后来买卖不好做了,也就在家闲坐着。有两个丫头,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书都念得不错。听说政府这几年每月给一点救济,两个丫头的学杂费也免了。眼下看,赵伯儿女中就他们家生活比较紧张。
三儿子在四个儿子中最有教门,家庭也最和睦。高中毕业先是学理发技术,干了几年理发行当,去年应聘到南湖家乐福大型超市作管理人员。三媳妇原在水磨沟“七一纺织厂”上班,后来下岗,生了一个女儿,已经9岁了。丈人是东乡果园人,家里教门好,所以对丫头从小管教严,三媳妇过门这些年对公公婆婆十分孝敬,对丈夫也照顾得很周到。两口子信仰都很虔诚,五番乃玛孜不拉,斋月里一天斋不缺欠。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小日子过得安宁,赵伯很放心。
三女儿人麻利,女婿也好。可是,俗话说的好,人喜的安拉也喜。三女儿过门后身体就一直病病殃殃,生下儿子也就一年光景,由于脑部疾病治疗无效,1995年归真了。过了两年,女婿也得病离开了人世。失去父母的娃娃没有了依靠,由于婆家只有一个残疾叔叔,而娃娃姑妈又没有儿子,就被姑妈要过去抚养。可是,一年后好心的姑妈也无常了。那个残疾叔叔个人顾个人都困难,娃娃没有管,赵伯不能眼看着女儿的骨肉受苦,就领到了自己家里。2004年,听说娃娃的残疾叔叔也口唤了。
小儿子是1974年出生的,在儿女中间,身材最高,脑子最灵活。赵伯家搬到宁夏湾时,他刚上初中。当时宁夏湾有一帮小混混,不知什么时候小儿子和那些娃娃成了“哥们”,从此不好好读书,整天瞎逛,初中读了两年就肄业。他母亲去世那一年,赵伯担心这小子混下去出事,就拿出5000元积蓄,让他学习汽车驾驶,以为学了技术,有了固定工作,儿子就不会再走歧路。可是没有想到,儿子的汽车驾驶执照考到手了,那可恶的“白面”也缠上了他。
为了戒毒,赵伯先后4次送小儿子到戒毒所戒毒,每次都报了很大希望,但每次都失望。从戒毒所出来,短则一半个月,长则半年,这小子就老病复发,想方设法撒谎跟赵伯要钱,偷偷摸摸吸食毒品。每次送进戒毒所,赵伯因为盼望着儿子出来后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年年花钱替他审验执照,然而连续审了10多年,儿子也没有用过1个月。赵伯从伊斯兰教法到国家法律,从对身体的摧残到对社会的危害,不知道给小儿子讲了多少遍,有时甚至是反过来在求自己的儿子。但是,“白面”的力量太大了。儿子往往当面答应得很好,可一遇到那些“白面客”,就把什么都忘光了。平时在那里鬼混,毒瘾一犯,没有钱买,就到家跟老父亲索要,到哥哥姐姐家强借,一次两次可以给点,但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所以就让他空手离开。每当这时,这小子就破口大骂,说我这样难受,你们就忍心看着?我恨你这个老子,我没有你这个姐姐。赵伯有时候禁不住想,这不会是自己年轻时候贩卖那害人东西的报应吧?
也就是最近一两年,小儿子到父亲和兄妹家要钱的次数明显少了。这两三个月,买了水果来看赵伯,说在给一个老板发货,干的是正经生意,请爸爸别再操心。给姐姐和哥哥也这么说。赵伯听了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安拉的引导下,这个坏小子终于改好了。担心的是过些日子又犯病。几乎每番乃玛孜,赵伯都在做杜瓦:安拉啊!你是全能的主,求你引导这个娃娃,让他回归正路吧!
老伴归真后,赵伯一直和最小的女儿一同生活。三女儿的儿子,赵伯领回来时才5岁,居委会每月给200多元的孤儿生活费。今年孙子12岁了,正在上小学5年级,还比较懂事。去年,小女儿结婚。女婿是老家广河排子坪人,在兰州当厨师,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小两口几乎天天通电话,感情很好,就是一年回不来几次。这样,平时家里就赵伯、小女儿和失去父母的外孙子3口人。小女儿孝顺,也勤快,除了来客人接待,赵伯基本上不操心什么家务事。
谈起孩子们参差不一的原因,赵伯认为:人能不能成才,既有安拉的定然,也靠父母的教育。作为父亲,他当时忙于工作,精力和时间都耗在厂子里,娃娃们主要靠母亲管教。可是买氏没一点文化,也没念过经,没啥系统的教育办法,只是操心儿女的吃饭穿衣,有功夫也不过是叮咛两声:“好好学习!别交那些坏娃娃。”至于到底学习如何,究竟平时跟谁来往,既不了解,也无法管束。孩子们基本上都是自我约束,自行成长。因此,虽然出自一个家庭,但人生追求、为人品行的差距比较大。
赵伯说,儿女没有一个值得他自豪的,是他后半辈子的遗憾。如今总结教训,主要有两条。其一,打小要想办法让娃娃们进寺里学些教门的基本知识,把他们信仰的根子扎牢。一个人相信后世,害怕安拉,一般就知道自己约束自己,不会做出格的事情。其二,要让娃娃们多读书,学些真本事。过去,农村里就是种田,不识字好像也没有什么大妨碍。现在这新社会,发展这么快,人没有文化就是瞎子瘸子,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生活当然也就没有保障。没有知识,遇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分不清是非,容易走错路。所以多学知识不仅是今世生活的必需,也是后世得脱离31的正道。
(采访于200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