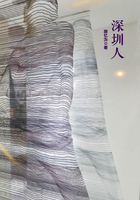闻言,阿房睁大了眼,顾不得嬴政有多么可怕,双手紧紧揪住他的衣襟,连声追问:“真的吗?落尘哥哥真的平安无事吗?”他能起兵,就说明生命无恙。这个消息,令阿房欣喜若狂。
觉察失言,嬴政有些后悔,覆水难收,索性继续说下去:“这下,你明白了吧?他在天下和你之间,做出了选择。明知道你有危险,依然醉心于王权的争夺。”
后面的话,阿房一句都没有听到。她只知道,苍落尘平安无事,这就已经足够了。之所以不来救她,一定有他的苦衷,她只需要等待,等待他来救她就可以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活着。”这句话是他们分离时许下的承诺,苍落尘和她,都没有食言。
将阿房的失神误以为是伤心,嬴政继续嘲讽道:“这下知道了吧?所谓的爱情根本经不起考验,只有权力和地位才是最可靠的。”
说着,调转马头,向营地而去。
回来后,嬴政唤过一名侍卫,吩咐几句,这才带着阿房入账休息。
不一会儿,便有两个士兵抬进来一口沉甸甸的木箱,轻轻放在地上,恭敬地退了出去。
疑惑地看着木箱,阿房不知道嬴政有什么意图,警戒之心又起,悄悄向后退了两步,清澈的眼睛眨也不眨,盯着嬴政。
无视阿房警惕的神情,嬴政径自上前,撕去箱子上的封条,双手用力,箱盖随之而开。
箱子打开的刹那,珠光流转,宝气氤氲,满室的灯烛顿时黯然失色。箱子里,满满的都是奇珍异宝。这些,是从韩国国库中挑选出来的稀世珍品,随便哪一样,都是价值连城。
“寡人宫中的珠宝,比这些还要珍贵。只要你想要,尽可以随便挑选。只要你答应,从今往后留在寡人身边,将你的人和心都交给寡人,用你的能力守护我大秦,这些,都是你的。”嬴政随手从里面抓出一块硕大的上乘翡翠,递到她的面前,“喜欢的话,就拿去雕成首饰。”给她这个,是因为她似乎很喜欢玉佩。这块翡翠比她颈间佩戴的那块羊脂玉坠贵重得多,想来,她定会喜欢。
“我不要。”看都不看一眼,阿房冷冷拒绝。不是苍落尘给她的,纵然是天下至宝也只是石头一块。
“你!”只因为这漠然的拒绝,嬴政的怒火终于燃到了极点,抬脚将箱子踢翻,在珠宝散落声中一把将阿房抓起,拎到了帐外,伸手抓过马鞭,怒吼道,“枉费寡人对你如此迁就,如此纵容,你却执迷不悟!那个苍落尘有什么好?值得你如此执着?若是不给你一些教训,难消寡人心头之恨!”
第一次想要宠溺一个女人,却被她视如敝履。只要想到她心中始终念念不忘另外一个男人,嬴政的怒火便再难遏制。
看着伏在地上,因为恐惧而颤抖,却始终倔犟地咬紧唇,不肯松口求饶的阿房,嬴政青筋暴突,握着马鞭的手,高高扬起,却始终没有落下。
向来残忍狠毒的他,纵然是在暴怒之中,依然无法狠下心,鞭打眼前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可是,不给她一点颜色,又实在难以驱散他的烦躁和恼怒。
寒风,呼啸而过。左右为难的嬴政忽然看到了马背上的水囊,眼睛微微眯起,有了主意。
慢慢蹲下,嬴政轻轻抚摸着阿房单薄的背:“你穿得这么少,此刻,一定很冷吧?”虽然是关心体贴的语调,声音却阴森恐怖,闻之,却令人胆寒。
夜晚的沙漠,阴寒刺骨,加上肆虐的寒风,阿房早已冻得手脚发麻。加上嬴政阴恻恻的语气,她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噤。
“别急。很快,你会更冷。”邪美的容颜挂着残忍的神情,此刻的嬴政,已经变成了恶魔。
阿房的心,因为恐惧而抽搐。还未想明白他话中的意思,冰冷的水,已经从头顶淋下。
青丝,瞬间湿透,狼狈地贴在脸颊和后背上。顺着发丝的末端,向下流淌。最终渗入黄沙,不见踪迹。
还未等阿房反应,又是一袋水泼在身上。单薄的衣衫,贪婪地吸收着水分,很快,便已湿透。
全身的肌肤刹那间紧紧绷起,本能地想要抗拒这刺骨的寒冷。可惜,这样的抵抗,根本无济于事。严寒张开大口,贪婪地吞噬着阿房的体温。牙齿咯咯作响,纤弱的身躯开始无意识地痉挛。
嬴政居高临下,冷笑道:“如何?这滋味是不是很过瘾?只要你跪下来认错求饶,寡人就饶了你。”说着,嬴政返身进了帐篷,准备等阿房冷得受不了,进来求他。这个教训应该足以令她记忆深刻。这次过后,谅她以后再也不敢挑衅他的权威。
等了许久,阿房却毫无回应。嬴政的怒火更盛。这女人,未免太倔犟了一些。
大步出了帐篷,见阿房依旧是之前的姿势伏在地上。嬴政更加恼火,弯腰抓起阿房肩膀,将她身子转过来,咬牙切齿:“你是准备和寡人一直较劲到底是吗?”
阿房原本低垂的头,随着这个动作,软绵绵地仰起,露出修长的脖颈和她颈间的鸿鹄玉佩。向来温润洁白的玉佩,此刻仿佛感觉到了主人的痛苦,透出不祥的青色。
几缕冰冷浸湿的长发,紧贴在她的脸上,漆黑、死寂。她的脸,与玉佩一般,冰冷,透出淡淡的青色。一侧脸颊,沾着少许黄沙,有几粒,随着嬴政的动作,无声地滑落,仿佛失去生命的流星。
阿房的手脚,已经停止抽搐。修长的臂,亦是软绵绵垂下,因为嬴政的摇晃,在身侧划出不规律的弧线。
“说话,不许在寡人面前装死!”手上加大力道,嬴政提高声音,几乎是大吼出声。她一定是装的,装出这副可怜的样子,博取他的同情。就好像是那天假装扭伤脚,伺机逃跑一样。
可是,她身体的冰冷透过他的掌心传来,他的心,忍不住颤抖起来。
这样的冰冷,不是装出来的。这样冰冷的她,就好像是已经……死了!
不会的,怎么会这样?他只是想给她点教训,却从未想过要她的命。她虽然身子单薄,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会昏死过去啊!
飞快扯下身上的洁白狐裘,将阿房全身包起,只露出一张惨白泛青的小脸。快步走回帐内。
手指颤抖,探向阿房颈间。巨大的懊悔和恐惧紧紧将嬴政勒住,连呼吸,都变得格外费力。
从未感受过后悔和害怕的感觉,今夜,他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滋味。
指尖,传来微弱的脉动,虽然无力,但确实是在一下一下顽强地跳动。
她,还活着!
紧紧将阿房抱起,希望能用这种方式给她更多的温暖。口中嘶吼:“快叫军医来!点上暖炉,越多越好!军医,军医怎么还不来?再耽搁,杀无赦!”
军医气喘吁吁,拼了命地跑来,还未进门,便听到最后一句。
当即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进了营帐,他连声求饶:“王上饶命!王上饶命啊!”
哪有心思听他废话,嬴政伸手,将军医像拎小鸡一样拎到阿房身前,用杀人般的眼神盯着军医:“无论如何,你要把她救活。若是除了差池,寡人就将你千刀万剐!”
凉气顺着脚后跟一直爬到头顶,军医咽了口唾沫,强自忍住恐惧,伸手搭上阿房皓腕。
感受到投在他后背上的寒芒,军医战战兢兢号过脉,又翻起阿房的眼皮看了看,这才哆嗦着跪在嬴政面前,斟酌着如何说才不会惹祸上身,免得这个已经明显失控的暴君迁怒于他。
“启禀王上,这位姑娘是因为寒毒入体,伤了血脉,所以才会昏迷不醒。”
“废话!”一脚将军医踢了两个跟头,嬴政怒骂道。
“只是浇了些冷水,她怎么就成了这副样子?”咬着牙挤出这几个字,嬴政实在想不通。若说她因此染了风寒,高烧不退,他倒是可以理解。可为什么会直接晕倒,气息奄奄?
忍着胸口的闷痛,军医仓皇爬起,不敢再靠近,跪在原地回答:“女子身体与男子不同,生性就属寒凉,其中又有许多生性便畏寒怕冷,这位姑娘看来,便是如此。寒上加寒,所以昏迷不醒。”
听军医这样说,嬴政突然回想起来。这个女人似乎很怕冷,与他共乘一骑时,偶然碰到她的柔荑,总是冰凉的。而在帐中,她总是喜欢凑在暖炉旁,像只猫儿一样蜷成一团。
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早点想到?若是他知道,绝不会如此对她!
可是现在,悔恨和懊恼无济于事。他一定要救她,不惜一切代价。
“快开药方,不管多珍贵的药材都可以,快点救她!”
听到嬴政的怒吼,可怜的军医瑟缩着身子,颤抖着回答:“当务之急,是将她身上的湿衣换掉,用柔软的毯子裹紧,盖上棉被,尽量恢复体温。再开些补气养血的药方,喂她喝下,看能否有效。”
“知道了,你快去吧。”嬴政挥手,让他退下。
军医急忙躬身退出。到了门口,还未来得及拭去冷汗,阴恻恻的声音飘了出来:“若是无效,就杀了你!”
说完,嬴政不再理会差点吓死的军医,转身扶起阿房,除去她身上的纯白狐裘,露出湿淋淋的衣裙……
此时,同样是夜幕笼罩下的旷野,百余人马像黑色的闪电,马蹄翻飞,从远处疾驰而来,又迅速消失在前方的黑暗中。不多时,已经越过韩国边境,沿着通往秦国的必经之路,向大漠进发。
为首一人,俊逸冷漠,眼中却燃烧着足以烧毁一切的炙焰。胯下黑马,颇有灵性,不需主人催促,便四蹄生风,如生双翼。奔跑间,隐隐有血汗渗出,随即被劲风吹干。
“阿房,等我!我这就来救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活着……”
沙漠营帐内,按照军医的交代,嬴政将裹着阿房的银白狐裘打开,露出里面浸湿的衣衫。
手到之处,衣衫层层褪去,很快,阿房便不着寸缕。匀称完美的曲线,毫无保留地展露在嬴政眼前。不反抗,不挣扎,静静地躺在那里,就像是最巧手的工匠用最上乘的羊脂玉雕琢而出,美得让人窒息。
然而,嬴政此刻,对这样旖旎的美景却视若无睹。
他看到的,是阿房白皙光滑、仿如凝脂的肌肤上透出的淡淡青色。纵然有橙黄的炉火映在上面,依然无法驱散那近似死亡的色彩。
指尖传来的冰冷,沿着臂膀迅速蔓延,窜进心脏,又疯狂地涌入血液,最后,凝结成冰,冷得令人战栗。
伸手扯过绒毯,将阿房重新裹好。嬴政的手,难以抑制地颤抖。一不小心,绒毯滑下一角,露出阿房圆润的肩。上面一点朱红,鲜艳绚丽,正是象征贞洁的守宫砂!
“怎么会?”嬴政喃喃出声。她不是苍落尘的宠姬吗?怎么会还是处子之身?苛求完美的他,若是早知道这个事情,定会欣喜,会满足,不再心存芥蒂。
但是,此刻,在嬴政眼中,这个守宫砂已经毫无意义。自从阿房昏死的那一刻,他才猛然惊觉,原来,这个女人对于自己,竟是如此重要。看着她毫无知觉,静静躺在那里的样子,他的心,仿佛被生生剜下一块,血淋淋,牵扯出撕裂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