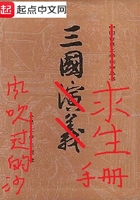在外敌入侵、困难当头的时刻,北大、清华、南开3校能够几经变动,最终在昆明重开教业,确属不易。但3校广大师生在当时时局动荡、物价飞升、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种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费短缺。抗战前,3校的经费来源各不相同。北大的经费完全靠国民党政府支付;南开系私立学校,抗战开始后经费来源枯竭,接受政府部分津贴;清华经费则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以庚款支付,抗战开始不久,庚款停付,清华的经费来源也告中断。这样,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校经费已完全由国库支付。从1937年9月开始,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由,紧缩文教经费,将原核定各国立学校的经费改按7成拨发。临时大学搬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大后,国民党政府则只把7成经费中的四成交给联大,所余3成又以所谓“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为借口,规定全部上缴。联大每年的经费预算数平均为120万元左右,仅及抗战前清华一校的经费额,而这个数额国民党政府还一拖再拖。至于联大的校舍建筑和图书设备所需费用,政府则置之不顾。在三校合并、人员倍增而货币又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联大在经费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经常入不敷出。为了筹措经费,学校当局和一些教授不得不四处奔走,请求援助,同时还得向银行透支和借债。
二是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匮乏。日军侵战北平后,北大的图书、仪器和校具大量被毁,丰富的藏书和珍贵的仪器落入敌手。清华虽提前运出一部分图书、仪器,但在转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损失严重。长沙临大时期,全校仅有中外文图书6000余册。西南联大虽设法搜集购买,但在上海、武汉相继沦陷后,国内来源几近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战香港后,国外图书也只能通过印度孟买购置。由于教育经费有限,无法满足需要。8年中,联大共有中文、日文图书34100册,西文图书13900册,合计不过 48000册。1940年,英国牛津大学赠书1454册。北京图书馆迁至昆明后,也为联大提供了部分图书、期刊。另外还由联大出资将北图战前向国外订购的西文期刊70余箱自香港运至昆明,供联大理、工两院使用。但这些图书资料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尤其是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奇缺,根本不能做到人手一份。因图书量少,学生到图书馆借书,经常要排起长长的队伍,但还是有些学生连一本书也借不到。学生借不到、买不起书籍,就主要靠上课时专心听讲,认真地记笔记来汲取知识,进行学习。
当时的仪器设备也十分简陋缺乏,实验用药品严重不足,以至不得不停止和削减一些实验项目,一些实验性的科学研究也无法进行。工学院由于清华、南开南迁时抢运出一些仪器,还能勉强应付教学的需要。理学院的情况就差多了,北大南迁时,没能运出任何仪器设备,只有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将分光仪的光学部分(三棱镜)带了出来。由美回国的马大猷带回一具低压汞弧灯,于是在附近的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把三棱镜等放在一个简陋的木制架子,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实验。生物系的实验用显微镜太少,只能用切片固定在显微镜上的办法,让学生排队轮流看。化学系只能保证5门课有实验,而且是用自制的泥炉烧木炭来代替煤气炉和电炉。像烧碱、硫酸一类最普通的化学药品还得靠从香港进口,辗转获得。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只能把校舍附近残破不全的碉堡改装成气象台。师生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因陋就简,想尽办法自制或仿制一些实验仪器,坚持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但是,由于仪器设备的精确度太差,很多实验误差大得惊人,只能进行实验方法和步骤的训练,根本不可能由此获得准确的数据和结果。
三是师生的生活条件艰苦。先说教师,从1937年9月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7成发放(以50元为基数,金额按7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所剩寥寥。自1940年起,虽又改为发放全薪,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联大师生已经同广大人民一样,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到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每月薪金已经由战前的300多元降到实值仅合战前的8. 3元,只够维护全家半个月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般职工的生活更是困苦不堪。当时的联大教授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出外兼差。理科的一位教授夜间兼做家庭教师,只是为了换得一餐晚膳,足见其穷困潦倒的程度。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任一专教员,晚上还要在油灯下,埋头为人刻制印章,以换取一家8口的糊口费用;著名哲学家汤用彤等一些教授一度只能食粥度日;梅贻琦吃的经常是白饭拌辣椒,如果吃上了菠菜豆腐汤,就很高兴;吴大猷教授身着大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抡教授穿的鞋子,经常是前后见天。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发放一些诸如平价米贷金、教员奖助金、学术研究补助费等款项,但这种津贴同物价的涨幅相比,则有如杯水车薪,根本于事无补。如1943年发给每个教授的所谓学术研究补助费500元,其实际币值仅折合战前2元左右。即使在这种困窘的生活条件下,大多数教师仍出于责任感,勤勤恳恳地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当然,这种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也难免对联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种种影响。教师因外出兼差,缺课、迟到的现象屡见不鲜;随意合并课程,缩短学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再说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联大的校舍简陋、分散,学生们上课、吃饭、住宿都不在一起。很多学生住的是茅草顶、土墙、泥地的宿舍,灯光昏暗,而且即使是一间很小的茅屋,也要挤住40多人。宿舍里没有书桌,教室中的课桌,很多也是用土基搭上木板,拼凑而成。学生们自学时除了要去抢占图书馆有限的座位外,有的就不得不到街市的茶馆里去看书。有一个时期,由于宿舍和图书馆简陋不堪,每逢6月到8月的雨季,学生们就不得不打着伞睡觉、看书了。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是,“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在昆明屡遭日寇飞机轰炸的那段时间,校舍受到破坏不说,学生上课的时间也被迫改在上午7点至10点,下午3点到6点,两课中间只休息5分钟。一有警报声,就立即停课。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活动。在经济方面,联大学生的状况也是十分困苦的。1940年昆明的物价开始陡涨后,联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虽然享受公费待遇的学生数在逐年增加,但仍有一部分学生与公费无缘。而即使是享有公费的学生,也因物价不断飞涨,实际上仍然达不到温饱水平。学生的伙食费在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到1940年涨到每月200元,1944年涨到每月1000多元,1945年到了五六千元,而在1946年则到了每月伙食费1万元,还是整月尝不到肉味。学生们吃的是用发霉的黑米,加上1/10的谷子、稗子、砂子、泥巴等物的所谓“八宝饭”,菜是不见油和盐的水煮青菜。即便这样,还是不得不把每日的三餐改为两顿。由于学生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于是兼差之风盛行。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约有一半的学生在校外兼差,其中以当中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的最为普遍。也有些学生在商店当伙计、或上街卖报、作邮差。很多学生因为经济无着,兼差负担过重,学习质量难有保证,被迫休学、退学的比比皆是,有的学生时断时续,读了六、七年才可毕业。
四是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统制。抗战期间,陈立夫担任了教育部长,竭力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制度和法西斯的教育统制政策,对学校和师生采取全面的统制干涉办法,严重窒息了学校学术研究的自由气氛,限制了师生的进步活动。西南联大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自然也成为加强统制的重点对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加强对大学生的法西斯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提出要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最高准则”,而这时的三民主义,实际已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联大当局为了贯彻党化教育的方针,除把《三民主义》和《伦理学》定为必修课外,还成立了“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加强对学生的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同时还搞每月一次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由国民党党政要员对学生训话。通过这些名目繁多的党化课目,对学生进行封建的、法西斯的奴化教育。第二,加强对大学课程的统制,“部订”划一科目。1938年9、10月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1939年8月,又颁布了《各院系必修选修科目表》,企图通过划一大学课程的办法,来适应法西斯专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并达到控制学生思想的目的。联大当局基本上是按照“部订”标准实施了全校的共同必修科目的。而对于各系的必修和选修科目,因为广大教师的抵制,并没有完全按照教育部的那一套执行。第三,严格规定考试制度。从1941年起,教育部明令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改为总考制,除本学期课程外,须再通考各学年的主要科目,目的在于使广大学生陷入繁重的复习应试中去。就在这年,联大毕业班的学生组织了“反总考委员会”,反对总考制度。对于学生的抗争,教育部一再密令联大当局,要将学生“开除”或“不予毕业”,压制学生,最后竟发生了迫使联大四年级学生、反总考委员会干事自杀的后果。第四,片面强调培养“实用”人才。注重发展“实科”,而贬低文法科以至理科。这反映在招收学生和派遣公费留学生上,实用科学的比例要大于文理科。而在公费待遇等方面,工科学生也较文理科的学生优厚。这种做法深为广大教师所不满。第五,加强对教师“资格”的控制。1940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以“学术审查”的名义,规定各大学已聘任和准备聘任的教师均须呈报教育部,由教育部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审查、核定其等级,并由教育部发给所谓的审查合格证书。而学校必须依据部定的等级聘任教员。这不但有利于加强国民党对大学生的统制,而且也使他们以审查为借口排挤、打击进步教师。联大教授对这种“资格审查”曾强烈反对,拒绝填表上报,结果教育部竟蛮横地扣发了这一年的学术研究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