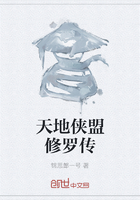薛逸尘见仲云神色有异,颇为沮然,心中不明其理,忍不住出言问道:“我看小友一人流落至此,也无甚么依靠,可是路中遇到麻烦之事?”顿了顿又道:“若是有人恃强用武,欺负了你,大可不必如此,老夫亲自出手,替你教训教训那人也便罢了。”薛逸尘武功极高,早已臻入化境,自是不再与人随便动武,但他从来嫉恶如仇,平生最忿仗势凌人,一见仲云这般,急于仲云半晌不答话,只得瞎猜乱蒙,毫无事理根据。
仲云苦笑着摇摇头道:“不是。”踱了数步,猛地念起木离霜容颜,仿佛就在眼前,似幻似真,瞧了一会儿,倏地又消散而去,一时悲痛万分,这份情感在心中压抑许久,终于如江潮大浪般喷涌而出,他感激薛逸尘救了自己性命,当即坐下身来,便捡了些重要的,将这几年的遭遇一一娓娓道来。
待得言毕,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四五个时辰,此时天微微发亮,一缕光线穿过石缝照入洞中,洞中一切事物被照得清清楚楚。烛光熄灭,余烟袅袅而上,流露出稍许萧索。仲云讲了一夜,也不知疲倦,陡然间把这几个月以来沉浸在心底的言语一股脑的说完,竟是格外的痛快,却又觉若有所失,恍惚才明白了故人已去,再也无从陪伴左右,而这一切与自己万万脱离不了干系,更是陷入深深自责之中,感慨万千,眼睛一酸,忽的放声痛哭。
仲云自从义父被害,流落江湖以后,虽遇到重重困难,却也没有如今日这样哭过,薛逸尘听得仔细,胸中一结亦不由为之牵动,默默叹了口气,等到仲云哭声渐息,哈哈大笑道:“原来是为情所困,确是身不由己,眼见心爱之人离去,恨不能挽回,哭一场又有甚干系。”薛逸尘一语道尽,兀自仰天长笑,笑声中含着几分凄怆之意,笑音刚落,竟也抑制不住,伏在地上埋头便哭,登时老泪纵横,哽咽之极。仲云心下大奇,收住泪水嘀咕道:“这老头好生奇怪,我失去霜妹,哭一哭也就罢了,他又有什么伤心之事?再者已经这么大年岁,武功高强至斯,什么事情还能看不开么?”越想越是犯疑,但见他哭得伤心,又不好出言打断,于是干脆坐在一旁,瞑目凝神,忽然念头一转,心想:“是了,以前在金陵之时,躲在那个井下,曾听王前辈说过这一段往事,薛逸尘练成绝世神功形物术后,重新奔回纵物门中,虽然杀死了孙仁,却也误将心爱之人孙芸杀了,此后他有时疯癫,有时正常,想必便是因为此事对他打击甚重。”
暗道:“我把这些年经历全部说出,触及‘情’字,自然会惹得薛前辈神伤一番,薛前辈听之竟丝毫不顾及面子,一哭一笑完全是性情使然,不存半点做作,比我们这些人强出甚多了。”想到这里,不禁对薛逸尘又佩服了一分。
二人彼此心交,蓦然契合,对对方均生出几许好感,薛逸尘拭尽眼泪,笑道:“痛快,痛快,老夫今日遇见了你,实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仲云正欲说话,又听薛逸尘道:“小友,你瞧老夫这一身武艺,怎么样?”仲云道:“薛前辈武功高超,早已胜过当今世上高手,比之先贤,自也不遑多让,在下钦佩万分。”仲云心性本高,很少对人歆慕,他与薛逸尘交手几次,皆是败退,这句话说得倒是认真。薛逸尘点点头道:“老夫自天山出来后,早就看厌了这世间争执,是以一个人漂泊四处,潜心修习武功,直至今日,武功方有所成就。我看小友武功极好,老夫一人独来独往,亦是寂寞的紧。不若小友留在此地,与老夫共同研习武学之道,岂不比在外面的花花世界闯荡要好得多?”
仲云听他言语诚挚,心下感动,忖道:“霜妹已去,世事也再没有任何牵挂,薛前辈说的不错,我不如留在此地,随他苦心修习武艺,几年之后,指不定会忘记失去霜妹之痛。”便道:“如此甚好,晚辈遵从便了。”薛逸尘拊掌大笑道:“少年人能耐得住寂寞,陪一个老头在此,也是不易。”说罢,转身飘然而去,仲云站起来欲要跟上,只觉胸口一阵剧痛,浑身上下酸楚难当,直如散架一般,只得又坐回原处。
不消多时,薛逸尘又折了回来,仲云定睛一看,顿时怔了怔,原来薛逸尘并非空手而归,在他手上凭空多出了两头狼,那两头狼双目圆瞪,神情狰狞可怖,犹自咆哮着喘气,却被薛逸尘牢牢抓住颈部,无论怎么挣扎都是动弹不得。
薛逸尘笑道:“昨夜你被狼群围攻,老夫即便手刃了这两头畜生,替你出口恶气。”双臂一振,可怜那两头狼叫也没来得及叫,就让薛逸尘雄浑内力震得五脏俱裂而死。二人当即将狼皮剥了,捡些干柴升起了一堆火,用木棍串上狼肉,放在其上烤着,不一会儿便喷香四溢,仲云一路上饮露止渴,拔草充饥,全仗着内功深厚坚持到现今,很久未能吃过像样餐饭。如今闻着香气扑鼻,早就忍耐不住,不顾烫手,抓起来便大口嚼咽,片刻,两头狼肉就被二人吃得一干二净。
仲云体力渐复,双腿盘坐,默运内功,初时方觉无异,哪料越到后来,越觉真气无法凝聚,只一提气,真气上升至“鸠尾穴”处,即四下溃散,乱冲乱撞,好似体内有两股力道,相互之间并不融合,仲云试了几次,均告无功。薛逸尘早先救他之时,已经知道此番情况,叹了声道:“你体内这两股真气,绝不是出于同一气脉,以前还能相安无事,但你大悲之后,这两股真气不受控制,肆意横冲直撞,各处交锋,若不早些束缚住这两股真气,只怕日后祸患无穷。轻则四肢残废,武功尽失,重则性命难保。”
仲云听得黯然,寻思道:“这必是红绸果花香之毒复发,那时侥幸躲过一劫,武功因此大进,它现在又来报复我啦。”心如死灰道:“人不免一死,早死晚死,不是一样么?”薛逸尘哼了声道:“此言差矣。你小子年纪轻轻,日后大有作为,这般不明不白的死了,岂不可惜?”接着道:“你体内这两股劲力恁地古怪异常,时而聚合,时而分散,以老夫之能,也只可抑住其中一股劲力,至于另一股劲力,便要靠你自己了。”仲云心知体内的两股劲力中一股为杨绾君所赐,即红绸果花香之毒。在渊山庄炼毒有方,杨绾君更是其中的炼毒大家,剧毒进入体内后,长期盘桓在胸腹之间,一直抑制自己的内力。倘不是阴差阳错,利用水流劲力冲开了剧毒,现今怕是早已命赴黄泉。此间剧毒化为内力,与本身内力相抗,情形愈发的凶险,如不想出良策,终究难逃此劫。
待了片刻,仲云定了定心神,道:“怎样靠我自己?”薛逸尘道:“再简单不过,老夫传你上乘内功心法,你以力制力,兴许能抑制住另一股劲力,之后再将二者调和一处,武学修为还可再攀一层。”仲云摇摇头道:“不妥不妥。”薛逸尘怒道:“有何不妥,只有这个办法,你小子尚可留下一条命。”仲云长叹一声,便将自己如何中毒,又如何学得“混阳孑行功”以图解救,一一给薛逸尘说了。薛逸尘不屑道:“赵独鹤是何人?他所传的内功心法能和老夫的比么?”
仲云心神一动,他晓得薛逸尘武功乃是另辟蹊径,最终才得大成,或许还真有其他法子,能令他摆脱体内之毒。正想着,但听薛逸尘道:“你体内之毒奇特怪异,已形成内力与本身内力相互压制,如想将其除去,只得顺其自然,慢慢消解。老夫这套功法,能连通体内十四条经脉,每条经脉都有其独到练习之法,待得练成之时,功力自当大增,除你体内之毒,也是容易之举。”
薛逸尘话音未落,只见仲云忽然跪下,叩首道:“不论成与不成,先谢过前辈。”薛逸尘单掌托起仲云道:“朝我磕头做什么?老夫又不是你师父,若你真有诚意,也得向老夫这内功心法磕头,哈哈。”仲云笑了笑道:“不知前辈这门功夫从何而来?”刚一说完,就觉不妥,急忙改口道:“晚辈失言,这定当为前辈自行创立的了。”薛逸尘负手道:“非也非也,小子,你第一句话问的不错,这门功夫绝非老夫创立,乃是从他处‘借’来的。”仲云“哦”了一声,心里疑惑道:“薛前辈此人极为自负,他此时武功天下无敌,断然不会在自己面前提起其他武学,除非这门功法确有独到之处。”一念未绝,又听薛逸尘道:“这门内功心法颇为高深,老夫领悟得十之七八,你可知这门功法老夫是从何处得到的么?”仲云摇头不知。薛逸尘见仲云眼中尽是疑惑,笑道:“这门内功心法正是名动天下的‘纵物门的秘密’!”
此语一毕,仲云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苦心追寻的纵物门的秘密居然还在薛逸尘手中,更没想到的是纵物门的秘密却是一门高深的内功心法。仲云正自惊讶,但瞧薛逸尘来回走了几步,皱眉道:“只惜这门内功心法老夫未能全部掌握,否则驱逐出你体内之毒就是十拿九稳了。”
仲云淡淡一笑道:“万事强求不得,保住性命是福,丢了命也怨不了别人。”薛逸尘面色含愠,道:“有老夫在,还怕你小子活不了么?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练。”顿了顿道:“这套内功心法分为四章,分别是:定神,凝气,返璞,化相。自‘凝气’章始,分别有通连十二经脉独特之道,至‘化相’章方能化去原来本相,达到水乳交融,无所不欲的最高境界,一章较一章深奥,老夫练得零零落落,也花去了七八年的功夫。”仲云只觉这些章目的名字分外熟悉,却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转念又问道:“薛前辈,晚辈曾听人说,这纵物门的秘密先前确实在薛前辈手中,但后来让武林派盟主仲……仲平抢走,前辈怎地还有这门内功心法?”
薛逸尘眼中忽然精光暴涨,直射仲云,徐徐缓和下来,道:“蠢材蠢材,老夫就不能事先记住么?休要多言,且听我念给你口诀。”仲云顿时醒悟,不敢再多话,不想薛逸尘第一句方出口,仲云就险些惊得跳起身,原来这口诀不是别的,正是仲云在幻潭石壁上所见到的内功心法。仲云不由胡乱寻思起来,登时一团团迷雾浮现在脑海中,半晌挥之不去:“这纵物门的秘密为何会出现在幻谭的石壁上,母亲的骸骨又为何会在那里?母亲身边死的那个女子又是谁?”思索良久,只感一片混乱,没有半点眉目,不觉已然过去半个时辰,薛逸尘所念的内功口诀,自己倒是一句也未能记住。
薛逸尘见仲云神思外游,心头不快,咳了声道:“小子,你记住多少了?”仲云一怔,恍然回过神来,断断续续道:“只记住一小半……”薛逸尘冷冷道:“老夫再念一遍,你且听好了。”于是又张口念出,仲云听了几句,不由想到他处:“不错,这正是幻潭石壁上所刻的内功心法,但幻潭石壁上仅有‘定神、凝气、返璞三章,为何没有最后一章呢?”忽而心念电闪:“听师父苏忘机曾说,父亲一度心性大变,把他和周旷一齐扫地出门。除了防止他二人偷盗纵物门的秘密,只怕还有其他缘故。父亲一直好好地,怎么会突然心性大变?”转瞬想到了薛逸尘之前对他说的话:“习武之人,最怕便是运功时出现杂念……”陡然明白了些:“定然是父亲练功时出现杂念,导致气血不顺,从而心性亦是与以前大相径庭,但父亲身为武林派盟主,武功修为自是在寻常高手之上,怎会不明白此等道理?”又寻思许久,蓦地清楚了:“父亲练功必然是心无旁骛,那问题只能出在这门内功心法上,抑或是父亲修炼这门心法时受到阻滞,薛前辈说,这门心法极其艰深,里面一些问题连他自己都解答不出,父亲怎么能想出?”
正预备接着想下去,忽听薛逸尘怒道:“又想些其他事情了罢?我且问你,老夫念了两遍,你记住多少?”仲云甚感歉仄,脸上发烫,须臾不语。薛逸尘眼睛一闭,不满道:“孺子不可教也!”亦不多话,又念了一遍,这回仲云不敢大意,一字一字认真听取,他天生聪慧,记忆甚佳,这一遍念完,竟记了个八成有余。薛逸尘检验一遍,见仲云记性极好,自是喜上眉梢,道:“你这小子不肯下功,还好记性不赖,若是再用功些,只消五六年光景,便可领会个大概了。”仲云连连称是。
薛逸尘当即一句一句解释给仲云听,教他从“定神”章开始练起,仲云先前在幻潭时曾经习练过,领悟起来也是异常的快,仅过了几个时辰,就练完了“定神”全章。薛逸尘瞧仲云练得这般神速,也颇为惊讶,心中立时生出爱才之念,点头道:“小子领悟不错,倒省了老夫许多事情,依照这个速度,只用一年时间,你就可以掌握大概了。”仲云连声道谢,更是不敢懈怠,一晃过去了半年光景,仲云白天随着薛逸尘一起练习,至了黄昏时分就出去打些野味,二人大快朵颐,说也奇怪,仲云体内紊乱真气逐渐调序,慢慢有生蓬之相,仲云自然晓得是修炼内功心法的缘故,从此愈加勤奋练习,他根基极好,又加上天资聪颖,转瞬已练过十条脉络,进入最后一章“化相”,此时仲云只感身体百骸俱轻,殊不知武功修为已在不察觉中大有增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