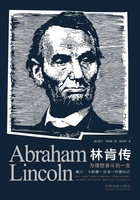他清楚地记得,从上海到青岛的客运船,全是“自”字打头的,叫“自力”、“自更”、“自生”、“自奋”、“自发”、“自图”、“自强”,联起来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毛主席语录。
鲁祥云回到家后,父母才知道他上了广州。看到儿子平安回来了,父母吊着的心放下了,只是说了他两句,叫他今后出门跟家里打声招呼,免得家里人焦急。
其实鲁祥云看得出来,父母都为他能贩回这么多上海手表来高兴,夸他有本事。手表很快出手了,挣了两千多块钱,用这些钱给二弟盖了四间大瓦房。到这个时候,鲁祥云才真正觉得在朱留街上,他可以抬起头来扬眉吐气了。
瞄准市场巧经营
手表让鲁祥云挣了大钱尝到了甜头,那时一个农村整劳动力,累死累活干一年,好的生产队年底能开个三四百元钱的支,差的也就是一二百元,他一趟南下,跟上一个整劳力挣十年,这钱来得多快。
同时,他也从手表上看到了农村市场的广阔前景,只要有东西,不管好的坏的,大家都要。从此,他的思想完全进入了正规的商业模式,一门心思搞经商。手表虽然赚得大,但风险也很大,一旦出了事,就要赔个大的。他经过考察就改做尼龙布的生意。从广州贩尼龙布也能挣大钱,一米尼龙布贩回来就赚六元钱。
鲁祥云做了两个大袋子,拿着个小扁担,到广州去,把袋子装满了货,用小扁担挑着,上火车,坐轮船,正式做起了“二郎神”的买卖。后来,他发现不用上广州了,上海这些地方也有了,虽然贵,但方便,省路省时间,成本杀下来并不高。
一次南下,就能挣一个整劳力一两年的收入,这样让人眼热的事,为什么只有鲁祥云才干,别人不能做?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磨练和经历,给了鲁祥云这样的机遇和胆量。
当时,放开搞活刚刚风生水起,信息的流通与传递,很大一部分还是广播和口头相传,商业信息的滞塞和农村的封闭,使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经商的大利,即使知道了,这些从来没有出过朱留村、蛇窝泊公社一亩三分地的人们,很多人连火车轮船都不知道为何物。
曾经有个故事说,一位老农到城市一亲戚家去,看到了火车。回来后,就在村里人面前显摆自己的见识说:“我看到了一个大家伙,躺着跑,比兔子还快,要是站起来跑哇,骑着马也赶不上它。”那时,乡下人,不知道大城市里面的人都是啥“精怪”,就是有做买卖这个“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
鲁祥云在“战山河综合商店”里是闯荡过“江湖”的,他有这个胆量,也有超人的见识和眼光。他贩了几天尼龙布,就想出了新道道:“卖尼龙布挣钱,把尼龙布做成衣裳卖,不是更挣钱吗?”他家里有台缝纫机,就叫母亲把尼龙布做成裤子。从卖原料到卖成品,附加值翻了一番多。
朱留赶集的时候,鲁祥云叫他弟弟把裤子搭在胳膊上,在大街上边走边说:“裤子,裤子!”那个卖方市场的年代里,根本不用喊,只要轻轻地说,人们就会疯抢疯夺地买。
钱如潮水一般往家涌,鲁先生害怕了,不叫干。鲁先生训他说:“祥云啊,你这个小子不长记性,忘了挨整那个事了?”
鲁祥云虽然吃过“文革”的苦头,也知道自己家的成分不能太过火,但是他觉得邓小平既然搞改革开放,就不会是假的。
鲁祥云心里不服父亲的说词,口里不说,心里暗暗地较劲:不叫贩尼龙布,不叫做衣裳卖,我就找个别的事做,反正挣钱发财做买卖的事,我这辈子干定了,谁也别想拦住我。
棍棒打不断梦想路
现在说来既是悲哀也是笑话,文化大革命讲两条路线的斗争,那时,鲁祥云跟他父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都是受尽了大苦的人。但他们不是党内的,是党外的“阶级斗争”的受害者;而这个时候,爷儿俩竟然真的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爷儿俩之间的这场路线斗争是什么呢,竟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较量,但其表现形式不是“文革”的批判,而是家规的整治。鲁祥云想的是发家致富,鲁先生怕的是发家致富,针锋相对,冲突怎么会不发生呢?
果然,战火终于燃起来了。
鲁祥云天天支着个耳朵打听哪里有发财的消息,也是命该家中发生一场战斗。
当时到银行很容易就能贷到款,只要你去说要贷款,他就贷给你。有些有胆量的就到银行贷款做买卖,卖东西做老板。
鲁祥云打听到栖霞有个人从银行里贷款买了辆大客车,线路是从栖霞跑青岛,可是没有人敢开,也没有人经营,就把车放在家里。他一看就是个好买卖,就兴冲冲地跑到栖霞,跟人家谈了承包的价钱,签了合同,就找人把大客车开回了朱留村。
鲁先生在“药铺”里,听着满街嚷嚷说村里弄了辆大客篷,再上栖霞上青岛不用发愁了,在咱村坐车就行了。鲁先生听了心里也挺高兴的。后来有个近支的叔跟鲁先生说:“这辆车不是大队的,是祥云弄来的,你快去看看吧。”
鲁先生一听,头嗡的一声,刚才的高兴劲早飞到九霄云外了,心里就没好气:“这个熊孩子,你不叫他干这样他干那样,越弄越大,不想过了?”鲁先生跑到村东头,看见崭新的大客篷停在那里,大人孩子围着看热闹,鲁祥云也得意洋洋地跟大家高兴地说着什么。他二话没说,扭头就回了“药铺”,把摊子收拾收拾,病也不看了,闷着头回了家,找了根棒子放在房门后,等着鲁祥云来家算账。
傍晚,鲁祥云兴冲冲地回了家,看见父亲的脸阴沉沉的,就觉得有什么事情让父亲上火了,上前问父亲有什么事。鲁先生爱搭理不搭理地说,等吃了晚饭再说吧。饭桌上,气氛很凝重,鲁先生不吭声,全家谁也不多说什么。
鲁祥云盘算着,父亲脸竖鼻子,很可能是为自己承包大客篷的事。他预料饭后必要论讲,就在心里打算着怎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支持自己的做法。他想,自己不是小孩子了,按照年龄算,也该娶媳妇自己成家立业过日子了。父亲总得让自己把这个事做下来挣两个钱成个家吧。如果父亲不听劝,他就自己管着这辆车,自己挣钱娶媳妇,不用家里再操心不就行了。
鲁祥云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可是世界上的事不是都照着自己打算的道儿走。吃过晚饭,母亲把碗筷拾掇下去后,鲁先生就开腔了,他压着火气故意装着温和地说:“祥云,咱爷儿俩商量个事来。”
鲁祥云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就说:“爸,你是不是说客车的事?这个事我没跟您商量,是我不对。不过这个事赚钱……”
“你还知道跟我商量啊?你现在大了,翅膀硬了,还用跟我商量啊?”没等鲁祥云说完,鲁先生就连珠炮般地训上了,“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光知道钱啊钱啊的,我没有你这么个儿!”
说着,起身从门后拿出准备的棍子来,照着鲁祥云的后脊梁上就是一棍。鲁祥云一看不好,一转身到了院子里。
鲁家有个规矩,长辈打后辈,后辈不能躲。鲁祥云这一躲不要紧,本来在气头上的鲁玉明火冒三丈,紧接着就跟到院子里:“还反了你不成?你还敢以小反上啊?”拿着棍子就没头没脑地往鲁祥云身上打。
鲁祥云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在家里哭。--因为鲁家还有家规:父母管孩子,不管是谁都不能上来拦阻,父亲管,母亲不能拦,母亲管,父亲不能拦,后辈的更不能拦,也不能说情;只有长一辈的才能出来干涉说情。这种封建家规的原意是好的,就是不要一个管一个宠着,那样永远也管不好孩子。“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古训,在鲁家也另有“创新”,不管是儿女还是妻子,有做得不合“当家的”心意的地方,从不在人眼前说教,直等到家里没人了,才管教说理。
当然,打鲁祥云也是家法的一种,就是棍棒教育。家法一般不用,不是屡教不改实在让老家上火了,老家是不忍心打的。--且说鲁祥云看到父亲动了真火,知道跑也没有用,躲也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是不让父亲打着头,就把头往鸡窝里一钻,露着个屁股让父亲打。
这种“大山上的野鸡顾头不顾尾”的做法,让鲁先生心里更火。他把棍子一扔,一只手把鲁祥云从里面揪出来,不管鼻子脸的就拳打脚踢,几下子打得鲁祥云满地打滚。
鲁先生边打边骂,鲁祥云抱着头直哀求:“我不敢了爸,我不敢了爸,不敢了还不行吗?”打得鲁祥云满地找牙。
鲁祥云被打得躺在地上直哭,没有一点反抗的劲儿了,鲁先生的火气略消了,但他不软和,照着他后腚踢了一脚说:“起来,起来,来家好好说说,再听不听话了?”
鲁祥云从地上爬起来,抹抹嘴角上的血,浑身七痛八痒地跟着鲁先生进了屋,先是赔不是,然后表态说:“你不用生这么大气,爸,这事全是我不对。我知道你是为我好,知道你为我担心,我以后不管再做什么事,都跟你商议,你说做咱再做,你说不做,我就不做。”
鲁先生看看把儿子打到这个样子,心里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教训的口气也软了几分:“你说说,祥云啊,你也不是个小孩子了,什么事你不懂,当老家的能往沟里领你吗?你光看见钱,钱能救你的命啊?”
他又说:“跟你说了一遭又一遭,你就不往心里去,还越弄越大。以前偷偷摸摸地卖个服装,还不上眼;你现在弄个大客车来家跑运输,不光咱村人知道,全公社很快就响了盘子了,你想找死啊?”
鲁祥云见父亲的气消了,忍着痛跟父亲说:“爸,我看这个事不要紧,我们承包人家的车,如果要挨整,他们先得去整车主,不能先整咱。”
一句话把鲁先生的火又点起来了,他大着嗓门吓唬说:“你是吃一千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你可别忘了,咱跟人家不一样,人家贫雇农干了,什么事都没有,咱家可是什么成分?”
鲁祥云想想也是,父亲“文革”受了多大的磨难,如果有一天真像他说的那么样,自己做的事,不是给家庭添祸害吗?再说,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等父亲气消了再慢慢说清楚,或许也会叫自己干。想到这里,他对父亲说:“你不用生气了爸,跟人家签了合同,要把车退回去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就跟人家商量退回去。”
鲁先生见儿子软和下来听自己的话,也就作罢,进了西屋。过了一会儿,二弟过来说:“爸爸妈妈两个在西屋哭,说是打你打得真不该。”鲁祥云知道爸爸后悔,也知道爸妈是没办法。心里想着父母不容易,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这一夜,全家人的心都在苦海里浸泡着,直到鸡叫了,鲁祥云才闭了会儿眼。
第二天早上,鲁先生对祥云说:“夜来说的车的事,这几天赶快退回去吧,免得夜长梦多,树大招风,叫人找上来抖擞不下来。”
鲁祥云见大客车实在是留不下了,不得已回了栖霞,费了好大事,把车给退回去了。望着大客车卷起一溜烟尘顺着大道往北驶去,渐行渐远,鲁祥云的心都碎了。他从心里感到自己的梦在一点点地破碎着,心也破碎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眼里有了泪花。
果不出他所料,后来,承包的人赚了大钱。“那是人家挣的钱,不是咱挣的钱。”鲁祥云每当回顾起这事的时候,脸上就带着无奈的惋惜说:“算咱没有这块财运吧。”
理想之火真的熄灭了吗?梦想真的破灭了吗?鲁祥云没有放弃,他在默默地等待,他在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就是社会发展的大势,他知道,社会这样发展下去,父亲早晚会不再害怕,当他不害怕了的时候,他一定会鼓励自己成就梦想。同时,他还想,父亲说的也对,开大客篷跑运输目标太大,不如慢慢地找个不起眼的发财项目做起来……
春风沉醉的晚上,月上柳梢头,鲁祥云的理想之梦再一次飞翔在畅想与憧憬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