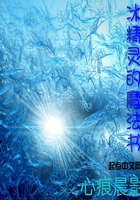男孩身上光溜溜,没有自己的皮毛,又丢了鹿皮衣服。
男孩走得很艰难,赤条条的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眼泪在脸上冻成冰,又有泪水顺着冰凌往下流。
走着,摔着,摔着,走着,男孩的腰就不由自主弯下来,两只手就自然而然落了地。四只脚比两只脚多了一倍支撑,就能少摔几个跟斗,弯下腰比直起腰少了一半高度,就能少招一点风。
但是,男孩还是追不上花熊,男孩只有五岁啊,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程。
走不动的时候,男孩就使出看家本领,让哭声在平原上震荡,让始祖母放慢脚步。
男孩毕竟是智人了,哭着,走着,想着,就有了主意。当始祖母用舌头温暖他的时候,一翻身,就抱住了始祖母的脖子,一抬腿,就趴到了始祖母的背上。
男孩重量轻,始祖母驮得动,男孩身子软,始祖母还觉得挺舒服。更重要的是,这样就不用走走停停,加快了速度。
就这样,广袤萧条的平原,一点点遁去,跌宕起伏的太行山脉,一点点升起。
山路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掉下万丈深渊。山路崎岖,累死累活,也走不了多少距离。可是山路旁有山崖山洞,又能让他们避雪挡风。
现在,这支小小的队伍,就正在太行山脉的山洞里,休养生息。
始祖母瘦了,没有了滚圆的肩胛,鼓胀的腰身,粗壮的腿,只有一副两米五的骨架,挑起一张黑白的皮。
小雌猫瘦了,半年的光阴,看不出身子变长,也看不出腿脚长粗,只有一条条的肋骨,清晰可数。
小男孩也瘦了,眼睛更大,眉骨更高,两只小手像鸡爪,两条细腿像竹竿。
不过,瘦归瘦,经过半年的冰雪打磨,大家都变得更能忍饥耐寒,更能抵抗苦难了。
现在,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了,一个个昏昏沉沉,卧在地上,靠着石壁。
始祖母曾一天又一天地出外觅食,又一次一次的空手而归。
白茫茫的天地,没有飞鸟,没有走兽,甚至没有一株草,一棵树。年复一年的严寒中,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都死了。
山洞里有一堆灰烬,是南撤的智人留下的,也许是十年百年千年以前。
石壁上有横七竖八的爪印,是为了抓吃上面的草根,也许是人也许是兽。
但是,今天,当一切活的和死的都不复存在,当一切吃的喝的都无影无踪,他们到哪里去寻求一条生路?
在极度的饥饿中,始祖母的眼睛发出两道绿光,在幽暗的山洞里移动着,扫描着,一遍,又一遍,终于停在了小男孩的身上。
男孩惊恐地睁大眼睛,他想放声痛哭,却发出一声尖叫。
绿色的目光抖了一下,从男孩的身上移开,继续在幽暗的山洞里扫描。
男孩坐不住了,颤抖的手撑着,细弱的腿蹬着,拼命地向洞口爬去。
当两道绿色的目光重新扫过来时,男孩就连滚带爬地出了山洞。
男孩默默地哭了,对着苍天,对着大山,对着自己瘦小的身体。
整整半年,男孩跟着始祖母一起走,一起吃,一起睡,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但是,就在刚才的一瞬间,男孩突然长大了,懂事了,独立了。
男孩用手背抹去冰冷的眼泪,四手四脚往前爬,前后左右到处看,在那个快要冻僵的小脑袋里,只装着一个念头:
吃的,吃的,吃的……
男孩在始祖母的背上趴惯了,自己走就会摔跟头。不过,现在的男孩长大了,懂事了,独立了。所以,摔疼了,也不哭,摔伤了,也不叫,舌头舔一舔,小手揉一揉,接着走,接着找。
摔到99个跟斗时,男孩的肚脐眼扎破了,流血了,男孩终于掉泪了。
就在这时,男孩发现,扎痛他的是一根树枝,还顶着两片树叶。
吃的!吃的!
男孩忘了肚子疼,抓起树叶就往嘴里塞。可是,树叶就像两块冰,掉进肚子就化了。
树枝插在雪地里,男孩就跪到地上,用手刨。
刨啊刨,又有了两片树叶子!刨啊刨,树枝下面露出了剑齿象的鼻子,鼻头上面就有了灰色的肉球。
男孩握住树枝,用力摇,用力拔,差点搓掉了皮。
男孩含住肉球,用力啃,用力咬,差点硌掉了牙。
男孩想到了火,在周口店的葫芦洞,男人女人用火去烧化坚硬的冰,用火去烧软硬邦邦的肉。但是,葫芦洞里的篝火和男人女人们一起,埋在大山的肚子里了,想也是白想。
男孩想到了石头,在周口店的葫芦洞,男人女人们捡来尖利的小石头,又在大石头上磨得更锋利,绑在树枝上杀猎物,捏在手里剥兽皮。但是,这里到处都覆盖着冰雪,根本没石头。
突然,男孩想到了山洞里的花熊,想到了她们又尖又利的牙齿和爪子。男孩眼睛放光了,连走带摔回山洞。
“花熊--”
“花熊--”
男孩一边走一边喊,两只花熊就来到了山洞口。
“大象--”
“大象--”
男孩挥舞着手里的树枝使劲喊,两个奄奄一息的生命,趴在地上就是不动。
男孩在雪地里使劲跳,就跳出了一个好办法。
男孩走近小花熊,举起树枝敲脑袋,一下,你不动,两下,你不起,三下四下,起来了,男孩扭头就开跑。
男孩跑,花熊追,一追就追到了山坡下,一看就看见了象鼻子。
奄奄一息的生命,立刻有了力气,暗绿色的目光立刻变得雪亮。始祖母和小雌猫有八副利爪,两对利齿,刨开坚冰,撕裂象皮,只是时间问题。
粗壮的象鼻子和庞大的象头被刨出来了,还有两根惨白的象牙。
触到象牙时,始祖母犹豫了片刻。那两根寒光凛凛的剑齿,曾经是让一切猛兽,也包括自己,望而生畏的武器。现在,却因为主人的死亡,失去了尊严,也失去了保护主人的能力,静静地,哀哀地,躺在那里,听凭侵犯,任由宰割。始祖母的黑眼睛里闪过一道悲伤的涟漪。
那是一只成年的雌象。当天气没有变冷,树木还很葱茏时,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曾有过无数只雌象,率领着七八只,十几只,大象和小象,在森林里漫步,在溪水里打滚,在草地上进食。没有谁去打搅他们,不论是飞扬跋扈的大熊猫,横冲直撞的黑熊,钻来钻去的鬣狗,还是成群结队的豺狼。
没有谁会招惹他们,因为他们的体形太大了,大得让一切猛兽望洋兴叹。他们的剑齿太威武了,威武得让一切尖牙利齿自惭形秽。
然而,曾几何时,正是身体太巨大,才不堪食物的短缺,也正是剑齿的威武,才不堪沉重的负担。才成为冰天雪地里,最早牺牲的物种。
死者死矣,生者还要继续。浓厚的伤感和忧郁,并没有阻止始祖母的饥肠辘辘,也没有挡住她的尖爪利齿。
剑齿象的鼻子和头颅被无情地撕裂了,抓碎了,一块,一块,又一块地,滚进了始祖母的肚皮,也塞满了小雌猫和男孩的嘴巴。
喜出望外,大快朵颐,男孩的脸上有了笑容,小雌猫的肚皮鼓了起来,再看那始祖母,正昂首挺立,傲雪迎风。
饱餐一顿之后,始祖母没有把剩下的食物带走。剑齿象的身体太大,大到无法一次刨出来。再说,这方圆几十里,没有走兽,没有飞鸟,甚至没有一只蚊蝇,又何必搬回山洞呢?累了,回山洞休息,饿了,来这里进餐,不是更合理,更省力?
但是,还是会有想不到的事情。
当三个填饱了肚皮,养足了精神的幸运者离去后,一只小黑熊出现了,一只三岁的小雌雄,就住在旁边的山洞里。一个月前,她的母亲老黑熊出去觅食,从此就没有回来。孤独的小黑熊在山洞里苦苦地等待,悲哀地呜咽。由于饥饿,她也曾走出山洞去寻觅。但是,得到的只有凄凉和失望。她还太小,不懂得失去母亲之后,应该继续往南走。她就那样孤苦伶仃地待在山洞里,消耗着瘦弱的身体,释放着幼小的生命。
就在弥留之际,她听到了生命的声音,是那个男孩的叫喊声。还有比这更亲切更有召唤力的声音吗?小黑熊睁开眼睛,把自己的半个灵魂,从地狱里拽出来,恢复了清醒。
拖着皮包骨的身体,小黑熊爬到山洞口,恰好看到生命们正在大吃大嚼。口水顺着嘴角流淌,可她却不敢走出山洞。她是在南迁的途中出生的,没见过熊猫和智人。
对异类的恐惧在阻挡,对食物的渴望在推动,小黑熊就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直到始祖母他们离去。
怯生生,颤巍巍,左顾右盼,小黑熊终于走出了山洞,尽管她也没见过剑齿象,却一点也不惧怕。因为她已经死了。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谁,不论有多么威猛,一旦失去生命,也就失去了一切。
小黑熊很快就吃饱了,有了精神,有了力气,也有了天真,就直立起来,哼哼着舞曲,一圈,一圈,又一圈地旋转起来。她的胸前,就亮出一弯白色的月亮。
3天,5天,3个相依为命和一个幼小胆怯的生灵,分享着剑齿象的牺牲。
10天,20天,再丰盛的大餐也有用完的时候,换来的却是四个幸存者的身体健壮,生存信心。
艰难的始祖母的身子圆滚滚地鼓起来,又有了天神威风。
小雌猫长大了,竹笋拔节似的,把那半年的损失补了回来,尽管算年龄,她还是只亚成体,但是饥寒交迫的历练,天赐美食的满足,使她早熟,也有了天之骄子的神气。
小男孩也高了胖了,塌陷下去的腮帮子鼓起来,撑起一张圆脸蛋,乌溜溜的大眼睛,闪烁着自信和坚定。那根从象鼻子里拔出的树枝,始终握在手里,白天,是拐棍,晚上,是伙伴。
抱着那根树枝入睡的男孩,作了很多梦。有噩梦,也有美梦,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艰难的始祖母,小雌猫,还有一只怯生生的小黑熊。
几天前,男孩就发现了那只小黑熊。黄昏时,他到山洞外去撒尿,就看见她在吃象肉。他没有赶走她,也没有惊动她,只是悄悄地看。小黑熊又香又甜的吃相,让他看到了自己,小黑熊天真无邪的舞蹈,又牵出了他的笑容。毕竟,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让人开心的事太少了。
剑齿象被吃完的第二天,始祖母就决定开拔了,趁着身强力壮,也趁着好天气。他们还要走很远的路程,还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
还是老规矩,始祖母开路,小雌猫居中,小男孩断后。只是男孩身上多了三件宝贝:
一块结实的象皮,绑在腰间,是挡风保暖的皮衣。
一个灰色的肉球,吊在胸前,是逢凶化吉的护身符。
一根磨光的树枝,握在手里,则是能带来好运气的魔棍。
所以,这一次,男孩不用趴在始祖母的身上了,自己也能走,还一边走一边回头,挥一挥魔棍,晃一晃护身符,扯起嗓子喊几声。
小雌猫被男孩喊蒙了,也不断回头,看看男孩,看看远山,不知道是谁出了问题。
只有男孩才知道,他是在喊那只小黑熊。剑齿象吃完了,他们3个也走了,小黑熊留在这里多可怜,多孤单。
终于,天真的小黑熊出现了,探头探脑地跟了上来。经过几十天的朝夕相处,小黑熊对那3个生灵,已经亲切熟悉。现在,他们要走了,她怎么能不跟上去?尽管她并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走多久。
前面有天神威风的始祖母,后面有天真无邪的小黑熊,男孩越走越高兴,就咿咿呀呀地唱起了山歌,冰天雪地的太行山脉就充满了生机。
在男孩的歌声里,他们总是能碰到好运气。当他们饥饿的时候,男孩手中的魔棍,总是能从雪地里点到一只剑齿象的鼻子和身子,成为小小队伍的给养。
可怜的剑齿象,曾几何时,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巨无霸,何等的雄壮威风,何等的繁荣昌盛,何等的战无不胜,怎么就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呢?
现实是残酷的,特别是在非常时期,只有生或者死,只有吃或者被吃。不过,当这只小小的队伍,即将到达大河,当这几个幸存的生灵,得到最后一次救命的食物时,还是被震慑了。
那是一只壮年的雌象,巨大的身躯,不是躺着,也不是站着,而是跪在地上,头朝南方。
那是到达大河北岸的最后一只剑齿象。一年前,她率领自己的家族,开始了南迁的征途,小象、雄象、亚成体的雌象,足足有18只。后来,半路上又收容了3只,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走在大山里,要多雄壮有多雄壮。
但是,恰恰是这雄壮,成了无形的杀手。因为在那个比他们更庞大更雄壮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食物,去支撑他们的生存。
一个生命倒下了,他们用冰雪掩埋了尸体,继续前进。
又一个生命倒下了,还是用冰雪掩埋了,接着前进。
就这样,一个,两个,3个,直到10个20个,成为太行山脉中的荒冢。
就这样,一只,两只,3只,直到10只20只,成为后来者的食物。
就这样,一山,一山,又一山,撇下自己的队伍。
就这样,一步,一步,又一步,带走自己的孤独。
现在,当大河已经在望,南方就在前面时,她自己也坚持不住了。已经没有谁来掩埋她的身体了,她就那样跪在了地上,雪白的剑齿,像一副支架,撑着身体,鼻梁上的肉球,像一朵鲜花,正在开放。
头颈再也不会转动,眼睛再也不会流泪。魂魄早就散了,却盘绕在空中,纠缠着雪,纠缠着风。身体早就僵了,却不肯倒下,对抗着雪,对抗着风。她死得不甘心啊!
她是在向北方的祖先谢罪吗?他们开拓的疆土,在她的手中丢失殆尽。他们繁育的后代,在她的时代全军覆灭。而这一切,不是她不努力,不抗争,而是造物绝情,天地不容啊!
她是在向南方的后代谢罪吗?她和她的家族,在华北平原优化出来的耐寒基因,终于被泯灭在大河以北,这就意味着,在下一个更加严酷的冰期到来时,南方的家族,乃至整个物种,都将面临灭顶之灾。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失败,她的无能啊!
艰难的始祖母站在跪立的雌象面前,沉默着,沉思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眼前的景象令她震慑,也勾起了万般凄清。
几十万年前,他们的祖先是一起离开秦岭的。
十几万年前,他们的祖先是一起雄霸华北平原的。
可是今天,最巨大的剑齿象种群却已经泯灭在大河的北岸,丧失了未来,也丢失了过去。
始祖母的眼里荡起悲伤的涟漪。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到底,就算她已经抵达大河,就算她今天还在活着,可是,谁能保证她能安全渡过大河?又有谁能保证转瞬之间,她不会死于非命?
小雌猫叫了一声,那是饥饿难耐的,催促开餐的叫声。
始祖母没听见。
小雌猫用脑袋拱了一下母亲。
始祖母还是不动。
小雌猫按捺不住,一口咬住了剑齿象的鼻子。
始祖母突然发怒,照着小雌猫的屁股,狠狠地咬了一口。
小雌猫一声尖叫,困惑地看着母亲。
站在一旁的男孩,也恐惧地退后几步。
但这只是瞬间的事情,当小雌猫的屁股渗出鲜血时,始祖母立刻清醒过来,伸出舌头,舔着她的伤口。
小雌猫哼哼着,述说自己的委屈,抗议母亲的蛮横。她不明白,在吃过那么多剑齿象之后,为什么这一只就不能碰。
始祖母终于来到剑齿象身边,面对面地跪下来。
一双黑幽幽的眼睛,看着那双死灰色的眼睛。
一个湿漉漉的鼻子,触摸那个硬邦邦的鼻子。
一对热望的犬齿,撞击那对冰冷的剑齿。
她在祈祷吗?忏悔吗?还是在企求?
起风了,昏天黑地。
下雪了,万物混沌。
苍天啊,宽恕她的残忍吧!
大地啊,怜悯她的无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