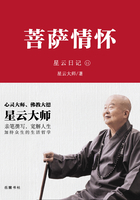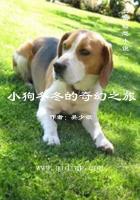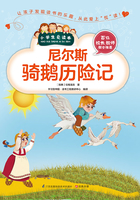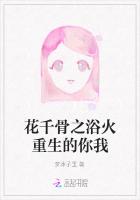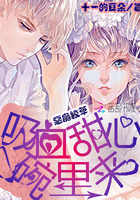西夏前期曾多次出现过后族、外戚当政专权的情况,后族与皇族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皇族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如谅诈母没藏氏与其兄没藏讹庞、秉常母梁氏与其兄梁乙埋、乾顺母(第二个梁太后)与其兄梁迄逋时期,后族把持朝政,权倾一时。仁孝当政以后,为扭转局面,强化皇权,下令编订了《律令》,力图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和巩固皇权。如《律令》第一章之“大不恭门”规定:“盗毁护神、天神,传御旨时不行臣礼,起轻视心,及御前、制、御旨直接唤人往,无故不来等,一律造意以剑斩,从犯无期徒刑”。第七章之“敕禁门”也规定:“节亲、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石黄)、鸟足赤(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举告赏当给十缗现钱,其中当允许女人穿红、黄各种衣服。又和尚中住家者及服法依另穿法:袈裟、裙等当是黄色。出家者袈裟等当为黄色,大小不是一种黄,当按另外颜色穿。若违律穿纯黄衣时,依律实行。前述衣服、髻冠等诸人所有应毁当毁,欲卖,当于应卖何处自愿去卖。”“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诸人等敕禁:不允有金刀、金剑、金枪。以金骑鞍全盖全口,并以真玉为骑鞍。其中节亲、宰相及经略、内宫骑马、驸马,及往边地为军将等人允许镶金,停止为将不允再持用。若违律时徒一年,举告赏给十缗钱。”“佛殿、星宫、神殿、内宫等以外,官民屋舍上除口花外,不允装饰大朱,大青,大绿。旧有亦当毁掉。若违律,新装饰,不毁旧有时,当罚五缗钱,给举告者,将所饰做毁掉。”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律令》从建筑、服饰和用品等方面规定了皇族所享有的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权利。西夏统治者虽然给佛教以极高的地位,但是宗教的权利再大也大不过皇权。克恰诺夫在《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一书中着重提到了西夏佛经的检查制度,由此可以想象,西夏统治者竭力要将对当时来说最为重要的思想领域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他在《西夏国家佛教寺庙的法律地位》中也写道:在远东地区,佛教徒的活动总是在国家的监督下进行的。这都说明了统治者除了笃信佛教以外,还把它视作巩固和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加以利用。
三、西夏的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由于地域关系,历史渊源和境内民族成份等因素,当时西夏境内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是同时存在,共同流行。西夏前期为弘传佛教,曾先后6次向宋请赐佛经,并以宋代官刻本《开宝藏》为底本翻译成西夏文《大藏经》,这说明了汉传佛教在西夏的盛行。唐安史之乱以后,河西曾为吐蕃所据,当时佛教在河西已极为兴盛,为西夏藏传佛教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加之为避朗达玛禁佛之祸,许多吐蕃僧人携佛经逃往河西地区,更加大了藏传佛教在西夏佛教中的比重,所以西夏早期即有吐蕃僧人在其境内弘法传教。《律令》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如第十一章之“为僧道修寺庙门”载:“诸人于寺庙内不许口口、杀生、捕捉禽鸟。倘若违律时,徒六个月。”“皇使及大人随缘者居于他人诸寺庙、官堂、神帐等内,不许居宿栓缚驮马牲畜,所属侍奉者不许于僧入门户引导妇人住近。违律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侍奉者当外出而住。”“诸寺庙、官堂、神帐中不许诸人住宿口,违律时比于寺庙杀生之罪状当减一等……”这些条款大多是汉传佛教戒律规定,这也为僧人的清修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律令》还规定:“诸僧人,道士本人已亡,有出家牒,彼之父、伯叔、子、兄弟、孙诸亲戚同姓名等涂改字迹,变为他人出家牒而为僧人、道士者,依为伪僧人、道士法判断。”这其中的“子”为何人,笔者认为应有两种理解:1、可能是指他出家以前所生的儿子。2、也可能是受藏传佛教影响,因为藏传佛教一些教派的僧人是可以娶妻生子的。
《律令》中还多次提到羌、番、汉僧人、道士的称谓,在试经时,对羌、番、汉族行童所颂经文也有不同的要求,说明了汉传和藏传佛教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了西夏境内西夏僧、吐蕃僧、汉僧人数之多,他们为西夏佛教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另外,其它文献资料中也记载了有关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流行的一些情况。乾顺天佑民安五年(1094)《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铭》结尾处有:“感通塔下羌汉二众提举赐绯和尚臣王那征遇。”此处的羌,应该是指吐蕃,可知当时凉州已有管理吐蕃和汉族佛教事务的僧官,也说明当时河西地区吐蕃僧人众多。另据藏文文献《贤者喜宴》记载,西夏第五世泰呼王遣使臣入藏迎请噶玛噶举派法王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未能前来,随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来西夏,藏索哇被西夏王尊为上师,传授藏传佛教的经义和仪轨,并翻译佛经,很受宠信。后来都松钦巴建粗布寺修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缨络及幢、盖等各种饰物。又载:萨迦派祖师札巴坚赞的弟子觉本,曾被西夏人奉为上师。元代《黑鞑事略》载:“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元代人马祖常也写过一首《河西歌》:“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泛指僧人)作夫婿。”这都反映了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的影响。
四、西夏僧人的特权及度僧制度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原以来,中国人开始接触佛教。魏晋时,对出家为僧、尼者并没有什么限制,可以自由出家。到后来,出家僧人数量增多,编户减少,严重地影响到了官府的财政收入和兵役徭役。所以,从南朝刘宋元嘉、大明时期(424~464)及北魏正平至延兴年间(451~476)开始,南北朝政府已普遍采取了僧尼公度、禁止私度的政策。唐宋时期,政府对僧籍管理空前强化,不仅实行了严密的僧尼籍帐制度,且建立了完善的度牒、戒牒、六念等僧尼身份证件的管理办法。从《律令》内容上看,西夏同样也承袭了唐宋的度牒、籍帐等制度,严禁私度僧人,对违律者予以严惩重罚。《律令》中对此所列甚详,现举几例试说明,如《律令》十一章之“为僧道修寺庙门”:“种种善时剃度使为僧人时,僧人行童、室下常住二种行童等,以及道士行童等中可使为僧人,此外种种诸类中,不许使为僧人。若违律时,使为僧人者及为僧人者等之造意当绞杀,从犯徒十二年。若为僧人者未及丁,则罪勿治,使为僧人者依法断,为僧人处之师傅与造意罪相同。担保者知觉则当比从犯减一等。其中受贿者与枉法贪赃罪比较,从重者判断。”由此可见,西夏严禁私度僧人,并对私度行为进行严惩。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僧人、寺庙地位崇高,享有很多特权,如第一章之“谋逆门”规定“祖母、婶母、嫂娣、姑,此等寡居,及有女妹,或已嫁,或为他人养女,或有为僧人、道士等者,莫入连坐中……”和“应连坐人早已为僧人、道士,已出家与家院不往来,与彼处谋逆后,原主父母、节亲等勿连坐,父母等犯逆罪,亦依前所示出家人勿人连坐中。”《律令》中还规定除十恶和杂罪中不论官者以外,其余的罪状可以官品当,不施黥刑,赐衣者比庶人罪减一等。同时,法律对寺庙、神像等进行保护,若有损坏者给予严惩。《律令》第三章之“盗毁佛神地墓门”还规定:“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其中僧人、道士及军所属管事者损毁时,当比他人罪状增加一等。若非损坏,盗而供养者,则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若价值很多,则视强盗、偷盗钱数之罪及损毁罪比较,依其重者判断。”从这一条款看,西夏政府用法律的手段对佛教、道教和儒学进行保护,并且把佛像置于首位。对盗佛像者,不是损坏而供养者,法律则网开一面,处罚的力度也大大减轻,而对知法犯法者则罪加一等。这与西夏统治者崇佛的政策是相一致的。还规定“诸寺庙、道观等所属设置常住中,大小局分擅自拿取盗持时,加罪之法,当与前述盗官物同。”这些规定把盗毁护神、天神与传御旨时不行臣礼同等对待,把寺庙的财物比同官物,足见寺庙的地位之高。第二,在西夏,僧人基本上是不纳税、不服兵役的特殊阶层,如僧尼太滥,会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兵役徭役。从《律令》中我们可以知道西夏赋税是相当沉重的,除了田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变相负担。西夏地处西北,国小民穷,为了生存发展和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它在建国之初,就置兵30多万,戍守四境。西夏在立国的190年问,与周边国家的战争时断时续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每次都点兵和壮丁数万乃至十几万。除了兵役外,西夏征派徭役,用于修治河渠桥道和宫阙王陵、建寺立塔和官府寺庙的日常杂役等。这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所以,很多人设法出家为僧、尼,以逃避纳税和赋役。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源和兵源,西夏统治者在大力推崇佛教的同时,也采取一定措施严格控制僧人的数量,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实行试经制度,严把剃度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