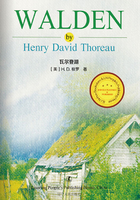清代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曾说:“吾乡(维扬)茶肆,甲于天下,多有以此为业者。”
这当然不是一句虚话,无论历史或是现在,一直都是如此,扬州人至今仍有“早上皮包水”的说法,说的就是大早起来泡茶馆、吃早茶。随手翻开《扬州画舫录》,在那些竖排的发黄的字纸间,透过时间的烟云,依稀瞥见沿水临河,茶馆茶肆仍然处处都是,在一处普普通通写小秦淮茶肆的文字前停留片刻,“小秦淮茶肆,在五敌台,临水小屋三楹,黄石攒兀,石中古木数株,下围一弓地,置石几石床。前构方亭,久称佳构。”——这样的茶肆莫名地就让我为之神往,那样依水而建,几茎芭蕉或数株古木下,二三好友闲闲地坐在石几上,面前二三青瓷或是紫砂茶杯,青翠的明前毛尖,冲了水,看白的水气恍若轻烟,袅袅而起,几可悟禅。“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这当然是夸大了的,但在那水边的茶馆,凭栏品茗,水流得自然是静静的,身边风柔柔地拂过,又是何等一个清凉静谧的世界,想想世间事,真不知纷纷扰扰的名与利最后又是为了什么?何如一杯清茶来得自在与悠然。
这样的茶馆也许是只应当在梦中出现的,梦中的我,也许只是一袭长衫,梦一般在这个城市的水边放浪着,且诗且画,且酒且歌,悠游自在,我只为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罢也罢,人生原只是落得自在的,那么多的羁绊平白地要来干什么呢?所以没来由地就对那水边的茶馆好感着,或是从过去的文字中来,或是自先天中来,尤记得刚到维扬之地时,羁泊在问月桥附近,黄昏时,出得小小的宾馆,来到桥上,斜阳日暮里,对河一排水边的茅草苫就的房子忽然间就把我的目光吸引过去了,这个城市的老城区,高楼最高不会高于七层,还得雕栏玉砌,飞檐翘角,以与那些唐宋明时留下的文物石塔、文昌阁、四望亭等相一致,而这整整齐齐的三四间草房在水边留着,古雅处却分明自有二分野趣,那茅草苫得齐齐的,据说每年都要专程去海边割了草换上,盯着那一排水边的草房不由就发痴了———忽然就觉得这一切那么地熟悉,熟悉得让人心里慌慌的,仿佛想起许多东西,前世今生一般,然而细细想去,却一样也想不出,只看见面前的河水无言地流着……后来知道这就是冶春茶社的水绘阁,也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茅草房,所有房子都临水而建,沈从文的文章里常见有吊脚楼——其实冶春的房子似也可名之为吊脚楼,或者说是水榭,都是小半临河,大半靠岸,只是少了湘西那真正的野趣(自然更没有沈从文看到的多情水手与多情妇人了),地方靠近乾隆水上游览线的起点,入目风景俱是古朴雅致,到这里,选个沿窗的位置坐下,一壶茶,一碟干丝,一盘肴肉,几只点心(蒸饺、烧卖,或包子)。“扬州好,茶社客堪邀,加料干丝堆细缕,烧酒水晶肴。”这样闲闲地吃着,闲闲地聊着,边吃边看风景,对面假山竹石,花木扶疏,水中偶有小艇画舫,穿梭往来,于浮生中偷得这片刻的闲情,总是好的。据说过去有船从河边过时,高叫几声,从窗口就可以把那茶、点心递到船上,现在不知可不可以,我坐船经过冶春那雕栏的窗下时,总想叫声:“上茶。”但声音却只在喉咙处打个圈儿,便闷下去了,到底没这个习惯,或者也怕人笑话——至少我从来没看过有人在河中叫茶的。
扬州吃早茶的茶馆最有名的其实是富春茶社,但可惜的是闷在巷子里,虽说是百年老店,名气不小,但感觉却没什么意境,没有那种在水边散散淡淡闲趣自得的意境,包括九如分座、菜根香等,给我的感觉都是如此,何况,味道也不比冶春胜出多少,所以终没有冶春那水边的茶社让我由衷地欢喜。
这样一想,自己品茶,原来竟品的是那种意境与心情,或者说仍只是爱的那种水边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