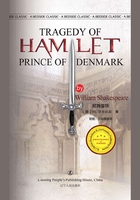“一溪春水泛黄颊”——这句元诗很形象,黄颊也就是黄颡鱼,我们那儿都称作昂刺,春天尤多——这实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鱼。
昂刺生性倔强,小的约一指长,大的也不过两指,头宽有须,似小鲇,身上滑溜溜的,胸鳍硬而无鳞,淡黄色,略有黑色断纹,身形看来极灵活。
小时觉得昂刺鱼好玩,因它的胡须和一根会叫的硬刺。
鲇鱼、鲤鱼的胡须是长在嘴的两边,一边一茎,昂刺鱼的胡须却不同,是长在嘴的上下,四根左右,上面的胡须一半白色一半黑色,嘴唇下的胡须却几乎都是黄色,这种怪异的样子让我很愿意接近它。
昂刺鱼背上的硬刺可以捏住,那根刺极尖利,颇长,呈锯齿状,一不小心是会被扎住的——有危险,然而更多的却是趣味,因为每每捏住刺的根部,这小小的鱼就全身扭动挣扎,发出“昂刺昂刺”的声音,不知是不是一种威胁或警告,这声音实在给儿时的我带来莫大快乐。
昂刺鱼得名的原因也就是这特有的声音——我很喜欢捏这根刺,恶作剧地听那“昂刺昂刺”的声音。不过,倔强地坚持不懈挣扎着的昂刺鱼很快便会从你手中滑出,掉在地上或者归入水中。吃昂刺鱼最多的时候似乎在清明前后,因为每到那一段时间水乡人家便要罱泥,彼时的昂刺鱼其实是罱泥的副产品。
罱泥,也就是将河底的烂泥(厚厚的包含一个冬天积下的枯萎菱叶水草等形成的有机质河泥,是养田的极佳天然肥料)用一种特制的竹罱夹子夹出来。
那时候家乡几乎是不用化肥的,农谚云:“人要桂圆枣子,田要河泥草子。”说的就是罱河泥肥田的重要性。罱泥可算是一场浩大的农事民俗活动——几乎是全村人一起行动,老辈人说过去罱泥一度还要集中起来放爆竹敬神才算数的。集中罱泥还在于河泥有好有坏,如果有人提前罱的话是会引起争议的。
从没有一户农家犯俗抢先,都是集中后再散到各个河港罱泥。那是水乡让人难忘的风景——走在不靠近河边的田埂上,常常看见麦苗深处散落着十多根竹梢簇,有节奏地上下窜动。走近了,才知道是内田的河,河里横竖着不下于五六条罱泥船,一条船两个人,三根篙子,一根撑船,两根是罱泥。河水低于田地,走在远处的田埂上,看来自然是很多的竹梢在动了。
每次罱泥后家里都会有一大盆水鲜,白的、黑的、黄的、青的,从鲫鱼、虎头鲨、青虾,到螺蛳、蚬子等,几乎什么都有,而黄色的昂刺尤多。
那些混在河泥中的水鲜带回家洗净后,常常混在一起红烧,或略放些老咸菜,出锅后绝无任何泥土腥气,其味之鲜美让人此刻都不禁食指大动。
钓鱼其实也是可以钓到昂刺的。
儿时家乡的打谷场附近有几个牛汪——也就是水牛休息打滚的水塘,有一次,几个小伙伴拉着自己去钓鱼,就在那个牛汪里,居然钓到了几条极大的昂刺,约有三四两重——这是极其少见的,与河中淡黄色昂刺不同的是,牛汪里的昂刺浑身作青绿色,肉圆滚滚的,力气极大,然而也就是那次,因为摘钩有些难度,自己居然被那大昂刺鱼刺着了手,肿痛似乎持续了几天才渐渐消除,这使得儿时的我在相当时间内碰着昂刺后没再敢捏那根尖刺。
家乡的昂刺吃法除了红烧,还可汆汤,汤极白,其肉细腻嫩白,无小刺,很适合老人与孩子食用。
扬州人爱以昂刺伴臭大元红烧——臭大元也就是臭豆腐,需洗得极干净,加以红辣椒、蒜片、姜丝、白糖,在铁锅中炒一段时间后,再入昂刺鱼,煸透,倒进铺有黄豆芽底料的砂锅中,加酱油,以小火慢炖,直至臭大元烧沸起孔为止,此时起锅撒些葱花、香菜末儿,上桌后,掀开砂锅盖儿,红绿相间,仍自沸腾不已,未动筷子便喷香扑鼻,鱼与臭豆腐均极嫩,甜、臭、香、鲜,诸味杂糅,食之真不知身在何处。
南京一位朋友有一次听我眉飞色舞地说起这道菜,惊讶不已,说他吃过,但他下的断语是“十分难吃,昂刺还是汆汤好,取其本味嘛”。
他后一句话我赞同,但前一句话却无法认同。后来在南京为此专门点过臭豆腐烧昂刺,果然味道不对劲儿——一则烹调方法不对;二则所用昂刺像是死了一段时间的,死了的昂刺会发硬,与鲜活者味道相差极大;三则臭豆腐也是小块状的——扬州的臭大元是那种圆形、发得很好的有孔臭豆腐。材料不对,加上加工方法的不,当,凑在一处当然不好吃。昂朋友从洛杉矶来扬,专门带他去吃了扬州的昂刺烧刺臭大元,昂刺吃光不说,即使落入砂锅底部的臭豆腐碎块,也被他用筷子捡来吃了。
再说说名字——昂刺这名字我小时只知道读音,为写法似乎专门想过,到底没想明白,这疑问在偶遇一位老者后总算得到解决,向他请教,才知道昂刺鱼正确的写法应是“鱼”。《本草纲目》鳞部黄颡鱼条记有“黄颡鱼,释名鞅轧”。
读作“angsi”,或“昂刺”,其实是江淮方言对古汉语语音的保留,读法是对的,写法却是错的,但的写法实在是少有人知道,既如此,只好依然以昂刺呼之了——况且这个词既形象又形声,昂刺既指其身上那根昂起的刺,亦可比拟那刺发出的声音:“昂刺,昂刺!”很想再听到那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