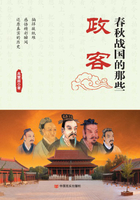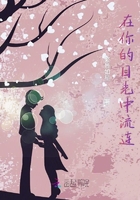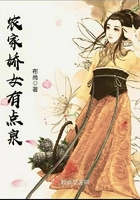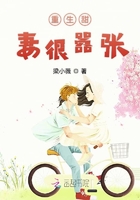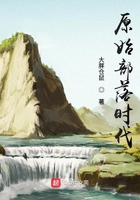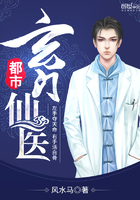1 开始学说话
眨眼到了1890年春天,海伦10岁了。
她开始学习说话。她想说话的愿望很久了。
一般听力正常的小孩,在家人或邻居的谈话中,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说话。一个耳朵听不见的孩子,学习说话十分困难,绝大多数成了哑巴,只能靠手语与别人交谈。如果一个孩子又聋又瞎,那么他不但不能学习说话,而且用手语与人交流也十分困难,因为他看不见别人的手势或指语。海伦就是一个又瞎又聋的孩子,但是,由于她的才能加上努力,她不但能用手语与别人交谈,而且更进一步,在她 10岁的时候,她决心要学习发音,掌握正常人的语言本领,实现用口语与人交谈的宿愿。
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正常儿童三四岁时已经会说话了,可海伦到1890年春天才开始学习用发音器官说话,这时她已10岁了。学习语言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她到这个年龄才开始呀呀学语,何况又是个聋子,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海伦虽然耳聋,可她的发音器官都是正常的。只要她有决心,还是可以与正常人一样说话。
她从小就一直想尽办法发出声音。她时常把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或者是摸摸嘴唇,认真地练习发声。
她很喜欢用手去摸会发出声音的东西,每当猫在叫或狗在吠时,她都会兴奋地用手摸它们的喉部;当别人唱歌或是弹钢琴时,她也会用手去摸他们的喉咙或是钢琴。
在她还没有生那场大病之前,她已会说些简单的单字,由于那场大病烧坏了她的耳朵,从此她就忘了说话。
变成聋子之后,她的声带仍然很正常,可以发出任何声音。她哭或笑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与正常人一样。她没有天生的语言障碍,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耳朵失聪,无法模仿说话。幼时,她常爬到母亲的膝上,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脸上,因为,她对母亲嘴唇的动作很感兴趣。
沙利文老师来后,教会她用指语与别人交流思想。但用手势或指语说话,往往无法表达抽象的想法,因此,她时常觉得很尴尬。
后来,有人告诉海伦说,如果经过严格的训练,她照样可以说话,她听到这个说法,心里高兴极了,因为她自己一直在努力发声。
家里人怕她的努力失败,经常劝慰她说:
“你不要这么勉强去做,用现在这种手语,别人也会明白你的意思,所以……”
但她对这些安慰置若罔闻,继续努力地学习发声。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解决问题的良机来了。
这就是罗拉·布莉姬就读的学校里的一位老师拉姆逊夫人来看海伦。拉姆逊夫人刚从瑞典、挪威等地旅行回国。她告诉海伦说,有一位眼睛看不见,耳朵也聋了,而且不会说话的挪威少女,在接受教育之后,居然会说话了。她说:“这位少女名叫朗希尔特·卡特。她所说的话,我们都听得懂,而且说得非常好。”
海伦听了她这番话之后,兴奋得不得了,同时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像那位少女一样学会说话。”
渴望像烈火一样在海伦心中熊熊燃烧。
于是,沙利文老师带海伦去拜访霍列斯曼学校的老师沙拉·郝拉先生。这位先生是个声学专家。
郝拉先生是位亲切、热心的人,他马上就开始教海伦发声。
这一天是1890年3月26日,从这天起,海伦在老师指导下正式练习发音。
郝拉先生的教法是让海伦的手轻轻地去摸他的嘴唇,让她知道在发音时,舌头与嘴唇的动作。海伦非常热心地边模仿边学习,居然在一小时内,她会发出M、P、A、S、T、I六个音。
郝拉先生反复教了海伦11次之后,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说出“It i s w arm”(“天气很暖和”)。
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当然,她的发音仍然是断断续续,带点口吃,但这至少是一般人所说的话啊!海伦学说话的信心更足了。她下定决心,从此以后,即使再笨拙,也要说话。
本来,她是一位连一个字都不会说的聋哑儿童,现在虽然说得不好,但总算是会说话了,这种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海伦兴奋之余,对着玩具、石头、树木、小鸟或是小狗,都结结巴巴地说起话来。
当她叫着妹妹时,蜜尔特蕾特会拿着食物走过来;当她叫小狗的名字时,小狗也会跑到她的身边。这时候她心中感到的喜慰,如果不是深受哑巴之痛的人,绝对无法体会。
当然,由于她当了10年哑巴,现在陡然学习说话,一开始绝非说得很好,只不过练习些基本发音而已。郝拉先生与沙利文老师也许懂得她的话,但其他的人,对她说的话,可能只是一知半解。
为了使她说的话能让别人听懂,沙利文老师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矫正她。经过一段很艰苦的努力,海伦终于能够正确、清楚地吐出每个单词了。为了把这些单词组合成句子,海伦又花了不少的时间与功夫,如果没有沙利文老师从旁协助,海伦的说话能力决不会提高得这么快。沙利文一生自始至终都在教海伦说话。
一个聋子要学说话,本来就十分困难。而海伦学习说话,更是比一般的聋子还要困难,因为老师嘴唇的动作、喉咙的震动、脸部的表情等等,她都看不见,必须用手去摸,才能知道。因此,她常常会弄错,有时一句话要反复练上几十次,甚至几百次,才能学会。对海伦而言,学说一句话,花上五六个小时是常事。
要正确的发音,就得练习,练习,再练习,有时海伦练习得连自己都快绝望了,恨不得能丢开一切,什么都不管。但是,过一会儿又想到如果自己能开口说话,家人一定会高兴万分,这么一想,她又重新振作精神,认真学习。
她的心灵,感到了一种新的力量。它正挣脱束缚,获得新的知识和信念。
海伦在自传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这一情形:
没有一个耳聋的孩子会忘记当他说出第一句话时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因为他急切地试图说出他从未听见过的话——冲出死寂的牢狱,那里没有爱的声调,没有小鸟的歌唱,也从来没有音乐的旋律来划破死一样的寂静。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我热切的心情。正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常常对玩具、石头、树、鸟以及不会开口的各种动物说话。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分享我的快乐——当蜜尔特蕾特应声来到我身边,或者我的狗乖乖地听从我的命令的时候,我感到的那种快乐。我觉得,如果我能够流利地说话,而且不需要翻译,那将是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恩赐!当我说话的时候,幸福的情感溢于言表,因为那些言语是我过去怎样也无法用手指来表达的。
但是千万别以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就真的学会说话了。我学到的仅仅是说话的某些基本要素。富勒小姐和沙利文老师听得懂我的话,但大多数人难得从100个词中听懂一个词。也别以为我学会了这些基本的要素以后,就能够全凭自己学会说话了。要是没有沙利文老师的教育天才,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牺牲精神,我要达到很自然地讲话的程度,简直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夜以继日地勤学苦练,才让我的亲密的朋友们能够听懂我的话。其次,我需要沙利文老师经常地帮助我练习发准每一个音,并把这些音素用无数种办法拼在一起。就是到现在,她还每天纠正我的错误读音。
只有聋哑人的老师才能真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才能完全理解我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特殊困难。我完全靠手指来理解老师的话语:我只能凭触觉来感知她喉咙的颤动、嘴唇的动作和脸部的表情,然而这种感觉常常出差错。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强迫自己反复念一个词或一个句子。这种练习有时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我觉得是那么回事时为止。我的工作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挫折和疲劳常常使我沮丧不已,但不一会儿想到我将很快回家向亲人们汇报我取得的成绩时,我又重新振奋起来。我急切地盼望着亲人们分享我的幸福。
我的小妹妹就将听得懂我的话了。这个信念比任何障碍都更强有力。我如痴似狂地喃喃自语:我现在不再是哑巴了!只要想到能和母亲讲话并能理解她的嘴唇作出的反应,我就充满了勇气。我惊奇地发现,用嘴说话竟比用手指拼写容易得多,我不想再用手语跟人谈话了。但沙利文小姐和几个朋友对我讲话时仍使用手语。因为这样比让我懂得他们用嘴说的话更快更方便。
在这里,我也许应该把手语的使用解释一下,因为这种手语令人感到迷惑不解。别人给我念书或同我谈话时,使用的是一种聋人常用的单手手语。我将手轻轻地放在谈话者的手上,轻到不至影响谈话者的手的动作。对方的手指移动时,我能很容易地感觉到他们的手指的动作,就像亲眼看见的一样。而且我感觉到的不是单个的字母,而是一个一个的单词,这和你们看书时的情况完全一样。经常的练习使我的朋友们的手指变得非常灵活。他们拼写得很快,快得就像一个熟练的打字员在打字一样。
海伦学会了说话,给家人带来无限的喜悦。
父亲、母亲,争着抱她,紧紧地抱住她。妹妹围着她跳起舞来。父亲为此而自豪。这使海伦想到了一首《圣经》中的预言:
“群山众岭高声歌唱,原野森林拍手欢呼!”
2 《霜的国王》事件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在海伦12岁那年,天真烂漫、过着幸福生活的她,在生活中已经遭受到人生不幸的她,突然中生活的长河又起波澜,她被卷入“剽窃”的旋涡中。
这是1892年的冬天。
在这个冬天里,快乐将弃她而去。
接下来的是她要承受生活的又一次打击。
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她将生活在“疑虑、焦急和恐惧”之中。她差点因为这次打击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连读书的兴趣也差点丧失了。
她在自传中写道:
“直到现在,一想起那些可怕的日子,我的心仍不寒而栗。”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原来海伦写过一篇故事,名字叫《霜的国王》。而她的这篇文笔极好,几乎展现出了她的天才的故事,被人指控为“剽窃之作”。这不啻是平地一声惊雷,炸响在海伦的头顶。
她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倒过去。一则小故事,酿起一场轩然大波。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霜的国王》这篇小故事,海伦写于1890年的秋季。她是写给波金斯盲人学校的亚纳格诺先生看的。当初,她并没有想到要去发表。
万万没有想到,这则故事后来会公开发表,从而成为她烦恼的根本原因。
那时候,海伦还居住在那间乡下小别墅,别墅门外,有一个偌大的蕨草采石场。
秋高气爽,风景迷人。
小海伦一时才思奔涌,突然萌发要创作的欲望。于是,她在采石场,那迷人的石凳子上,铺开了写字板。几乎是一气呵成。
一个12岁的盲女,能够一气呵成写一篇千余字的散文体故事,这实属不易。
引发这个故事的写作,起因应是因为沙利文老师在这秋天里常常向她讲一些动人的故事。沙利文小姐向她描述:深秋的树叶是如何美丽;采石场的石头是如何漂亮;流水淙淙,鸟鸣声声……
这使海伦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储存在她的脑海中,已经很久很久了。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存放越久,就越有些滋味。
这“另一个故事”也是别人对她讲过的。
于是,海伦开始在她的脑海中编写这个会令她激动的故事。她坐在采石场的石凳子上,铺开了写字板,用盲文迅速地写起来。她怕现在不写出来,这个“故事”会迅速从她的脑海里“溜”掉。
文思泉涌!海伦快快地在盲文写字板上写着。她把脑海中记住的东西,几乎全部都写出来了。
她根本没有考虑这些东西,原作者是谁,她是在什么时候学到的。全文写毕,她兴致勃勃地念给沙利文小姐听。海伦念得兴趣盎然。
沙利文小姐偶尔纠正她的发音。沙利文小姐也陶醉在故事的情节中。
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向家人宣读了这篇作品。全家人都感到十分惊奇。
这么优美的文章!全家人都很高兴。
家里有人当时还问过她:“你是不是在哪本书上读到过?”这个问题使海伦大吃一惊。
“没有呀……”她说。她一点印象都没有。谁给她读过这样的文章呢?她实在是记不清楚了。
这篇童话故事原名《秋天的树叶》,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不文雅,便改为《霜的国王》。沙利文老师对童话略做了修改,海伦又认真用盲文点字誊写了一遍。
这篇文章,她寄给了安南库诺斯先生。他十分欣赏这篇作品。
安南库诺斯是盲校很有名望的校长。他将此文推荐给校刊,在第一期帕金斯盲人学校的通讯刊物上发表了。
见到已发表的作品,海伦万分高兴。
然而乐极生悲。就在这时,有人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即揭发海伦,说她是剽窃了坎比小姐的《冰霜仙女》的文章。童话《冰霜仙女》早已收集在一本《小鸟与它的朋友》的童话书中,大家都可见到。安南库诺斯听到这个说法,觉得很尴尬,但他仍很相信海伦,认为两篇童话内容相同纯属巧合,不值得认真追究。
但当海伦回到波士顿的帕金斯盲校继续学习时,有位对海伦素有成见的女教师,就认真追查起这件事来。她与海伦进行个别谈话,探她的口风。海伦天真纯洁,无意中说出了沙利文老师,说她曾告诉她霜人用水彩把树叶染出美丽颜色的故事。这位女教师立刻主观推断说:“这么说,你是早就知道《冰霜仙女》的内容了,沙利文老师既然会告诉你霜人的故事,那她一定也告诉过你坎比女士的《冰霜仙女》!”
“不,老师!我从来没有听过《冰霜仙女》这个故事,也从来都没听过坎比女士这个名字。”
不论她如何为自己辩护,这位老师始终不肯相信,她一口咬定海伦是抄袭别人的作品。她还把她的看法与结论,告诉了安南库诺斯先生。
安南库诺斯先生听了她的谗言,竟然大发雷霆,把海伦叫来,严厉训斥了一顿。从此,无论海伦如何解释,校长都不信任她了。他认定她与沙利文老师合谋,将别人的作品改头换面,据为己作,目的是为了出风头。
后来,学校的教师会及理事会,都曾把海伦叫去,严格地盘问。当他们质问她的时候,连沙利文老师都不许进去,好像怕她们会订立攻守同盟似的。教师会盘问时,一开始就要海伦承认抄袭别人作品的错误。海伦面对长久的严厉的盘问,不知要如何应付才好,只觉得又累又难过。最后,她对所有的质问,都不做任何解释,只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过了好久,他们才让她出来。
这天晚上,海伦整夜不曾入睡,在床上辗转反侧,一会儿痛哭,一会儿又全身发抖。她为自己做出这种羞耻的事而连累老师,感到非常难过。但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她自己也不知道。
幸好海伦这时还是一个小孩,随着时间的消逝,她的痛苦逐渐被冲淡,孩子最容易忘记不愉快的事情,心上的伤痕也很容易愈合。
可是,沙利文老师必须为自己洗刷,因为她确实不知道《冰霜仙女》这篇童话,也没读过收入了这篇童话的那本故事书。她决没有伙同自己的学生作弊,连这样的念头也没产生过。于是,她拜托为人正直的贝尔博士,对这个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