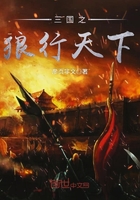就在王敬铭在感慨朱友裕和王彦章两人的武勇时,远处一阵急剧的马蹄声响起,如暗夜的惊雷一般在天边炸响,朱友裕和王彦章一愣,随即他们知道己方的援军来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火把和旌旗蜿蜒而来,冲入了平卢军的营寨……
当先一人四十来岁年纪,正是汴梁城临时的兵马指挥使王重师,他身边的是一身戎装的朱友宁,朱友宁手中是一杆一丈八长的马槊。这是朱温当年从一个敌将手中缴获的,做工很是精细,朱友宁看了十分喜爱,朱温索性就送给了他。
王重师的另一边是朱友文,他的兵器是一把长刀,刀锋的寒光在火把的照耀下闪耀生寒,他与朱友文两人与王重师三人齐头并进,势如破竹的攻入了敌军的营寨,如汤泼雪般把迎击的敌军杀的溃不成军。
虽然王重师他们的主力部队距离朱友裕他们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但朱友裕和王彦章已经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来自对面敌军的压力遽然减小。他们很清楚,这是敌军士气瞬间低落的结果。
王敬铭长叹一声,知道大势已去,趁着敌方的大军还没有攻来的时候,留下三千人断后,自己率领中军急速撤走。
王重师命朱友宁带领五千人一路追击,平卢军人马一路溃退,等王敬铭摆脱了朱友宁的追兵的时候,检点人马,三万多人的大军已经不足一万,他长叹一声,命令部队埋锅造饭,稍事休息就继续赶路,真的是如丧家之犬一般。
却说朱友文带着三千人马把王敬铭留下来断后的人马冲散,命令几名都将继续追杀,自己却带着亲兵来见大哥朱友裕。朱友文见大哥一身是血,急忙道:“大哥,你受伤了?”
朱友裕拖着疲惫的身躯勉强笑道:“不碍事,大部分都是别人的血,幸亏你们及时赶到,要不然我跟这位王校尉恐怕要交代在这里了。”
朱友文略带埋怨的道:“大哥,你也太大胆了,带着五百人就敢冲击敌人两万多人的阵营,你怎么说也得跟王重师将军商量一下啊,最不济也要算上我一份儿才对,害得我们担心了好长时间。”
虽然朱友文的话略带责备,但字里行间里却带着浓重的温馨,让朱友裕心中十分感动,朱友裕道:“是做大哥的考虑不周,让二弟担心了。”
这时朱友文才注意到朱友裕身边的王彦章,王彦章身上多处负伤,可却从没有一刻放弃过战斗,他胯下的战马也同样疲惫不堪,两杆铁枪上全是血迹斑斑,在火把的照耀下,王彦章整个人犹如从地狱中出来的魔鬼般让人胆寒。
朱友文在心底里暗赞一声:“好一员虎将!”口中却道:“王校尉,你不尊王重师王将军将令,私自出城,陷大公子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你可知罪?”
朱友裕急忙道:“二弟,这不管他的事,是我让他跟我一起偷袭敌营的,你知道,我是王府的长子,他没有不听从我的命令的理由,所以这次擅自出城的罪名由我一个人承担,与王校尉无关。”
朱友文道:“这个不是小弟我能够管的了的,你也知道,现在我只是管一些钱粮的事情,至于其他的东西不是我份内的事情,我也管不了。还是让王将军来决断吧。”
朱友裕虽然是朱温的长子,可在军中并无官职,只是靠着父亲的身份被朝廷封了一个宣节校尉的虚衔,王重师现在是汴梁城的主将,所以有什么事情都要交给王重师处理。
王重师已经许久没有在战场上出现了,因为以前作战勇猛,身上多处负伤,身体落下残疾,所以不得不在家养伤多年。朱温留他在汴梁不过是做个样子,毕竟汴梁是朱温的大后方,轻易不会受到攻击,却没想到被平卢军的人马乔装改扮长途奔袭,就这么来到了汴梁城下,是以这名当年在军中显赫一时的大将不得不在多年后重新披上战甲,又一次重温当年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
由于以前肺部受过伤,骑马没有多长时间的王重师就已经有些气喘,脸上出现了一片潮红,但是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朱温的长子身陷重围,他不得不再一次跨上战马,又一次屹立在战场之上。而不同的是,以前他是冲锋陷阵,而这一次他却是在指挥方遒,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了年轻人。
不可否认朱温的几个子侄都武艺精熟,在万马丛中都可以轻松自如游刃有余,颇有朱温年轻时的风采。可他不敢让他们冒险,无论是作为朱温儿子的朱友伦,还是作为朱温侄子的朱友宁,昂或是那个名义上的义子朱友文,都是朱温的心头肉,他们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都是他这个主将的失职,都会让他无法面对对自己信任有加的主公朱温。
当朱友裕和朱友文二人带着浑身浴血的王彦章来到王重师面前的时候,王重师并没有提朱友裕擅自出城的罪名,只见他艰难的翻身下马,抱拳道:“大公子,末将迎接来迟,让大公子身陷重围,实乃末将之罪,末将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还望大公子勿怪。”
朱友裕急忙回礼道:“老将军言重了,这一次是我过于莽撞,让老将军担心了,请老将军责罚。”
几人一番寒暄,王重师下令收兵回城。
朱友裕回到城中,魏国夫人张小惠,还有黄颖、韦凤等朱温的几位夫人见了浑身是血的朱友裕,不由的一个个心疼的跟什么似的,一口一个“我儿怎么可以如此冒险”等等的话说出来,当然也少不了一番责备。朱友裕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陪着笑脸,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处理过了,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有几处皮外伤而已。
倒是王彦章身上有几处伤口有些重,只是他身体强壮,被郎中包扎了一番止住血以后也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这一战王彦章奋勇杀敌,阵斩敌军别将一人,都将两人,校尉五人,战功赫赫,只是由于这一次是擅自出兵,所以暂时功过相抵,该奖还是该罚要等朱温回来再做定夺。
几位夫人絮叨了半天才发现这时候应该让朱友裕先好好休息一下,所以纷纷回后院去了,只有张小惠一个人流了下来,道:“友裕,你这孩子有能力,无论是文是武,在众位兄弟中都是顶尖的,只是你行事不应该如此莽撞。你黄姨说不让你轻易出战也是为了你好,毕竟你们兄弟都是王爷的儿子,王爷已经对不起你的母亲了,所以我们几个更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并不是我们不想让你出兵征战,而是我们怕万一你有个什么损失,你娘那里我们不好交代,这也是为了你好。”
朱友裕心中不由的有些感动,哽咽的道:“母亲,我……”
张小惠笑道:“你的性子我了解,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我对你们兄弟几个一直视为己出,这些你们也都能够看在眼里,特别是你爹,他对你们每个人的溺爱都是一般,所以我不希望看见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受伤害。”
朱友裕道:“我知道,可是我不想让人家看不起,我已经长大了,不能一直生活在你们的羽翼之下,我不像四弟,他生下来就注定要继承父亲的家业的,而我不同,如果我不能在军中有什么作为的话,以后岂不是要就此碌碌一生?”
张小惠深深的看了朱友裕一眼,欲言又止,良久之后才叹道:“我本不想跟你说的,事到如今也就没有再瞒你的必要了,现在你爹还正当壮年,本不该考虑这些事情,可你爹曾向我提起过,对于他的几个儿子之中,他最看好的人是你,他想,如果他在百年之后,他想把他的家业传给你,也只有你才能把宣武军发扬光大。你四弟心地过于仁慈,恐怕不能驭众,是以不是继承人的最佳人选,你爹白手起家,创下的这么大一份家业,可不想在你四弟手中毁了。”
朱友裕的四弟是朱友贞,也是张小惠的亲生儿子,张小惠能够如此对朱友裕说话,足见她对朱友裕能力的肯定,也足见她对丈夫的言行的重视,她并不因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失去继承权而有什么意见,虽然现在儿子还顶着一个世子的头衔,可她心里同样清楚,儿子友贞不是做大事的人。
如果在太平年月的话,朱友贞那种性格可以成为一代名臣或者是一代明君,可现在是乱世,这个枭雄并起的年代,仁慈就要吃亏,过度的仁慈就成了懦弱。
朱友裕仿佛豁然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切来的竟然是那么的突然,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就在他心中更高兴的时候,张小惠的声音又接着道:“友裕,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一切都还只是暂定,现在你爹还正当壮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你也不要在心中存着什么想法,万一以后你爹再做出其他的选择,你也不要怪他。”
朱友裕急忙道:“孩儿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