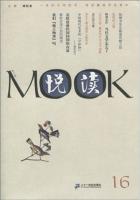那天妈在黑暗中一直抱着我流泪,他“咣”地一拳打在生硬的墙上,他说:“要不是为了小南我会出去和他们拼命。”妈说:“难得你还能为了小南。”他深深叹了口气抚摩我的脸,我看着他手背上流下的血,放声大哭。他已经是个50岁的男人了,怎么还能这样呢?我心里开始恨他,因为心疼而愤愤地恨着。
终于,在我读中学那年,他被调到了离家50公里的地方,那是一个林场,他能管理的,只有满山的树木。因为交通不方便,50公里的路,他只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到达。妈生他的气,在他离开以后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也生他的气,可我还是想念他,到了假期,催着让他回来,带我到他生活的地方。50公里,他带着我走了整整一天,其中有一半是蜿蜒的山路,难以想象,那个地方是怎样的荒芜,少有的几户人家,没有食堂,吃饭要自己做,买菜要到5公里外的镇上。那天看着他荒芜的小屋我一次次忍着眼泪,他不喜欢我哭,他希望我会像他一样坚强。
那样的日子,他一过便是8年,8年,寂寞和荒芜渐渐磨平了他性格中的锋利,他似乎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可是他依然骄傲,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所做的一切,更是不许任何人说。然后我考上了大学,是在实行并规制的第三年,当时两个哥哥虽已工作,单薄的薪水也只够负担自己的生活,数千元的学费对于他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经济意识的男人来说,无疑是笔巨款,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借过任何东西的他,为了我的学费到处借钱,然后为了还钱为了我的生活费,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戒掉了抽了30多年的烟。
戒烟没有让他长胖却让他更加消瘦了,他送我去学校,在那些孩子年轻风光的父母面前,他苍老得让人难以相信是我的父亲。可他还是那样骄傲,骄傲地在宿舍里指挥着我收拾自己的床铺,骄傲地说:“这个城市,当初我来接兵的时候,还是个小破地方呢。”然后他像将军视察一样,背着手昂首挺胸地走过了整个校园,我挽着他的手臂,我是他最心爱的兵。
然后每年开学的时候,他还是坚持送我上火车。那个小站,快车只有两分钟的停靠时间,每次他都要坚持跟我上去帮我找到座位,不顾列车员的阻拦,然后在车门关闭前他一跃而下,莽撞得像个青年,惹得列车员一次次朝他直翻白眼,脾气那么不好的他,呵呵笑着好脾气地由着他们对他的抱怨。只有为了我,他能这样忍着。我贴在车窗玻璃上,看着他刷刷向后退去的已渐渐苍老的面容,他这个男人,都这么老了,还是这么固执,我拿他根本没有办法。
在我读大三那年,在交通发达到汽车可以一直开到他在的山顶的时候,他终于退休回到家里。为了适应退休的生活他种了花买了鸟,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照顾好,花总是没有开就死去,那些笼里的小鸟最后也都被他放掉了,他说讨厌它们女人啼哭一样的鸣叫。他更不喜欢看电视和报纸,上面的新闻越来越让他生气。他唯一的爱好是骑着自行车到处行走,那样地不甘寂寞不认年老。
彼时,我已经是个别人眼中出色的女子,年轻聪慧,还能写出漂亮的文章,可是每次他打电话,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傻丫头,你从小就笨,在外面多长个心眼……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说我笨的人,在他眼里我什么也不会什么都不懂,永远像个无知的孩子。虽然事实上,我真的已经长大了,不仅能够负担自己的生活,还能给他买他爱喝的各种名酒。
他看起来心满意足,因为在他最初的意愿里,想要个女儿无非是换日后的好酒。这谁都知道,就算他像个孩子一样狡辩都没有用。当然,女儿长大了还有一件事,就是恋爱。
告别大学我义无返顾地离开诸多繁华城市的诱惑回到了家乡的小城,我知道世界很大,可是没有什么地方能比他更诱惑我。回来的那年冬天,我碰上了他,他叫我小南,和他一模一样的口气。他们有同样的眼神和几乎同样的声音,我爱上了他,不顾他长我10岁不顾他有妻有子。在那个漫长的冬天里,我只在意我的爱情,不管其他。
我却一直没有告诉他,一直瞒着他和妈,我知道不管他有多爱我,也不会容忍我做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他的善良他的骄傲他做人的原则都不允许。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隐瞒着,可事情还是被用另外的方式摊开了。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的妻子知道后没有找我而是找去了家里,妈焦急而慌乱地在电话里说:“她来咱家了,正跟他爸呢闹呢。”等我明白过来,感觉到了心都在飞速地下坠,这是最坏的方式,我不知道固执而骄傲的他,怎样面对一个捍卫自己婚姻的女人对他心爱女儿的讨伐,他有生的60多年,没有做过任何能够被别人指责的事,他永远地义正言辞,现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敢想他该如何安置他逐渐苍老的尊严。
心如霜寒,一路奔跑着回去,连车都忘了坐。等我在寒冷的风里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推开家门时,院子里却是出人意料地安宁。妈站在门边,目光依旧充满忐忑,他却在花草中唯一存活的冬青树前,耐心地用剪刀修剪着它的枝叶。听到推门声他抬起头来,看着我气喘吁吁地样子责怪:“跑啥跑,大冷的天灌一肚子冷风,快进屋喝点热水。”口吻平常平和,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应着跟妈走进去,他还在那里剪着冬青的枝叶。我小声地问妈发生的事情,妈说:“我放下电话时,他爸已经把她在赶跑了,从来没见他那么不讲理过,说人家污蔑你,还说,我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谁都没她好,差点把人家气翻……丫头,你告诉妈,到底咋回事……”
妈一边絮叨一边给我倒开水,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想象着妈说的情形,想象着一贯以讲道理为做人准则的他,怎样蛮不讲理地赶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为了他任性的女儿,他又一次破了例。我刚要说什么他走了进来,放下剪子拍了拍手看着我,慢慢地说:“丫头,回头把他领回来让爸瞧瞧。”
我和妈都怔住了,原来他是相信的,相信那个女人所说的话,而他最后的态度,却是如此。难道在他眼里,女儿所做的一切真的都是绝对正确吗?让一生明辨是非的他,原由都不肯问一句,这样地委屈自己的心性,委屈他一度比生命更看重的骄傲。
我说不出一句话,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的眼泪簌簌而下。
那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说我们分手吧。我说:“不管我有多爱他,也无法超越我爱他。”“他是谁?”他疑惑地问。
我没有回答,这个答案,我自己知道就够了。慢慢放下电话,那一刻,心若无风的水面,有异样地温柔和平静。我想起他说,我是上天赐给他的生命的惊喜,那么我怎么忍心让他一次次为我,委屈上天赐于他的生命的骄傲呢?有生之年,我一定会用他过爱我的方式去爱他,不让他受一点点的委屈。
无处感恩
凉月满天
又在做梦。
梦里他的老父亲胖胖的,软软的,身子象婴儿一样,倚靠着他,他半扶半抱,一边走一边宽慰:“爹,甭怕!你儿子砸锅卖铁也要给你治病。你想吃啥?面包,蛋糕?……”梦里举了一大堆吃的,全离不开一个“甜”字。他在梦里忘了爹的糖尿病,却一如既往地记得他爱吃甜。小的时候,没有糖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偶有卖甘蔗的,用刀剁开,一段一段的,一毛钱一段。爹禁不住他的缠磨,掏出金贵的一毛钱,买一段。皮太厚,太硬,他太小,牙也嫩,根本咬不动,爹就给他转着圈用牙往下剥皮,剥一片,嚼一嚼,吮一吮,咂咂有声。把剥得净光净的甘蔗递给他,看他大口大口咬着吮糖汁,甜得“咝!哈!咝!哈!”抽凉气,爹的喉结就一动一动。吃到最后,剩个硬结,有一股苦味,他不肯再啃,爹就把这个硬结一点点嚼碎了,一点糖分也不肯剩,全吮进嘴巴里,一边吮他一边问:“爹,甜不?”“甜!”爹回答得斩钉截铁。
除了甜的,还有香的。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拉大车,跳下猪圈起粪,又累又饿,最想吃的就是葱油大饼。可是家里常年连白面都没有几斤,哪里有余粮烙饼。有一次爹被征去修河堤,活又苦又重,晚上有加餐,一个人分一斤饼。爹一口也没舍得吃,十五六里山路星夜奔回,叫醒娘仨--娘,他,还有他的哥哥,一块分享这一顿盛宴。他身体弱,受优待,分的最多。爹只给自己留了窄窄的一条,正捏住往嘴里送,转头发现他渴望的眼神,又把这一条撕一大半,喂到他嘴里,把另一小半喂到哥哥嘴里,然后爹就吮手上的油,一边吮一边把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真香!”
那个时候,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好有本事,挣好多好多钱,给爹一气买好几十斤葱油大饼!
几乎是转眼间,二十年又过去了。哥哥没考上学,在家里务农,娶妻生子,过自己的小光景;他考了出来,虽然只是当了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挣钱不多,但是在农村人的眼里,就算很有出息了。一样娶妻生子,过自己的小光景。与此同时,爹迅速衰老下去,年轻时的挣命劳作,现在要他的身体连本带息,全部返还。几乎是一夜之间,爹就半身不遂了,然后又是一夜之间,得了糖尿病,然后呢?一个又一个一夜之间,爹的身体从原先的强壮如牛,变成现在的软弱如婴儿。
而他,也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心理不平衡。
爹第一次得病,他跑前跑后,看病,化验,前前后后花了三千多块钱。这对于一个刚刚举债买了房子,又需要养家糊口的普通老师来说,的确有点难以承受。原本想着哥哥能帮一点,没想到哥哥不但没一点帮忙的意思,而且还大放厥词:“这钱就该他出!谁让他一个月挣那么多钱!”
这话传进他耳朵里的时候,他刚刚为哥哥盖房子筹了两万块钱,而且不顾妻子的反对,把来城里打工的侄女接到家里来吃住,这下子真气得他浑身发冷:我上辈子该你的还是欠你的?爹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然而,父亲的身体真是象一场雪崩,眼看着轰隆隆塌架了。越来越频繁地犯病,一次比一次严重,每次父母都习惯性地给他打电话,他的态度越来越勉强,话越来越冷,钱也给得越来越少。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我哥哥也是儿子,爹有病,他应该负担一半的钱。”这话一出,母亲的脸一下子变得晦暗,而爹常年风吹日晒、浓油赤酱的脸竟也泛上一丝羞红。他不管,假装看不见,反正要让爹娘知道自己的不满,很不满。
可是为什么要在梦里,仍旧一片温柔地对待自己的老父亲呢?
梦还没醒,就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一接电话,又完了:刚还了这个月的房贷,给孩子交了一个月的补习费,气儿还没顺过来,爹又犯了病。这次更严重,不光腿不能走,连话也说不了了,隔着电话只听见呜哩呜噜的声音。
“你爹又犯病了,怎么办?”电话里传来娘迟疑的声音。
“我哥呢?”
“他在这儿哩。可是,他说,他没钱……”
“他没有,我有!来吧!”他气冲冲挂断电话。
再见到爹的时候,他不由惊叹梦的预兆性。父亲果然软如婴儿,得由他半扶半抱。见到他的一霎那,爹的脸上竟浮现出一丝软弱的笑,象婴儿依赖母亲,那样纯真,那样温存。他不由心软:“爹,甭怕,有病治病,有我呢,不要操心。”爹呜噜着问他,象乞问一个神:“我的嘴,还能不能说话?”“能!”他语气轻松。
看病,打针,做检查,打吊瓶。一如既往。哥哥本来跟着来的,他心头一喜:说不定哥哥这次良心发现,能帮着付一付药帐。没想到结帐的时候,哥哥借故有多远跑多远。他的心里这个气!只恨爹娘当初为什么儿子要生两个,这下子唱《墙头记》够人手了。
他心里的火山再也憋不住了,当着重病的老父亲,把药价单摔在哥哥面前:“哥哥,为给爹看病,我里外里花了一万块了,你是长子,赡养父母你也有责任,你就不能分担一点?”哥哥也不是吃素的,反唇相讥:“咱爹妈供你上大学,我说什么了?他们最亲你了,这病就该你替他们看。不就一万块钱吗?你就这么不孝顺?”他气得拂袖而去,把老爹撂在医院里。一路上他脑子里反复闪回娘的泪眼和爹尴尬的笑容,心里一阵阵地疼。但同时又升起一股报复的快感:让哥哥一个人去处理这个烂摊子吧!两个老人分文皆无,他总不能给扔在医院里!
这件事怎么处理的,他始终没有过问。上班,下班,做饭,吃饭,他的电话不打回去,爹娘的电话也不打过来。妻子也不再唠叨了,他的生活清净了许多,但却清净得发空,象夜半的空谷,远远传来啄木鸟啄木的声音:空、空、空……罢!他垂头丧气:何必呢?这气斗的真是不值。难道为了两兄弟不和,就把爹娘架空?明天,给爹买个轮椅去吧。他腿脚不方便了,拄拐杖又太危险,坐个轮椅,方便得很。虽然钱是要花一点,可是,身体都是爹妈给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何至于不舍得花这区区的一千多块钱?
主意打定,马上实施,第二天他就把轮椅买了回来,雪亮的轮椅呀,他看着心里高兴:嗯,先不要告诉爹,今天礼拜一,到礼拜天的时候,拿回去,让他看看,他的小儿子心里想着他呢。到时再让他好好高兴一下吧!
他开始掰着手指头数天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明天,就可以回家了。老父亲坐在轻便轮椅上,他推着父亲在街道上巡行,有人来问,父亲就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嘴巴含混不清地告诉人家:“这是我二子买给我的,花了两千……”
当天晚上,又开始做梦,梦里爹坐着轮椅,一脸的笑,看着眼前的自己,慈爱满眼。然后呢?他在神奇地缩小,缩小,缩小到十来岁的模样,圆圆的脸,虎头虎脑,捧着一角葱油大饼,眼睛还看着爹那一块……梦还没醒,电话铃响,一看来电,马上拿起话筒迫不及待:“喂,妈,你们还好吗?我给我爹买了一辆轮椅,明天就给他送回去。”
“二子”,电话那头传来压抑不住的哭声:“你爹用不上了……”
发丧、送葬、一系列的程序做完,他的身上象抽了筋,软绵绵的提不起精神。耳边还在响着娘絮絮的哭声:“你爹上次从你那儿走后,又添了心脏病,怕你又跟你哥哥闹意见,忍着不让告诉你。又怕再让你花钱,不舍得看……到严重的时候,嘴唇都憋得乌青乌青的。昨晚他说难受,想二子。我要给你打电话,他又不让,说你正睡觉哩,教课很累的,等明天早晨。谁知半夜里他就……”
坐在给父亲买的轮椅上,抽一袋子父亲那廉价的叶子烟,青色烟雾袅袅升腾,烟雾里再也看不见老父亲憨厚的脸。到现在才明白,一切争端都是无用,“子欲养而亲不在”才是最深的痛,痛就痛在,此生再也,无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