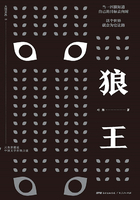在等叮叮来的当中,我盯着赵大禾的公司看了很久。这幢大楼层层叠叠的楼层让人很难细数具体有多少层,在楼房的最上端,好像生长着许多绿色植物,几个超大型的字体“赵氏矿业集团股份责任有限公司”排得整整齐齐,像几只成了精的蜘蛛爬在绿色植物下方。这里是赵大禾的地盘,不是我呆的地方,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精英。
叮叮开车来接我,见我站在这里,惊奇地问:“怎么上这地来了,是瞄准了什么大人物还是走亲戚啊?”
我不能说是来找赵大禾的,撒个谎说只是路过。叮叮看了看大楼顶端那几个字,嘿嘿地笑了,说:“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哪里,那个小女孩的大款爹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们不是早就决定不动他了吗?”
叮叮不知从哪里带来了一个瘦不拉几的修理工,脸颊凹陷下去,像是几年没吃饱饭。他掀起我的车子前盖,左右敲击,半天也没见他敲出个名堂来。叮叮那辆破车已经有躁音了,还是老田在的时候花三万块买来的。我问那个修车的:“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他像是被污辱了,斜我一眼,说:“不会修我跑来这里干嘛,吃饱了撑得啊。”
我问他几时能修好,他说不知道,可能要换什么东西,需要一些时间。我委屈地上了叮叮的破车,这里摸摸,那里拍拍,座位破旧不堪,坐下去发出吱吱的声响,车窗玻璃上还有几条裂痕,找不到一块像样的地方,跟他原来那辆“桑塔纳”差远了。我说:“你这车能开得动吗,不会半路上掉轮子吧?”
叮叮没好气地说:“开一天算一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穷死了啊。”接着他问我认不认识东城区开地下赌坊的那个刘麻子。
“知道啊,在他那赌过好几回,我赢过他不少钱,他看见我都怕。”
“这两天不知打哪儿跑来了一个土老板,每天在他那儿输一两万就走,不带眨一下眼睛,已经有好几天了。”
“还有这等好事啊。”我一阵兴奋,“这便宜可不能让刘麻子一人独占了,这小子也就凭会出两手老千骗骗小瘪三,在我面前捏不出个好屁。”
“就是嘛,谁不知道你是老千高手,这好事可不能白白放过。”叮叮讨好地说。
这马屁拍得舒服之极,我一时兴起,拍着大腿说:“晚上我们去狠宰他几刀,赢了分你一半,我们叫上王钦一块去。”
我开始给王钦打电话,叮叮的这个消息来得很及时,暂时让我忘了刚才在赵大禾那里的不快。赌徒最大的兴趣就是有赌局玩。王钦在电话里说他不想去,说一到刘麻子那里就会想起老田,心里不舒服。我问叮叮:“老田什么时候上过那儿,我都不记得了?”
“你真的忘了,他那个老婆不是那里泡的吗。”
我悟过神来,老田的老婆曾是那家小赌坊里一个漂亮的服务员。老田有一次在那玩时喝多了酒,又吐又闹,那服务员对他伺候的很好,又递水又拿毛巾,让老田心生好感,没几天就开着车狂追起她来。我心里升起一缕物是人非的伤感,故人已去,大家开心的时候一晃就过去了。老田追到了女服务员,老田也结了婚,老田也离开了人世。
叮叮问我要不要再弄个漂亮妞陪陪,说玩得太晚也有个乐趣。我白他一眼,这家伙一天到晚就离不开女人。我说不要,要弄你自己弄,我不喜欢赌博的时候有女人在边上。叮叮思谋了半天,掏出电话窃窃私语一阵,我听出他是在给柳慧慧打,心想什么女人不好找,又找这烂货,这婊子还真能折腾我们兄弟。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碰这女人一下。
天空刚刚降下热度来,外面旋起了一些风,几丝凉爽扑在脸上,犹如哪个可爱的女子在你面前轻呵了一口气。马路上两边的叫不出名的树叶子在轻轻晃动,像一些按摩店里的小姐站在门口冲着路人招手。
我在自己房间里换好衣服,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大箱子,开始配置晚上要用的那些出老千的装备。比如透视眼镜,灌水银的骰子,触摸式扑克,以及其它一些先进的道具等等,这些宝贝我弄了几年才弄齐全。整理了半天,叮叮的车已在楼下不停地按响着喇叭,我下了楼骂道:“催什么催啊,不弄好装备能赚到银子吗?”
“不是我按的。”叮叮尴尬的笑着说。
“那是谁他妈按的,这么想找抽啊?”我跑过去拉开车门,定眼一看,眉头大皱。车里还坐着另外一个人,一个穿得花艳浓色,满脸笑逐颜开的女人,正是柳慧慧。
“阿昭,我以为你睡着了呢。”柳慧慧吃吃地笑望着我,嘴里嚼着泡泡糖玩,吹出来又缩回去,一双大大的杏眼透露着无限妖艳。
“哪能呢,我这个人一听有赌,三天三夜都可以不睡。”我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地坐到车子后面。这个死叮叮,走到哪儿都要带着柳慧慧,也不怕人笑话。
我们先到一家餐馆里去吃了一顿大餐,叮叮拼命说等会儿要他来付钱,可能他知道我晚上会有银子进账,指望我多分他一份。柳慧慧已面貌一新,又换了个新的发型,当着叮叮的面,在我面前装得斯文十足,弄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也不和我多说话,只跟叮叮嘻嘻哈哈的。我也不理她,暗想叮叮也是活该,明知道她除了老田之外还跟过很多人,竟然一点也不嫌弃。
男人跟女人的相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依赖,另一种就是精神上的。叮叮可能属于后一种。有时我很想不透,在我们四个人中,能够出现像叮叮这种恋情的男人,恋得又是这种女人,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王钦在我的不断邀请下还是开车来了,他开的是一辆QQ小型车,应该是他那个女朋友的,一点都不配他的形象。王钦说他只是来吃饭的,近来手气太差,不想去赌博,。吃饭期间,他问我还有多少本钱,不要赌输光了连车都养不起了。我大笑着说:“以前跟老田比我不敢说,那个刘麻子算什么角色啊,两年前就是我手下败将。他要想赢我,除非让他娘重新再生他一次。”
两年前,我第一次去东城区地下赌坊的时候,刘麻子可谓是一个大牌,赌技高明,名气远扬,大有天下霸主的气魄。我记得当时我是去替叮叮报仇雪恨的。有一次叮叮哭丧着脸跟我说,他被刘麻子玩了一把,栽进去一万多。我问他们玩的是什么,叮叮说也就是普通的梭哈,好几次明明他有把握的牌,就是被刘麻子吃了,真想不通。
我哈哈大笑,说:“就你那盗版的水平,正儿八经地去跟人家玩,那不是给人送钱吗,看哥哥教你一手,保你一辈子享用不尽。”
尽管有我的打气,叮叮还是不敢,只怂恿我去挑战刘麻子。
那时我刚学会了一手牌技,手也正痒痒的,想找个人小试一把牛刀。到刘麻子那儿,这家伙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式,一张嘴就问我带了多少钱,说他可不跟没钱的人玩。我说我身上就两万块,赌一把输赢就走。刘麻子不屑地问我玩什么,我说就玩个新鲜的吧,可能你一辈子都没见过。
刘麻子显出一脸的惊奇。我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副牌盖在桌面上,让他从里面给我挑出一张老K来。刘麻子愣愣地说,这:“我怎么挑得出来,我又不是变魔术的。”
“你随便挑,挑出后就盖在桌上,你不准看。”
刘麻子想看我玩什么花招,就按我说的随便挑了一张。我把那张牌面向自己,看了看,然后搁在桌角,用一只茶杯压住,问他:“你相信这张是老K吗?”
刘麻子嘿嘿地笑了,说:“绝对不可能。”
我把两万块钱甩在桌上,说:“你敢不敢赌?”
如我所愿,刘麻子盯了会儿我的眼睛,跟着下了两万块钱的赌注,估计他以为我是在诈他。况且他死也不会相信,他这么随手挑出来的牌就会是我说的老K。我笑眯眯地点着一根烟,等我叫他从茶杯下把那张牌开出来时,刘麻子立即傻了眼。
这张牌确是老K。
刘麻子与叮叮稀里糊涂的看着我得意地收起了桌子上的钱。过后叮叮疑惑地问我:“你这是什么手法,怎么没看清你换牌啊?”
“我根本就没换牌,这也不是手法,这是吉普赛暗示法。”看着叮叮傻傻的样子,我跟讲了一下这种牌的理论。
一副牌里有四张老K,这就有百分之十三的概率。如果第一张对方挑的牌不是老K而是A,我会让他再挑一张牌,这回就得报A,概率有百分之五十二。如果第二张正好是K,那么牌局便结束,就可以下赌注了。以此类推,最好不超过三次,否则会让别人起疑心。这种牌技想玩熟练的话,需要较长时间,等熟练之后让人挑牌往往都很准。
从此以后叮叮在牌桌上奉我为祖师爷,每次他想到外面赌博都要拉上我。所以此刻我敢告诉王钦我对刘麻子的蔑视并不是什么轻敌的表现。
“我不是担心刘麻子。”王钦说,“我是担心你说的那个什么土老板,你不是想吃他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别让他把你给吃了。”
我拍拍王钦的肩膀,说:“你学过几何吗,那个土老板赢不过刘麻子,刘麻子又赢不过我,你说,土老板能赢过我吗?”
我们吃了两三个小时,王钦提出来要先走,走到车前说忘了拿车钥匙,叫我递过去。我走到他跟前,王钦看了下叮叮那边,暗暗问我:“你是不是也上过了柳慧慧?”
我慌忙否认:“没有。”
王钦死盯了我看,说:“柳慧慧不是什么好货,我不反对你跟她玩玩,只是如果她想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影响了正事,我会宰了这婊子。”
我说:“你听到什么了,柳慧慧有这能耐吗?”
王钦冷冷笑道:“最毒妇人心,女人要出卖你是不用理由的,我可是吃过苦头。虽然我现在还不明白柳慧慧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她已经这样做了,你要小心点。”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心生疑虑,想问个究竟。
王钦瞧了瞧与柳慧慧聊得亲热的叮叮,说:“叮叮太喜欢这女人了,所以她说什么他都会相信,我怕她利用叮叮来调拨你们的关系。”
我笑了,不屑地说:“调拨什么,有什么好挑拨的。”
王钦摇摇头,说:“不知道,我只是偶尔一次在厕所里听到叮叮发了句牢骚,他对你可是有很大的意见。”
我再次去看叮叮,他坐在餐厅里,架着二郎腿,端着一杯饮料与柳慧慧打情骂俏,笑得不亦乐乎。联想到刚才他对我的那一系列表情,我丝毫没看出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可能是王钦太多心了,这是他一惯的作风。不过有一点大家都很佩服王钦,那就是他做事不仅细心,而且为人也很义气,老田正是受他的影响才肯加入到我们当中。
我催王钦赶紧开车,关上他的车门,笑着说:“你放心,没事的,我跟叮叮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能被这女人挑拨,那不是笑话吗?”
王钦点点头,启动车子时丢下一句话:“没事就好,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一声,柳慧慧说了你跟她在车里做爱的事,我亲耳听见的。”
看着王钦的车子绝尘而去,我怔住了几秒钟。
柳慧慧说这些有什么意图?刺激叮叮吗?
我有点搞不明白了。叮叮有可能与我拉脸吗?更难以想象。我又掏了根烟叼在嘴里,慢悠悠地点着,猛吸一口,把烟雾吐向空中。
整座城市在我喷出的烟雾中威严依旧,街灯挺立得笔直,玻璃墙面折射着太阳的光线,街心的喷泉盛开的似一把雨伞。宽敞的街面是一条长长的织带,在我的视野里平铺开去,四散延伸,如同我散乱的思绪。林立的楼宇聚集着挤成一簇一簇,跟一堆散洒在地平线上错落有致的积木一样,被黄昏的余光染成了美丽的桔红颜色。
我对这个城市应该是熟悉的,然而又像是陌生的。
可能它变化的太快了吧,仿佛就是一瞬间的事。我还未做好准备,它一下子就多了那么多外来的东西,脚踏三轮车被出租车取代,街边的摊点移进小巷了里,装修漂亮的商店越来越多,一些其它城市的模式似乎陆陆续续搬到了这里。原本质朴的益州人什么时候也渐渐淡去了曾经的形象,都清一色穿得鲜亮了许多,加快了行走的节奏。
这种节奏让我很不习惯,也不是很喜欢。我怕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会让我惶恐不安,让我失去原先的安全感。
叮叮与柳慧慧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后,叮叮望着远去的车子说:“王钦现在只知道天天守着他老婆,很久我们都没在一块好好玩过了。”
我把烟灰弹向街边的一块灯牌,笑着说:“是啊,人都会变的,连老田就扛不住命运的捉弄,我也不知道我们还能玩到什么时候。”
叮叮捅我一拳,笑道:“阿昭你是怎么了,突然伤感起来了,不像你的风格啊。”
我微笑着盯着叮叮的面容,思维飘散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