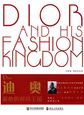约翰·莫立和我都认为马修·阿诺德是我们认识的最有魅力的人。他有种“吸引力”——这是唯一可以形容他出场效果和说话方式的词。即便是他的外貌或严肃的沉默也很有吸引力。
1880年,他和我们一起坐马车旅行,游览英格兰南部。同行的还有威廉·
布莱克和埃德温·A.艾比。在临近一个小村庄时,他问我是否可以让马车停几分钟,他解释说,这里是他教父基布尔主教的安息之地,他想要去祭拜一下他的坟墓。他继续道:
“啊,亲爱的基布尔!我在神学上的观点让他十分伤心,也让我十分伤心。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我的好朋友,他专程赶到牛津,为我竞选英国诗歌教授投票。”
我们一起走到静静的墓地,马修·阿诺德在基布尔的墓边默默沉思,这一幕牢牢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后来,我们谈到了他的神学见解,他说这些观点伤害了他最好的朋友。
“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向我表达过他深深的失望和不愉快,说我应该要成为一个主教。毫无疑问,我的写作阻碍了我的晋升,也伤害了我的朋友,但我无法控制,我必须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最后几个字时悲伤的语气和缓慢的节奏,这是他内心深处的话。他向大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随着时代的进步,大众开始接受他的观点。如今,他的教义不再受到任何谴责。马修·阿诺德是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无礼的话。在这点上,他和格莱斯顿都无可厚非。
但是他曾用短短一句话抹杀了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反对奇迹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因为奇迹并不存在。”
他和他的女儿(即现在的惠特里奇夫人)在1883年来过我们在纽约的家做客,也曾到我们在阿勒格尼山顶的家来拜访,因此我常常能见到他。我母亲和我曾用马车送他去纽约作第一次演讲。那次演讲的观众十分友好,但演讲不算成功,因为他不善于在公众面前演讲,他没有能力吸引观众。当我们回到家,他第一句话是:“哦,你们觉得怎么样?告诉我!我可以当一个演说家吗?”
我太希望他成功了,所以没有丝毫犹豫就告诉他,除非他适应了在公众面前讲话,否则他绝不可能成功。他必须要找一个演说家指点他一下。我的要求如此强烈,他同意了。在我们说完之后,他转向我母亲说道:“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已经给出了意见,但我想要知道你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讲有什么评价。”
“太严肃了,阿诺德先生,太严肃了。”我母亲慢慢地、温柔地说道。
阿诺德先生后来偶尔会提起这件事,当时他觉得这句话是当头一棒。当他从西部之旅回到纽约后,他进步很大,他的嗓音完全比得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他听从了我们的建议,跟着一位波士顿的演讲教授学习,之后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
他希望去听着名牧师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出发前往布鲁克林。我们提前通知了比彻先生,这样他可以在演讲后留下来和阿诺德先生见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他十分热情地欢迎阿诺德。比彻先生终于能见到神交已久的阿诺德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他握着阿诺德的手说:“阿诺德先生,你写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地读过,许多文章还读过好多遍,而且每次读都有所收获,每一次!”
“哦,这样的话,比彻先生,我恐怕你会发现,那些涉及你的段落应该被删除。”阿诺德先生回应到。
“哦,不,不,那些对我大有好处。”比彻先生笑着说,之后他们同时放声大笑。
比彻先生从不会不知所措。在我把马修·阿诺德介绍给他认识后,我还有幸为他介绍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英格索尔小姐还是第一次来基督教堂。”
他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直视着她慢慢地说道:“哇,哇,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异教徒。”那些见过年轻时的英格索尔小姐的人,都与比彻先生有同感。之后他又说:“你的父亲怎么样,英格索尔小姐?我希望他一切顺利。我们许多次都一同站在讲台上。能和他站在一起,我是多么的幸运啊!”
比彻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心胸开阔、慷慨大方的人,他善于吸收精华。
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融合了直觉的洞察力,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立场,都是对国家有益的。比彻先生给了这些朋友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1887年,阿诺德来我们苏格兰的家做客。一天,我们谈起体育,他说自己不狩猎,他不能杀死任何有翅膀的、能在蓝天翱翔的生物。不过他补充道,他没有放弃钓鱼——“那种感觉太愉悦了。”他谈到一位公爵,每年会给他两三次一整天的钓鱼时间。我忘记那位公爵是谁了,但是他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我们问阿诺德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有如此密切的来往。
“啊!”他说,“一位公爵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位重要人士,无论他的智商或行为如何。我们都是势利小人,百年的历史让我们全部成了势利小人。
我们无法抵抗,这是天生的。”
他微笑着说完这段话,我觉得他内心还有所保留。他本身不是个势利小人,而是一个天生就会“对有历史悠久的血统背景的人微笑”的人,一般来说,“血统”是无法质疑的。
然而,他确实对掌权者和有钱人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见范德比尔特先生。我大胆地推测,阿诺德会发现他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是的,但是认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他回答道,“这个全靠自己奋斗发财的人,显然会使那些依靠继承遗产的人黯然失色。”
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从没写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学评论。他说他有过这个想法,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去评论,更别说是批判莎士比亚了。他无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莎士比亚如此出众,他的作品无法用任何文学评论的规则来衡量,而且他希望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位天才的作品,因此总是回避这个话题。我说我对他有信心,因为他曾写出过至今无人能及的颂词,我帮他回忆了他写过的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他人遭受质疑,唯君独享自由。
我们问了又问,你微笑不语,耸立在知识之巅,像崇高的山岭。
那个被废黜的陛下,把脚跟扎进了海底,坚定不移。
让他所停留的地方成为天堂,只留下烟雾笼罩的山麓边缘,凡人徒劳地在死亡寻索;而你,是我们的星星,我们的阳光,你自审,自信,自我建树光荣,所有必须忍受的痛苦需要不朽精神,不再软弱,不再悲痛,找到自己胜利的唯一的呼声。
我认识肖先生(乔希·比林斯),并希望亲切又和蔼的传道者阿诺德先生能见见他,因为他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幸运的是,一天早晨,乔希来温莎酒店找我。我们当时住在那里,他还提到了阿诺德,并表达了仰慕之情。我说:“你今晚可以和他共进晚餐。女士们都外出了,只剩下阿诺德和我一起吃晚餐,你加入后,正好变成三人小组。”
他是一个害羞的人,拒绝了我的邀请,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我不接受任何借口,他必须答应我的邀请。他最终答应了。晚餐时,我坐在他们两位中间,看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会面,乐在其中。阿诺德先生对肖先生的说话方式很感兴趣,而且很喜欢听他说的西部轶事,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这么开怀。肖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他在演讲中发生的小插曲,因为15年来,他在美国所有人口超过一万的地方都作过演讲。
阿诺德先生渴望听到一个演说家是怎样吸引观众的。
“好的,”他说,“让他们笑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他们会认为你在笑话他们。观众听过笑话后,你一定要认真严肃地继续演讲。例如,‘在人生中,有两件事人类是无法预先准备的,谁愿意告诉我是哪两样?’有人大喊道:‘死亡。’‘好的,谁告诉我另外一个答案?’我得到了很多回复——财富、幸福、力量、婚约、税收。最后,我严肃地说:‘没有人说对第二个答案。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人类没法预先准备,那就是双胞胎。’然后屋子里的笑声都可以掀翻屋顶了。”阿诺德先生也哈哈大笑。
“你一直不断地编新段子吗?”阿诺德先生问道。
“是的,一直在编。如果你没有新段子,那你不可能年复一年地演讲,段子有时候也会不起作用。曾经有一次,我准备了自认为很搞笑的段子,一定能让全场笑翻,但却事与愿违,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都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在密歇根州的一天晚上,我坐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我知道这个词肯定能达到非凡的效果。我在孩子们中试验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这个词,比以前我用过的别的词产生的效果都要持久。我说道:
‘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完全理解之前,人们不会相信任何事。现在既有约拿又有鲸鱼。他们想要了解一切。在我看来,不管是约拿还是鲸鱼,他们都没完全弄懂。之后他们会问,约拿在鲸鱼的社会中干什么。’”
一天,肖先生沿着百老汇大街散步,一位真正的西部人上前搭讪:
“我想你是乔希·比林斯吧?”
“嗯,有时候我是叫这个名字。”
“我的口袋书里夹着给你的五千美元。”
“这里有一家戴尔蒙尼餐厅,进去坐坐,告诉我怎么一回事。”
他们坐下后,这个陌生人作了自我介绍。他是加州一个金矿的股东之一,股东们为了所有权问题产生了争议,合伙人会议也在争吵中不了了之。这个陌生人在离开会议前还威胁说,他敢于承担风险,进行法律诉讼。“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合伙人会议,告诉他们,我早上时翻了乔希·比林斯年鉴,今天的警句是:‘与其冒险去抓住牛角,不如换做抓牛尾,这样你会抓得更牢,并且在决定要放手时就能放手。’我们都哈哈大笑,觉得这句话十分有道理。我们听从了你的建议,解决了争端,在友好的气氛中散会。有人提议说,应该要给乔希五千美元。正好今天我要来东部,他们委派我来转交这笔钱,我也保证一定完成任务。钱在这里。”
我们那天的晚餐,是以阿诺德先生的话结束的:
“好了,肖先生,如果你愿意来英国作演讲,我很乐意欢迎你并把你介绍给第一批观众。其实由任何一个愚蠢的勋爵来介绍你,效果都会比我介绍你好,但是我真的十分乐意这么做。”
谁能想到,亲切又和蔼的传道者马修·阿诺德,要把开玩笑高手乔希·
比林斯介绍给伦敦的观众。
多年之后,他从没有忘记问候“我们狮子般的朋友,肖先生”。
在那次特别的晚餐之后几天的一个早晨,我和乔希在温莎的圆形大厅见面,他拿出一本小小的备忘录,说道:
“阿诺德在哪?我在想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世纪》每周付给我100美元,我同意写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有趣的琐事,并寄给他们。我试着写点什么,下面这则是来自齐基尔舅舅,是我这周的存货:‘评论家当然比作家伟大。任何能指出其他人犯的错误的人都比犯错误的人聪明得多。’”
我给阿诺德先生讲了一个芝加哥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关于芝加哥的故事。波士顿的一位女士到芝加哥拜访将要结婚的同学,注意力完全被芝加哥吸引了。一天晚上,一位知名人士问她,芝加哥最让她着迷的是什么,她优雅地回答道:
“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不是繁华的商业,也不是物质上显着的发展,更不是豪华的住宅,而是这里丰富的文化和优雅的氛围。”
他很快回复道:“哦,没错,这里的人们为流行而神魂颠倒。”
阿诺德先生没有作好享受芝加哥的准备,这个城市留给他的印象是庸俗之都。然后,对于能够遇见那么多“文化和文明”,他十分惊喜。在他出发之前,他很好奇,想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最有趣的事物。我笑着说,他也许先会被带去参观那里最壮观的景色——屠宰场。那里的最新机器十分先进,把猪赶进机器的一端,它的嚎叫声还没从你耳边消逝,另一端火腿就已经出来了。他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问: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去屠宰场?为什么有人会去听猪的嚎叫声呢?”我说不出个原委,这件事就此结束。
阿诺德先生经常引用以赛亚的话,称他为伟大的诗人,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旧约》中,阿诺德先生最喜欢的就是以赛亚。在我环游世界的途中,我发现其他宗教的圣典中的内容,都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我记得阿诺德先生说过,《圣经》也应该被这样处理。那些闻名世界的孔子和其他圣人的经典,都经过了精心挑选,以语录的形式出版。门徒们没有在书中加入无知愚昧的内容。
在这件事上考虑得越多,我的想法就越强烈,认为基督徒应该学习东方的做法,把小麦从谷壳中筛选出来,有时候甚至要从比谷壳更糟糕的垃圾中挑选出小麦。在《星期六晚的小屋》中,彭斯描绘了一个虔诚的人,为了晚祷仪式而抄写圣经。
“他审慎地精选了一部分。”
我们应该精选出一部分重点,以后只使用这些。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上,我都很感激能认识阿诺德先生这样的朋友。他被证明是一个领先于时代的真正的老师,也是在“未来和未知事物”方面最伟大、最具诗意的老师。
我把阿诺德先生从我们在阿勒格尼山的克里森的避暑胜地,带到了黑烟缭绕的匹兹堡。在从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到火车站的路上,横跨铁轨的天桥有两段楼梯,第二段楼梯特别的陡。当他爬到四分之三时,突然停下来,大口喘气。他靠在栏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对我说:“啊!总有一天它会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父亲一样。”
我那时不知道他有心脏病,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不久之后,我听到消息,他突然去世了。在英国他曾经努力躲开这道坎,想起他曾对自己命运的预测,我更加悲痛。失去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彭斯笔下的参孙的墓志铭了:
疲倦的他安息于此虔诚的追随者,放他一马!
如若诚实可以通往天堂,那么他已经离天堂不远了。
我现在想起了一个人,波士顿的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医生。大家都很喜欢他。他一直活到了80岁,但他自始至终是个大男孩。在马修·阿诺德去世后,一些朋友忍不住要以某种方式纪念他。他们默默地捐出必要数目的钱,没有想要动用公众的力量。他们认为,只有一些特定的人才有资格为这个基金捐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早就可以轻松地筹集到两三倍的钱了。我有幸被选中,成为有资格捐款的人之一,并在大西洋另一侧关注着这件事。当然,我从没有想到向霍姆斯医生提起这件事,不是因为他没有被选中,而是因为作家和专家不该被要求为这项基金捐款,因为这项基金主要就是为他们设立的。然而,一天早上,我收到了医生的短笺,说有人偷偷告诉他正在进行中的这个项目,还提到我也有份参与,他问是否自己也有足够的资格加入到捐款的行列中来。如果可以,他会十分感激。自从他听说了这件事,他无法抑制给我写信的冲动,希望能得到回复。不用说,他当然够资格。
人人都希望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敢说,捐款的人中,人人都会感激命运给予他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