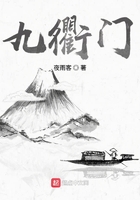他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几十场展览。他用一根根绳子,将这些照片串在一起,挂在城市的街头,与其说他展览的是他拍摄的一幅幅照片,不如说是一张张极度穷困、极度悲哀、极度绝望的脸,他希望人们记住这些可怜的面孔,并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帮助。
他自创了一种爱心资助模式:一对一。如果你被某张照片打动,希望帮助照片背后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么,他会将有关这个孩子的资料,全部提供给你。
通过这种方式,已经有一万三千多名孩子获得资助,重新回到校园。
他是这样算账的。能借宿的,绝不住店;能步行的,绝不乘车。他省下每一分钱,就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走得更远,拍到更多的孩子。有个北京朋友曾经请他吃了一顿饭,花了142元。朋友结账时,他心疼不已,他说,这是西部一个家庭一年的伙食费。说完,端起一个盘子,将里面的剩菜,呼噜呼噜全吃掉了。
他叫王搏,他的身份是甘肃天水的一位普通农民。但是,有人说他是摄影师,有人说他是慈善大使,有人说他是志愿者。他说自己只是个农民志愿者。
通过他的镜头,一万三千多名贫穷失学孩子获得了帮助,其中一些孩子的命运,可能从此改变。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可是,相对于他拍摄过的贫穷孩子,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相对于他所亲眼看到的还没有拍摄过的贫穷孩子,这更是沧海一粟。拍得越多,走到的地方越偏远,接触到的贫困孩子和家庭越多,他越觉得自己力不从心。
有人劝他,你不是救世主,那么多因为疾病、穷困失学的孩子,你帮得了吗?
他说了一个故事。大海边,每次海水退潮时,都会有很多小鱼被搁浅在沙滩上,烈日很快就会将它们烤焦。有位住在海边的老人,总是跟在潮水的后面,将一条条搁浅的小鱼,捡起来,扔回大海。有人劝他,你这样能救活几条鱼,更多的小鱼,没等到你去救它们,就早已死了。可是,老人说,捡一条,是一条。
王搏说,和那位老人一样,我也是帮一个,是一个。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曾经感动了无数人。一个都不能少,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可是,有多少孩子,正在失学,有多少穷困的家庭,仍然挣扎在苦难的边缘。和王搏一样,我们大多是普通人,靠辛苦所得养活自己和家人,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不是救世主,但是,以我们的微薄之力,却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你帮助了一个孩子,就少了一张愁苦的脸;你帮助了一个孩子,这个世界,就多了一张笑脸,多了一份温暖,一份希望。
一朵一朵的阳光
娘说阳光都是一朵一朵的,聚到一起,抱成一团,就连成了片,就有了春天。
分开,又变成一朵一朵,就有了冬天。
一朵一朵的阳光聚聚合合,就像世上的人们,就像家。
男孩把盛满水的碗递给男人,说,娘还说,爬上灶台的这朵阳光,某一天,也会照着你爹的脸呢。
求己不如求人
文/周海亮
这是一个分工愈来愈精细的世界,像链条,你只是其中一环。
不管你如何出色,不管你的位置有多重要,你仍然是其中一环,你代替不了任何人,环环相扣才构成链条的本身。我指的不仅是你的工作。
总会有你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小到往墙上挂一幅画,大到做一场战役的统领。这时候需要什么?求人。
求人是合作的一种方式。求人时,你与对方结成暂时的团队,这是双方甚至多方能量的补充。刘备的三顾茅庐是一种求人,比尔·盖茨最初劝说史蒂夫·鲍尔默与其合作是一种求人,你为自己的房子办贷款是一种求人,甚至,你周末去看牙医,也是一种求人——求人并不卑下。从某些角度来说,求人构成我们的生活,从而构成我们的世界——所以有了三国的鼎立与抗衡,所以有了庞大的微软帝国,所以你住上了宽敞的房子,所以你的牙齿重新变得坚固。求人与天才无关,与智慧无关,与时代无关,与机缘无关,甚至,求人与实力无关。有关的是你的态度。
独立是一种品质。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做到真正的独立。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修建出自己的木屋,蒲松龄在淄川西蒲村的老树下铺满了草席,他们看似过起一种完全隐居的 “独立”生活,但是,假如他们真正做到“独立”,世界上就绝不可能出现《瓦尔登湖》和《聊斋志异》。我们不仅在生活上做不到完全真正的独立,思想上同样做不到。
“求人不如求己”是对独立的褒赏和认同,却不是教导人们诸事只靠自己的微薄力量;“求己不如求人”是对合作的鼓励和肯定,却绝非是对独立自主完全的彻底的否定。“求己”更多表现为被动,“求人”更多表现为主动;“求己”是一种品质,“求人”则是一种智慧。
“求己”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求人”也是;“求己”是相对的,“求人”也是。我的意思是:迷信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人生大忌;我的建议是,诸事先求己,再求人。先给自己以信心,再给别人以信任。而当己所不能,不妨求人。
一切豁然开朗。
和生命拉钩
文/朱成玉
那时我在医院做阑尾炎手术,五岁的女儿像个小大人似的跑前跑后地照顾我,让疼痛不知不觉地渐渐远离了我。她就像一个小小的太阳,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点燃一个春天,哪里就会春意盎然,鸟语花香。女儿的乖巧使得病房里的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尤其是邻床的一个老太太。她看来是个重病患者,行动很不方便,连说话都很吃力的样子,可是每当看到我的女儿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便闪着光亮,跟着她的身影不停地转动。
女儿也喜欢她,偷偷跟我说她像她死去的奶奶。她常常爬到老人的床上去,缠着她讲故事。老人的故事很好听,就连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都会听得入神。但是很显然,她很累,每讲完一个故事,她的额头上都会沁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来。但每隔一会儿,她还会把女儿叫过去,接着给她讲故事,她知道这是她唯一可以让孩子坐到她床边的办法。在讲过第五个故事之后,她咯血了。护士一边批评她一边给她按摩,她憨憨地笑着说:“俺只想跟孩子多说会儿话。”
医生说她的病情非常严重,现在就是靠药物来维持着。当初是一个好心人救了她,把她送到医院来的,她靠拾荒为生,一个亲人都没有,拿不出钱来治病。医院已经为她垫付了2000多元了,为此,医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就是否继续为老人提供无偿治疗展开讨论,最后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一个“无底洞”,而医院毕竟不是慈善机构,都同意给老人停药。
停药就意味着宣判了她的死刑。在拔掉那些针管之前,几个善良的医生凑钱给她买了新衣服。在给她穿上新衣服的时候,护士们低声和我们说,或许那是她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她也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和护士说出了她的心愿。
谁都没有想到,她最后的心愿竟然是想搂搂我的女儿。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个要求是那样“过分”,谁会和一个将死的人躺在一个被窝啊!当医生向我们转达了她的愿望的时候,我们甚至来不及思考就一口回绝了,女儿不明就里,大声嚷嚷着要去,原因是可以听奶奶讲很多很多好听的故事。我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没有亲人的老人将死的时候的那种孤寂,那是比死亡更可怕的黑暗,可是我不能,也不敢让小小的女儿那么小就那么近距离地懂得死亡的含义。我叫家人把孩子领回家,孩子撅着嘴,很不情愿地跟着家人离开了。忽然,她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又跑了回来。她来到老人床边,在老人耳边小声嘀咕着什么,还神秘兮兮地把手伸进老人的被窝里。我们看到,老人微笑着向她点了点头,仿佛她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一样。
小小的太阳走掉了,病房里顿时变成了萧瑟的秋天,处处弥漫着衰败和哀伤的味道。
那个夜里,我很难入睡。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想得到哪怕是片刻的那一份亲情,而我没有给她,我掐灭了她生命里最后一丝火苗。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愧疚起来,朝她那里望过去。
借着月光,我看到老人的身子不停地抖动着,但是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我想她是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吧,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双手可以帮帮她。那个夜晚很平静,我没有因为死亡临近一个生命而感到惊惧,窗外的月光反而有些美丽,我不停地在想一个问题:女儿和老人偷偷地说了什么呢?
第二天早晨,护士来给老人把脉,发现老人的脉搏跳动正常,老人还活着,而且呼吸还比前些天顺畅了许多。
第三天,老人说她有饿的感觉了。她喝了我的家人为她熬的鸡汤。
接下来的几天里,老人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能自己支撑着坐起来了。这在我们这个医学落后的城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一周后,女儿来了,她给老人带来了一个毛茸茸的布娃娃,她说那个布娃娃就是她,让奶奶晚上搂着睡觉,就跟搂着她一样。老人的眼睛又开始闪着光亮,跟着她的身影不停地转动。
女儿忽然“严肃”了起来,她握住老人的手,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
“爸爸,我又有奶奶了,我想让奶奶回家去住。”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郑重决定”弄了个措手不及。女儿说她离开医院的那天,跟老人许下了一个诺言,她让老人等着她再来。她要给她一个大布娃娃,还要认她做奶奶。“说话就要算数,我们还拉钩了呢。”女儿怕我不同意,强调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眼里含满泪水。为老人,也为我的女儿。那一刻,我感到小小的女儿是那样伟大,她让我们这些大人们感到汗颜,无地自容。
院长听说了女儿和老人拉钩的故事之后,又一次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尽全力医治老人的病。“就算是为了一个孩子纯真的心愿。”那是院长在会议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奇迹发生,但我亲身经历的这个奇迹,更加让我刻骨铭心。它是由一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共同创造出来的。
老人出院,住到我们家来。女儿终于如愿以偿地睡到了老人的身边,她又缠着老人讲故事了,老人有些累,说明天给你讲两个,把今天的补上。“好,拉钩。”我又听到女儿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这个五岁的小小的太阳,将她的世界照耀得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夜里的时候,我过来给她们盖被子,我看到那双嫩嫩的胖乎乎的小手和那双骨瘦如柴的苍老的手握在了一起,像一幅摄影作品,极尽和谐之美。像这个世界某个地方正在完成的某种仪式,向我暗示着一种生命的真谛:生命需要爱来传递。爱,会让生命生生不息。